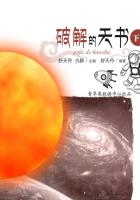1992年冬季的一个周五,书瑶已经上了二年级,下午放学时,天空飘着雪,地上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她已经习惯了四姨家的生活,也习惯了这段长长的上学路。没有犹豫,她戴好帽子手套就一头扎进了风雪了,和几个人同学一起回了家。
大门和家门都开着,可是家里没人,书瑶很纳闷,按说冬天正是农闲的时候,四姨一般都在家,只有四姨父会到镇上的木工厂挣钱,他是个心灵手巧又勤劳善良的人,对书瑶也很温和,不像四姨对他们那么严厉。
“门还开着,可能是去邻居家串门了吧。”书瑶心里这样想着。
到了邻居家,哥哥和妹妹都在那里,邻居阿姨说四姨父在木工厂拉闸中了电,四姨已经赶过去了,让他们兄妹三人先待在邻居家里。书瑶看见哥哥满脸焦急的表情,她的心里也升起一股隐隐的不安,妹妹才四岁,还不懂事,一个人在一边玩儿。
那天的雪很大,飘飘洒洒一直没有要停的意思,他们出不了门外,只能在家里坐着,直到夜深了,雪停了,家人也没来找他们,他们只好在邻居家过夜了。那个时候家里连个电话坐机都没有,更别说手机了,他们得不到四姨和姨父的一点消息。
等一盘大炕上的人都睡熟了时候,书瑶依旧辗转忐忑着无法入睡。她轻轻地捅了哥哥两下,哥哥翻过身来,他果然也没有睡着。
“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瞎说,你个乌鸦嘴!不会有什么事的!”哥哥的声音里带着难掩的不安。
“我就是睡不着,有点害怕!”
“别乱想了,能有什么事,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赶紧睡觉吧。”哥哥的声音更没有底气了。
最终他们在忐忑不安中昏昏沉沉的睡着了,一夜书瑶不停地做着噩梦,有时是被困在高处下不来,有时是被猛兽追咬,她想叫,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想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兄妹三人还在睡梦中,邻居阿姨从外面跑进来使劲的摇着哥哥。
“快起来快起来,你妈回来了,你爸出大事了!”
他们猛的爬起来,眼睛里都是惊慌,胡乱的套上衣服就往家跑去,一进院,一口棺材赫然停在一侧,四姨趴在棺材一边已经哭得哑了嗓子,头发散乱的飘在风中,一些邻居和亲戚在帮忙搭建灵棚,他们有的不住地叹气,有的抬手抹着眼泪。
“妈,这是怎么了?”十岁的哥哥跑过去拉住四姨的胳膊,他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只是不愿相信。
“你爸、你爸他…”四姨压抑的悲伤,却说不出话来,她看着他们几个,红肿的眼睛再次流下泪水,“你爸他没了!”四姨哇的哭出声来,全身剧烈的抽搐着。
“没了…没了…”书瑶嘴里喃喃的重复着,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人和事就那么一点一点地模糊起来。她从未经历过生死离别,眼前发生的一切让她那么措手不及,她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
妹妹在一旁拉着她的手,不知道发生了,满脸惊恐。
停了一夜的雪又下了起来,覆盖了他们的头发和身体,书瑶的心冷冷的疼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亲戚们都陆续赶到,书瑶的爸妈也来了,场面很混乱,每来一拨人都会哭一场,有的是嚎啕大哭,有的是低声呜咽。众人哭的时候,四姨也跟着哭,哥哥妹妹也跟着哭,她也会眼睛涩涩的,泪流不止。妹妹逢人就说“爸爸肯定是睡着了,睡醒了就会起来”,惹得众人更加心酸。
出殡那天,雪后天晴,天气依旧很冷,阳光照在雪地上,白晃晃的一片,刺得人眼睛生疼。哭了几天后,亲人的眼泪似乎都流干了,就那么默默地走成一长溜。放眼望去,满眼白色,披麻戴孝的、扬撒纸钱的,好像都融入了这苍苍的白雪中,被这无情的大地和寒冷吞噬了。
书瑶拉着妹妹在人群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她感觉自己的脚步那么艰难!她怎么也无法相信,四姨父就这么离开了他们,她满脑子都是他的影子:他一仰一伏地蹬着凤凰自行车、他用大海碗大口大口的吸溜着面条、他眯着小眼睛爽朗的大笑…他的影子就那样影影绰绰的浮在眼前、刻在心里,想抹也抹不去。
“姐姐,我爸爸是不是要出远门了?”妹妹摇了摇她的手。
“嗯…”
“他还会回来吗?”
“嗯…”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书瑶重复着妹妹的话,却不知如何回答。她抬头望着天,望着身旁的人们,努力的想找到答案。
在这漫天的雪地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寒冷和漫长…
妈妈陪四姨住了一段时间,四姨说自己命不好,三十几岁就成了寡妇,妈妈安慰她,让她一切向前看,孩子还小需要照顾,一定要振作起来。可话是那么说,谁又能体会那丧夫之痛呢?往往是没说几句姐妹俩就一起哭起来。一直住到放寒假,妈妈才带着书瑶一起回了家。
整个冬天,爸妈都为四姨父的事唏嘘不已,妈妈经常说“人的命,天注定”,但书瑶不信命,她觉得那只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意外。直至临近过年,大家都开始忙碌着拆洗铺盖打扫屋子、包饺子炸油饼贴对联,这种悲伤的气氛才被冲淡了一些。
“过年叫毕力格他们父女俩来咱家吧,人多热闹些,再说一个大男人家的也做不来什么吃的。”热心的妈妈和爸爸商量。
“行,孩子怪可怜的,我这就去叫他。”
“你说他们俩口子也真是的,说离就离了,孩子才六岁,多可怜呀,唉…”
书瑶这才知道他们的邻居毕力格叔叔已经离了婚,六岁的玲花跟了爸爸。那个小女孩很内向,整天讷讷的,仿佛沉默是她唯一的表情。跟人说话时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总会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这也许跟她的父母长年累月的争吵有关吧。
今年冬天的风异常的大,风卷起大粒大粒的沙子,打得人脸上生疼,出门只能带上厚厚的棉帽子,而且必须是像军用棉帽那样两侧有帽檐儿,可以从脖子下面拴住才能保护脸不被沙粒打伤。
他们一起过了年,三个孩子相处的不错,只是玲花比以前她妈妈在的时候更沉默了,这沉默,是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书瑶每每看到她低着头诺诺的样子,心里就堵得难受,她在心里责怪着毕力格叔叔和婶婶,她觉得玲花现在这可怜的处境都是他们的自私造成的。
年后,毕力格叔叔和爸爸一起喝着二锅头,酒过三巡后,他红着脸说:“老哥,我想求你件事,可真是开不了口啊…”
“有话就说吧。”
“我想…我想…”毕力格叔叔的脸更红了,他一个劲儿的抠自己的脑袋,表情很尴尬。
“哎,有什么话就直说嘛,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妈妈笑着走过来。
“我年后要出去打工,想把玲花放在你们家,等秋天她能上学的时候我就把她接走。”
“行,这没问题,我替你照顾她!”妈妈总是那么热心善良。
毕力格叔叔千恩万谢地拿来了几件孩子的换洗衣物,之后就独自远行了,玲花看着爸爸离开,没有哭闹,也没有说什么,像当初妈妈离开的时候一样,她只是低头沉默着。
就这样,玲花暂时成了他们家的一份子,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书瑶把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妹妹,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然而,似乎旁人都很难走进她的内心,她更爱和家里的老白狗待在一起,她常常会搂着白狗的脖子坐上半天,在它耳边小声的说话,有时开心地笑,有时偷偷地掉眼泪。小女孩一定是有许多心事,对身边的人都无从开口,只能将它们告诉老白狗。
年后,天气终于转暖了,雪一点点的消融,露出了褐色的潮湿的大地。书瑶从心里恨这个冬天,不光是因为它异常的寒冷,更因为发生在冬天里的生死和离别,这让她悲伤,也让她早早的看到了这人世间的种种不圆满。
这个漫长多雪的冬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