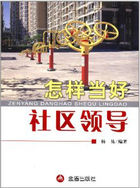时间晃晃悠悠的从高一溜到了高二,书瑶的学习并没有太大的起色,排名也晃晃悠悠的前进了几步却又停滞不前,历史和数学依旧是她的软肋。还好,书瑶并不像班里的一些同学,用多少功成绩都垫底,例如她的舍友周亚娟,让人心生叹息。高二下学期就要分班了,她还在犹豫着选文还是选理,用郝佳的话来说她这是“文不成理不就”。日子并不十分紧张,高一高二的课程只是按部就班的上着,这样的生活倒也惬意。
书瑶和两个同桌关系不错,经常一起聊天,现在王铮和艾丽娜讲解题目的时候,书瑶也会一起研究,虽然她依旧做不出他们不会的题,但她已经不那么自卑了,也许是习惯了吧。王铮还是整天嘻嘻哈哈的,不见其人先闻其声,艾丽娜依旧掩饰不住骨子里的高傲和自信,虽然她尽量做得平易近人。
王龙自打书瑶上次生日起就坚持一直给她写信,每月两封,从不间断,书瑶有时候会给他回信。她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情意,但他没有挑明,她也没有理由拒绝,她感觉这有些残忍,但也没有过多的考虑。
寒假又一次不期而遇,书瑶和弟弟早早赶回家去帮忙,家里雇的羊倌儿年纪大了,耐不住草原冬日的严寒,辞职回家养老去了。父母管着两群牲畜,真够他们忙的。
“过几天我的姑舅姐姐在市里聘闺女,我想去上事宴,还能和多年见不到的老姐妹们好好聊一聊。”妈妈嘀咕着,为生计所累,她已经好久没有出过门了。
“那我骑摩托把你送到镇上,你自己坐班车去吧。”
“爸,你也一起去吧,到事宴上好好热闹热闹,我和书斌在家里看着。”
“这几天天气说变就变,你们两个在家我不放心,还是让你妈自己去吧。”
“爸,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弟弟拍着胸脯保证。
“就是,来回就两天时间,我们都这么大了,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说书斌今年学会骑摩托了,放羊也方便了。你们开车去镇里,把摩托留下。”
爸爸去年花八千块从镇上买了一辆二手的212吉普车,出门总算方便了一些。记得小时候去镇里,不管多冷的天都得坐摩托,虽然戴着皮帽穿着皮裤和毡靴还是抵挡不住风雪的侵袭,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往往冻得她的双腿失去知觉,下车后不能走路,要坐在炕上暖很久才能下地。要是把耳朵冻了就更惨,会像猴子耳朵一样竖起来,又红又肿还很痒。这就需要用雪多搓一会儿,让耳朵慢慢的解冻,千万不能用热水洗,据说会引起血管痉挛,而造成局部坏死,掉了耳朵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好吧,你们小心一点,天气不好就别让羊出去了”。爸爸抽完一根烟后,做了最后的决定。
到了事宴的前一天,爸妈一早就出发了,他们要去赶“夜坐”(家乡的习俗,在婚宴正式开始的前天晚上要招待亲戚朋友叫做‘夜坐’)。临走前,妈妈又碎碎的嘱咐了很多,姐弟俩耳朵都听出老茧了,赶紧帮爸妈收拾东西送走了他们。
“噢耶,这回自由了!”爸妈的车子刚驶出去没几步路弟弟就手舞足蹈的欢呼起来。
书瑶也很开心,跑过去和弟弟击了掌,“今天爸妈不在家!”这一定是每个孩子最开心的事了。
当天阳光明媚,弟弟负责骑摩托出去放羊,书瑶则在家里做饭,并且准备好晚上喂羊的饲料。为了让羊吃得好一些,开春多保几个羊羔,她家买来几麻袋黄萝卜,每天要人工用擦菜板把它们擦成丝,再和玉米粒拌再在一起。喂羊之前要装在两侧有绳的小兜里,兜子比羊嘴稍稍大一些,这样正好让羊嘴伸进去,再在它的头上打一个活结,吃完了解下来。书瑶觉得这样天天一个个给羊带上去,吃完再一个个解下来实在太费事了,可妈妈说只有这样才能吃得公平,还能给膘不好的多喂一些,要是倒在槽里喂,膘好的羊反而抢得更多。
第二天一早,太阳周围昏昏暗暗的,太阳的光芒被遮住了,天空只剩下一个桔红色的圆盘。
“姐,你看今天是不是要刮沙尘暴啊,我看,要不就别让羊群出去了?”
“要刮也是下午,一时半会儿风还起不来。这300多只羊留在家里得吃不少草料呢,要不你先赶出去,看见变天再赶回来吧。”
“要不把母羊挑出来留在家里喂吧,这都快下羔了,变天时候赶得太快怕母羊落羔(母羊流产叫‘落羔’)。”
“你还挺心细的,就按你说的。”
十点多,吃完饭后弟弟骑摩托车赶着羊出去了,书瑶则在家里喂八九十只临产的母羊。
日过正午后,天空变成了灰黄的颜色,太阳完全被遮住了,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出了。顶在头上的天,好像渐渐的变得沉重起来,一点点地压下来,就要压在人的头上了。
书瑶一边做饭,一边焦急的等着弟弟,要变天了,书斌怎么还不把羊赶回来,她想出去找他,又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
天一会儿比一会儿更黑,好像传说中的2012就要到了,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枯草满天飞扬,黄尘蒙蒙、混沌一片,简直分辨不出何处是天,何处是地了。书瑶做好饭后也没有心思吃,她焦急地伸长脖子望着窗外。
“姐,风太大了,羊都顺风跑,摩托骑不成,我赶不回羊来!”书斌语无伦次地说着。
“现在羊在哪儿?”
“就在咱家正北面,也就二里路。”
“你留在家里,我去赶,千万别出来,乱跑容易迷路!”
书瑶说完后就一头扎进了大风里,这时雪也下起来了,狂风吹着雪花,吹得她东倒西歪,她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路跑着来到了书斌说的地方,却不见一只羊。书瑶站在原地四处张望,什么都看不清。“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羊肯定是顺着风往东南跑了”,她这样想着,拔腿向东南跑去,跑了三四里,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她心里慢慢的不安起来。
“夜坐”上觥筹交错,老实的父亲经不住几次三番的劝酒,喝得太多了,回到宾馆倒头大睡,不一会儿就起了鼾声。妈妈则看着窗外的天气心神不宁,连市里都这么起了风雪,那牧区的天气就一定更恶劣,想着家里的牲畜和缺少经验的孩子,她熬红了眼睛一夜没合眼。
暴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带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吹起无数沙粒拍打着书瑶的的脸,叫她透不过气来。这暴风雪的呼啸像狼号,又像远处的马嘶,有时又像人们在大难之中的呼救声,让人生出无限恐惧。
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她顾不得冷也顾不得饿,不停地四处张望寻找着,羊始终不见踪影。风小了一些,雪却越下越大,慢慢的漫过了她的鞋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好像有谁把雪花直接从天上倒下来一样。书瑶的双手冻僵了,不停地搓着手,棉鞋里也灌满了雪,被她的体温融化后,袜子和脚都泡在了水里。她觉得周身冰冷,连她的心也结冰了,她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弟弟的建议把羊群留在家里,巨大的失望一层层地包裹着她的心。
“哎—哎—”她在风雪里大叫着,希望羊能听到她的呼唤,回到她的身边,可一切都是徒劳的。她跌坐在地上,仰望着苍穹,雪簌簌地落到她的脸上,和着她的泪水在脸上冻成了冰。看来羊一定会丢了,想着家里的生计,书瑶心如刀割,她从没像现在这样绝望过,仿佛死神就在前方向她招手,抓走了她家的羊,而她,正慢慢地向他靠近。
她在雪地里走了很久,雪已经漫过了她的裤脚,她的全身慢慢的变得僵硬起来。这该死的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天完全黑了,她还在不停地走着,停下来更冷!她明明知道即使羊就在眼前,也根本无法分辨哪里是羊哪里是雪地,可她就是不死心,她宁愿这雪就这样把她埋掉,好让她挣脱这无边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