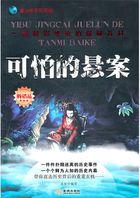七日假期在从乐山回来的第一天,变得不再是假期。
拖着疲惫的身体还在睡梦中挣扎,就听到爸爸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拳头很大,敲得整个屋子都是防盗门上噼里啪啦的声音,我穿着大嘴猴睡衣打开房门,右手还不停地擦拭着眼睛上的眼屎,“怎么啦?”语气里的不满情绪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你舅爷去世了,快,跟我走。”
我愣了三秒钟,转身回屋里脱下大嘴猴睡衣换上一身粉色Nike卫衣,连内衣都忘了穿,匆匆下了楼。
舅爷是我奶奶最小的弟弟,比奶奶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爸爸大不了几岁。舅爷家离我们仅五分钟的路程,是新建的安置房,我常记得爸爸和大伯二伯在他老房子里喝酒聊天醉醺醺的模样,却浑然不知他们已经搬了新房并且离我们那么近。
远远地就看到马路边搭着的蓝色帐篷,一排排花圈整齐地搁置在帐篷入口处,随着入口进去,是一张黑白照,照片里是舅爷精神的脸还带有些许胡渣。奶奶和二姑婆,大舅爷他们坐在大圆桌上面围成了一桌,大姨,三姨,大伯,二伯,爸爸,围成了另一桌。我站在奶奶旁边因为忘了穿内衣把双手死死地抱在胸前。
哀乐一响,奶奶的眼圈湿润了。我伸出手,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来安慰她,甚至连悬在半空的双手也开始无处安放。
葬礼办得很仓促,从哀乐花圈到没了声响,仅仅两日。舅爷是祖母最小的孩子,而祖母已经年近九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奶奶,姑婆,大舅爷他们感同就好,实在不愿惊扰了老人家。
葬礼第二天,舅爷的儿子说他要去开死亡证明,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死亡证明”四个字,望着他匆匆的背影,我竟难过得为了不知如何帮他而自责。
那日回去之后,爸爸坐在暗淡的灯光下,看着我认真地说,“我在家里存了一点好酒,如果活到五十岁,我就喝了它。”说完就笑了,语气失去了控制。我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就这么慢慢地,慢慢地染上了一圈红晕,仿佛那一刻,又看了他笔直地站在葬礼上直到结束的悲伤模样。
“乱讲,我不理你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身上,我嘟着嘴假装生气地跑开了。
房间里,我不敢开灯,我怕爸爸知道我的难过和不安,于是将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里,那一刻,我将自己藏在黑暗里。人生中第一次,我开始害怕失去,也开始意识到生命的脆弱。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
窗外一片朦胧,雨丝细细地飘散着,我睡到正午才懒懒地爬起来推开房门,眼睛又红又肿,卧室里的手机声让我又转了进去,电话那头是哥哥的声音。舅爷的逝去都让我忘了,明天是哥哥的婚礼。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换了身衣服下了楼,哥哥的车已经停在楼下许久。
我们要去接嫂子了。
嫂子很瘦,皮肤黝黑得像少数民族姑娘,印象中她从来不穿高跟鞋,个高的她哪怕穿平底鞋站在哥哥旁边都不比哥哥矮,总板着一张脸,对所有人。
关于我的准嫂子,我并没有太多好感。只记得某日周末因为起晚了要去赴同学的约匆匆赶上公交车在嘈杂的公交车上遇见她,目光相交的一霎间,她将头扭到了一旁,我投了一块钱零钱,径直走向了公交后门。从那以后,我认定她就是个小气的女人,那份车上的固执直至今日,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我咳嗽着,却不是因为生病。移了移座位,使自己更靠近车窗。车子在我面前的玻璃上像电影似的播放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没有了点点雨珠。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下午,可天空仍灰的分不出时辰来。
嫂子的老家在一个个种着叫不出名字花草的山丘下,晚上带我们吃了烧烤,便安顿在镇上的一个小旅馆。
那场小旅馆中发生的故事,真是好笑。同行的还有杰哥和他老婆,准嫂子的朋友。我和杰嫂子睡,杰哥和哥哥睡,准嫂子和她朋友睡,事情本该这样安排。准嫂子耍着小孩脾气非要跟哥哥睡,硬要把我安排和她那个素不相识的朋友睡,我气得咬紧牙齿,腮帮上的咬肌肉因为用力过猛的原因鼓成好大一块,想也知道有多难看。真想直接甩过去一句话,你就那么心急吗。忍了忍,把它咽了下去。低头,“我不想跟陌生人睡。”
哥哥走过来,安抚着我,拉着嫂子进了一间房。
喂,没良心的哥哥,我可是你娘家人!
事实证明,哥哥并非没良心。最后的结果,我和杰嫂子睡,杰哥一个人睡,准嫂子朋友一个人睡,嫂子如愿拖着哥哥进了“洞房”。
那天在小旅馆里,杰嫂子和我聊起了她和杰哥的故事,虽然夜黑的看不清面容,我却仿佛能清晰得感知她脸上的笑容。
“你男朋友呢?”杰嫂子翻了个身,问我。
已经凌晨一点,本来睡意朦胧的神经慢慢地提起了精神。
我的男朋友,我的老大。
这些天因为写字的原因常常沉浸在和枭的回忆中,却始终忘了,这段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平,我的老大。
认识平是我的幸运,很久很久之后我用一段很感伤的话来祭奠这段感情,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身,仰起头,倒吞着咸咸的眼泪。我说,我从不后悔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负在你身上。说完眼泪像是打开的水闸,哗哗地往下流,流进嘴里,的确是咸的。
是负人的负,不是付出的付。
认识老大是在一个游乐园,我的第一家实习公司。
初进游乐园面试的时候,我才不到十七岁。只因陪远道而来的朋友来过一次,然后指着游乐园那个五颜六色因为恐高只敢远远望着的摩天轮说,这里好多快乐,我也要来这里。于是,朋友走的第二天,我就单枪匹马地闯进来了。
闯进游乐园第一个遇见的人是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大叔,问的第一句话是,“叔叔,你们这里招人吗?”声音嫩嫩的,却一点也不胆怯。只记得保安大叔给我指了个方向,我就朝那个方向去了,很长一段路,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人力资源部。
实习近半年的时间,我和老大没有半点交集,只知道运营部八个设备长中有一个戴着眼镜个子高高又斯斯文文的。直到他调到我们设备。
部门是按设备分组,我们组一共八个人,负责大摆锤,激流勇进两个大设备,一到夏天,激流勇进总是排着满满的长队,人气爆棚,而那几个月,我们组的荷包也总比其他设备要鼓一些。
平调来的第一天,他们都老大老大地叫着,于是我也跟着叫。
那些日子是我青春隧道里最快乐的时光,我总是喜欢早早地来到乐园,换上卡通工作服,然后拿着给游客互动时用的麦克风,在操作间座椅上坐着翘个二郎腿舒舒服服地唱歌,开始上客的时候,又开始激情四射地大吼,“准备好了吗,马上就来到我们的最高点,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我常常透过设备台前的大玻璃看他们坐在设备上各种复杂的声音一个人莫名地大笑,那种感觉,就像小朋友一直在吃糖一般快乐。
第一次注意到老大是在激流勇进的操作台。那一天,因为一些繁琐的小事影响了我一整天,在给游客压安全杠的时候因为手使不出劲就直接用脚踩了下去,力气很大。游客疼得直接发火骂人,骂得很难听。
“安全杠不压紧坐什么设备!你要不愿意压你早说,只要不怕死!你要敢空着坐上去我就敢空着给你开!”我抬高音调,凶着表情吼过去,随后老大用双手环着推进了操作间。
透过操作间玻璃,我看到老大头上大滴的汗水和讨好的笑容,而那个游客正歇斯底里地指着操作间里的我。
至始至终,他没有责备我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