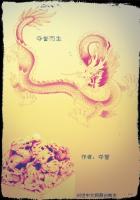痛苦是快乐的遗产。
这世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的假话,“我能体会到你的痛苦”是最假的一句。甚至你能“想象”到我的痛苦都是不可能的。
“你能吗?”
我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质问着吊丧者,她吃惊地不知所措。
四周的人用怜悯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大吼大叫,大哭大闹。半辈子的得体如今全部粉碎。他们并不介意,因为就在三小时前,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田歌。
他二十二岁,即将大学毕业。今天早上从家里开车去学校,明明白白亲口告诉我下周二再回家,今天却死在了回家的高速公路上。
交警队告诉我,田歌驾驶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因意外撞到了高速路护栏,头部受到重创,当场死亡。这是场意外。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出事时,车上还有一个人,叫蒙锦。他是田歌的大学舍友,他坐在副驾驶,除了有些脑震荡外,并无大碍。
田歌早上刚离开家,他为什么下午又开车回来?他每次回家总会给我打电话,今天为什么没有打?这些问题在交警看来无关乎车祸本身,但我是孩子他妈,我更了解我的儿子,这件事绝对有隐情。
我问蒙锦,田歌和他一起回县城干什么。他竟然说也不清楚。如果不清楚,他怎么会坐在车上?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恐惧,他的内心肯定知道什么。
三天后,田歌的葬礼,我出奇的平静。我打量着葬礼的每一个人。大哥、大嫂他们张罗着葬礼;可慧、可心、可勇这三个外甥女和外甥陪着我;我的前夫田军十年未见,如今也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惹我生厌……田歌的同学们,我的同事们,家里的亲戚们都小声交谈着,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是他们的嘴都在动。
我曾要求警察局彻查这次事故,但他们给我的回复是交通意外。他们是指望不上了,这件事要想弄明白,还得靠我自己。
我的目光落在了人群中蒙锦身上,他的头还裹着纱布。他眼角的余光瞟到了我,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转脸背过我去。
我不能打草惊蛇。
一个离异的中年女教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葬礼过后,依然去菜市场买菜,依然上班,依然过着日子。这在外人看来,认为我冷静得出奇。大哥、大嫂还没从田歌的意外中缓过来,我这个亲生母亲都已经开始过起了像之前一样的生活。
我冷静的表现让大哥更放心我,便让可心跟我同住。
大哥大嫂在农村,条件困难。可心是大哥的二女儿,比田歌小一岁。初中高中六年都是跟我一块住,也是我供她上学,跟亲闺女差不多。
可心话少,文静内敛。她跟我住在一起,我们也很少说话。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我常常出神,她也不打扰我,只是默默陪着我,估计是怕我寻短见。她哪里知道,一个做母亲的怎么允许别人用一个意外来解释儿子的死亡。我就算死,也得弄清楚这个“意外”。
田歌去世头七,我开始行动起来。我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在这个小县城里,各行各业都有我的学生,我首先想到的,也是我迫切要看到的,就是高速路上的监控。
我想到了一个学生,杨帅方。他在警察局。
我把他约了出来。他知道了田歌的事。
“王老师,我也听说了。您节哀顺变吧!”他刚从警校毕业没两年,还带着股子学生气。
我开门见山说:“老师今天把你约出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他有些意外,忙问:“您说,啥事?”
“我能不能查看一下5月19日西南段高速路录像?我儿子就是在那段高速路上出的事。”
杨帅方正了正头上戴的警帽,他的眼睛不自觉睁大了,问:“您要看这个干什么?”
我喝了一口水,说道:“有些事,我必须弄清楚。”
“老师,这个事不是特别好办。如果是涉及违法的案件,只要有相关的证明就可以向交警提出申请。但是这是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在定案之前,交警队、警察局都查看录像了,不会有问题的。”
“我没有看到!我必须得清楚我儿子到底是怎么没的!”
“老师,您别激动!”杨帅方慌忙抽出了纸巾,递给了我。我绷紧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压抑平复了一下情绪,擦了擦眼角,接着说:“很多人都说是意外,我也不是不相信警察局和交警队,但我作为死者的家属,我想我有权利知道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田歌十八岁就考下了驾驶证,他开车已经满三年了,那条高速公路来来回回走过上百次。为什么这次意外撞到护栏?也没有雾,也没下雨,他也不是酒驾。我想知道答案!”
杨帅方沉默了片刻,试探性地问:“老师,我不建议您看,我怕您看了受不了。车祸现场,心理承受弱的人,受不了这个刺激。”
“你放心!我肯定没问题。你帮帮老师,好吗?怎么申请?需要提供什么?我都可以准备。”
杨帅方见我如此坚定,知道是劝不动我,便说:“王老师,这事我尽量帮您办成。我会替您向交通局道路监控室提出申请。您等我消息。”
我回到了家里,可心已经把饭做好了。我简单吃了两口,便进了田歌的卧室,整理他所有的物品。我翻看田歌的每一个裤兜口袋。
可心走了进来,握住了我的手,说:“姑妈,您别翻了,表哥的这摞衣服,您已经翻找三遍了。”
我没理她,自顾自地淌起泪来。我实在没有忍住,眼泪啪嗒啪嗒滴落在田歌的床头,可心抱住了我,她哭着说:“表兄最孝顺,您得好好的,这样表兄才放心啊!”
眼泪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少半分,我哭到全身无力,如没有骨头一样,瘫在了田歌的床上。
在迷迷糊糊中,床似乎变成了船,在河水里荡悠悠。田歌坐在船头,我坐在船尾,我的脚渐渐有了寒意。
水一点一点慢慢地浸湿了我的鞋袜,我感觉船漏了,水在船里蔓延开来,我慌张喊着:“儿子,船漏了。快到妈这来!快点!快到妈这来!”
田歌只是冲着我笑,并不回答我。他站了起来,摇摆着身体,船越来越晃,几乎就要翻了。我大叫着,田歌大笑着。
他头一歪,径直栽倒了水里,他在水面上扑通扑通,喊着救命。我忙伸手去拉他,好不容易拉到了他的一只手。
我仅紧紧攥着他的手,他却一直往下沉,似乎他被水底里的什么东西拖拽着。
我没了力气。突然,我从黑蓝的河水中,隐隐约约看到一张苍白的脸,那张脸似乎很熟悉,又想不起来是谁,他对我诡秘一笑,我瞬时没了一丝气力。田歌的手从我手心脱落了,伴随着翻滚的水花,沉入了幽深的水底。
我猛地坐了起来,浑身颤抖,只感到身上全是寒意,不停地喘着粗气。
灯亮了。
我一回头,猛然间似乎又看到了水底那张苍白的脸,不觉得惊慌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