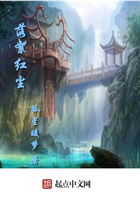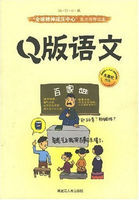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数十年前的血雨腥风、峥嵘年月的印痕,深深地镌刻在那个代人的心上,尽管年月流逝,沧海变迁,但总是挥之不去,如梦随影地伴随他们一生,尤其亲身经历并为之奉献青春热血的先辈们。
“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没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要继续与他们斗争!同志们冲啊……。”说着,小叔公又昏迷了过去。
这是在他清醒时,喊我父亲过去记录遗嘱,当父亲赶去时,弥留中他说的最后一段话,这也是一个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军人,留给后人的最后的一段话,在场的几位军人都流下了热泪。
小时候,总喜欢往小叔公家里跑,尽管要走六七公里的泥路,可总是盼着暑期,能在小叔公家住上几天。
印象中,小叔公很少在家,那时候不懂,只知道他是个大官,偶尔他在家,见了他,胆怯地躲得远远的,尽管他很疼我,因他的威仪着实让人见了胆寒,近一米九魁梧的身材,二道特长的剑眉下一双不怒自威的大眼睛,盯着你看一下,你会觉得瞬间后背发凉。
从小听着他英勇的故事长大,喜欢看那张挂在堂屋墙壁上,镶着玻璃框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的嘉奖令”,内容依稀记得是:‘蔡诚同志,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英勇作战,特此嘉奖’。
在卧室的西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照片,小叔公穿着八路军的军服,腰束武装带,武装带上别着一支手枪,英姿飒爽,正气凛然。
看着这张照片,久久凝望,思绪飞到那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华儿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开始了,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年轻的叔公在哥哥,也就是我爷爷的影响下,兄弟俩人和许许多多优秀中华儿女一起,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保家卫国,奋不顾身地把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热土上。
1938年3月的一天,凄厉的寒风在江北大地上肆虐,枯草蓑蓬,田间一座孤坟上,一只乌鸦发出悚人的鸣叫,侵华日军一个小队,在曹长川田雄二的率领下,由海门进入****,沿途烧杀抢掠。
中午时分,这队张牙舞爪的日军来到了黄仓镇南的兴隆村,又累又饿的日军想进村吃了饭再赶路,川田雄二一招手,翻译官徐志鸿媚笑着跑上前去,凑到川田雄二的面前,哈下腰问:“太君,有何吩咐?”
留着仁丹胡的曹长瞪着凶狠金鱼眼,对徐志鸿说着生硬的中文:“徐桑,你的进村,我们的米西米西,明白?”
徐志鸿立即头像鸡啄米似的回道:“明白明白。”心里却骂道:‘东洋猪,叫我一个人进村,他娘的’。可又不敢多说什么,川田的暴扈他是领教过的,海门伪军小队张三狗,因为一点小事和他顶了一句,结果被川田一刀下去,劈成二半。
徐志鸿是通州人,其父曾任国民政府监察二处副处长,又调任江苏督学。徐家家境殷实,徐父将其送到日本自己曾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芦沟桥事变后回国,经徐父同学、日军驻华派遣军徐州特高课组长山野俊介绍,担任驻南通日军翻译官。
徐志鸿走进村,一阵吠声响起,吓得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有了退缩的念头,转而一想,若是无功而返,必被一顿臭骂,有山野俊做后台,日军下级军士不会为难自己,可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岂不被耻笑?
在路边折了根粗壮树枝壮胆,硬着头皮向村中走去。
二条黑黄杂色犬尾随着他不停狂叫,徐志鸿嘴里骂骂咧咧,走几步停下来,用手里的树枝作势驱赶那二条犬,那犬越是赶它,它就越叫得疯狂。
好不容易挨到几间泥坯墙、茅草顶的房前,只屋里空无一人,桌上碗里还有剩饭。
原来这家人正在吃午饭,一听狗不停狂叫,儿子石财跑到门口一瞧,赶紧喊:“爹,你快来看”,只见村头路边的田埂上,站着十多个日本兵,一个戴着鬼子‘战斗帽’的人正朝这边走来,吓得拉起妻儿绕过草垛,沿东北角小河边上的芦柴丛,向北一路奔逃。
徐志鸿见这人家家中无人,便冲着日本兵喊了几声,那川田雄二手一挥,日本兵端着枪向这摸索着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个戴着钢盔的日本兵枪杆上还挂着一面“膏药”旗。那二只犬放过徐志鸿朝着日本兵吼了起来。
‘汪汪汪’的叫声把川田雄二给激怒了,从腰间掏出手枪‘呯呯’二声枪响,二只狗抽搐着倒在了血泊中,绝望地抬了头,又无力地垂下,眼睛死死地看着那些幸灾乐祸的畜生,好像要记住他们的面容,有朝一日报这血海深仇。
一个穿着黄色翻毛皮鞋的日本兵飞起一脚,重重踢在其中一条狗的背上,那狗痛苦地哼了几声,再也没了声息,那日本兵揣起上了刺刀的枪,一刺刀下去,‘扑滋’一声,正中另一条狗的眼窝,一声惨叫撕人心肺,毫无人性的鬼子兵哈哈哈大笑起来,畜生的凶残融在了这笑声里。
进了那户人家,日本兵在院中支起了锅架,准备生火做饭,那踢狗的鬼子拉开鸡栅的门,从里面捉出二只“格格格”扑腾的母鸡,手中匕首寒光一闪,二个鸡头落地。
三个鬼子进屋翻了会,也实在没有什么,提了一篮子鸡蛋出来。
“徐桑,我们再去别的人家看看。”川田喷着酒气,打着饱嗝对徐志鸿说。
“好好,太君,那我们现在走?”徐志鸿一直看着这些贪婪的鬼子,只是站在一边角落里,慢腾腾吃着一个半生不熟的鸡蛋。
川田战前是个地地道的地痞,在华北战场,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损员严重,日本军部从本土将一些未经训练的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这才使川田雄二这恶魔有了一展他凶残本性的温床。
川田站起身来,对还在吃饭的二个日本兵白了一眼,吼道:“井上、柳夫,你俩守在这,其他人出发。”
天空响起了雷声,在这峭寒还暖的时节打雷,确实少见,几只院角啄食麻雀惊得“叽叽喳喳”飞起,寒风吹过,一道闪电在空中一掠即逝,人间混沌,令上苍变色。
尽尽隔着一条旱沟,日本兵来到施家歧宅,一家四口倦缩在泥灶后瑟瑟发抖,川田狞笑着手一挥,二个日本兵上前把施家歧夫妇拉起,用枪托狠狠地击打他们的头部,殷红的鲜血从他们额头往下流。
二个孩子哭了起来,川田上前左右各拎一个提到场上。
“畜生,放开孩子!”夫妇俩挣扎着要去抱孩子,被日本兵揪住头发摁在地上,动弹不得,好在川田听不懂“畜生”是何意。
“小孩,那人家跑哪里去了?你的明白?”川田摁住哥哥大龙的肩头问。
才九岁的大龙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凶神似的‘东洋人’,摇摇头,其实他确实不知堂弟小石财一家跑哪去了。
川田转头看着小龙,小龙直往哥哥身后躲。
川田忽地抽出东洋刀,嘴里骂了一句:“八嘎”。
二个孩子这时不再害怕,也许他们懂得害怕无济于事,大龙护着弟弟,一股倔劲加上愤怒,小脸涨得红红的,眼中满是怒火,死死睁住川田手中的刀,俨然一副视死如归的凛然神态。
川田冲屋里喊了一句东洋话,二个鬼子把施家歧夫妇拖了出屋来,川田揪住施家歧衣襟问:“你的游击队的干活?”
施家歧一片茫然,不知道眼前这鬼子说的是啥。
“太君问你是不是游击队?”徐志鸿翻译道。
“游击队?游击队干吗的?我不认得。”
徐志鸿将他的话翻译给了川田,那川田一听,哈哈笑了起来,那猫头鹰叫似的笑声,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的带路!”川田用手指指施家歧。
徐志鸿用启海话轻声说:“要想活命就带路到汇龙镇。”
这时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随这小鬼子摆布,能捡条命也是万幸。
二孩子和娘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鬼子掳走,娘把大龙小龙搂在怀里,眼泪簌簌地掉下来。
二个刚才留守的鬼子临走,将茅屋点燃,浓烟升起火焰熊熊,只一会功夫,二间茅房化为灰烬。
“天杀的小鬼子啊,不得好死!”一家三口跑回来一看家没了,顿时捶胸顿足,不知道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鬼子一行大摇大摆向东继续走去,走过一条小桥,路二边地势凹凸不平,一蓬蓬的枯草像是土坎杂乱的头发,一棵棵刺槐树东倒西歪地斜插在坎的下面。
川田雄二放慢了脚步,警觉地四顾了会,又狡佶地让叫柳夫的鬼子押着施家歧走在前面。
突然,听到一声高喝:“打!”顿时枪声大作,路边没有屏障物,加上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站在路中央成了一个个活靶子。
眼看着三个鬼子倒下,川田回过神来,高喊:“还击、还击!”这时,施家歧见鬼子遭到伏击,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一拳重重击在柳夫的下巴,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势一滚,滚到左边的沟壑里。
那柳夫此时也不去管他了,伏在地上,拉动枪栓乱打一气。
“撤退,撤退”川田雄二高喊,再打下去必定全死在这,夺路向西没命地逃窜。
原来,这是****抗日自卫队在得知鬼子进犯,在这伏击了小鬼子,无意中救了施家歧的命。
此战毙敌四人,缴获枪支四支,手雷十多个,大灭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从日军侵占南通开始,****几支地方武装自发地合并在一起,加上民兵组织,统一指挥,正式成立了——****抗日自卫队,这支有二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自卫队队长戴荣,副队长兼政委龙彪,蔡诚担任二区队队长兼财助(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员,为党筹集资金),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担任财助是个极其危险的工作,随时都会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的危险,但叔公毅然接受了党委派给他的这个艰巨任务。
担任乡长的爷爷家里有面铜锣,一根木棍锤,这是用来发警报用的,一旦乡亲们听到这响亮的锣声,不管白天还是深夜,都会马上找隐避的地方躲起来,很多时候,许多人藏在坟场、沟坑里,那时候人们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不这样,说不定随时也会变成这坟场里面的一员。
从记事起,从没听到爷爷说起过关于他在战争年代的片言只语,好在有许多老人都将他们兄弟俩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寒冬腊月的一天,快要过年了,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冻僵的田野被一层白白的雪覆盖着,一间间低矨的茅草屋顶上,除了雪白,看不到一点杂色。叔公在门口跺了跺脚,轻轻咳了一声,推开爷爷家的门,他不知道爷爷着急找他有什么事。
“你来了,坐吧!”爷爷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吸着他那支永不离手旱烟管,不时地咳上几声。
奶奶坐在炕沿上纳着鞋底,抬起头来瞥了爷爷一眼,忍不住又唠叨了起来:“我说你能不能少抽点?都咳成这样了还抽抽抽,满嘴的烟味太重了,唉!”
叔公看了爷爷一眼,见他不吱声,他知道自己哥哥的脾气,平日里不言不语,不喜欢多说话。
叔公笑着说:“哥,嫂子也是为你好嘛,让你少抽点你就少抽二口。”
“你别听她的,整天磨叽”爷爷又猛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乳白色的烟雾,在小屋里漫延开来,然后将早烟管在小凳板脚上敲了几下,伸出右脚,在敲出来还带有火星的烟丝上踩了几脚,慢慢地站起身来,对叔公说了一句:“进来一下。”
奶奶对他们兄弟俩这种神秘谈话,早已司空见惯,奶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非常清楚党的纪律,不该她知道的,爷爷不会告诉她,她也不会问爷爷。
嘀咕了几句,奶奶下了炕,坐在口门为他们望风,她做惯了这样的工作,每次这个时候,她心里感到特别自豪。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整天不见你人影。”爷爷脸上露出一丝很少有的笑容。
叔公在爷爷面前总笑咪咪的,他尊重兄弟加同志的爷爷,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爷爷就已为党工作,尽管身份是隐蔽的,叔公还是知道他****党员的身份,既敬佩又向往。
听到哥哥问,叔公笑着说:“最近我们自卫队除了训练,还安排到各乡各镇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近海乡就有十三人主动要求参加自卫队,其他乡镇也有。”
爷爷赞喜地点点头,用他惯有的慢语条道:“现在形势很严峻,鬼子正沿京通公路向南通进犯,来势汹汹,以后的工作会更艰苦,万事要小心。”
爷爷又点上了那杆叔公给他从镇江带回来的铜烟杆,吸了一口,抬头望了望眼前这个在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胞弟,裹紧身上的棉祆,继续慢慢地说:“上级有个新任务……。”
叔公一听到任务,马上崩了起来,急急问:“哥,什么任务?”
“你怎么老改不了急脾气呢?”爷爷示意叔公坐下,叔公右手在脸颊上磨蹭二下,笑着坐了下来。
“上级指示我们,物色一个忠诚可靠的同志担任乡财助,这二天我思来想去,觉得你来担任比较合适。守仁也认为你能胜任。”(注:守仁,全名:盛守仁,时任吕四区区长,爷爷的亲表兄弟,全国解放后任南通地区第一任公安局局长)。
叔公严肃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这财助是抛头露的活,要面对形形式式的人,一定要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和说服工作,不能一不对就耍你的火爆脾气!”
叔公哈哈哈笑了起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这个工作。”
叔公的回答在爷爷意料之中,每次安排他任务,从不会露出一点的为难,总会爽快地答应。
“倪家二姐,你来啦?蔡忠道,倪家二姐来了。”奶奶见到还在横路上的同村倪二姐,便高声提醒爷爷,爷爷朝叔公使了个眼色,兄弟俩走了出来。
“哟,蔡诚兄弟也在啊,”倪二姐热情地和小叔公搭讪。
小叔公心里暗道:你这不是废话吗?平时就不太爱搭理她,今天兄弟俩正聊得高兴,被她一来给搅和了,心里自然不痛快,嘴里还是嗯了一声,毕竟乡里乡亲的。
叔公性格刚烈,眼里揉不下半颗沙子,这倪二姐是村里有名的快嘴,喜欢搬弄是非,东家长西家短,只要一进她耳朵,马上全村都知道,可她也有个绝活——说媒。
说媒在那时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媒婆可以将二个素不相识,又从未谋面的人搓合到一起过日子,对方的相貌、习性全然不知,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更甚者,就是偶尔相亲,可以由兄弟、邻居家俊俏的后生替代,等到真正结婚时,才发现对方不是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可此时为时已晚,虽已进了人家的门,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这就是封建社会遗留下的陋俗。
和嫂打了声招呼,小叔公便向区小队所在地——大地主,周国宰宅走去,身后雪地上留一串长长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