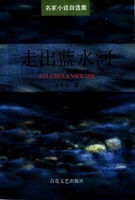我抓住她话里面的一个意思回答她道:“不关你的事。我爸爸的性格,需要经历这些。玲玲姐,你就别急了,我爸爸是个天才,他身边的人,全都要被他弄乱套。你不要怪自己,离我爸爸远一些倒好些。”这话说的那么镇定、肯定,我都觉得自己很像妈妈了,甚至也有妈妈的那种冷淡。是啊妈妈,我现在多么同意你的话。男人总爱傻乎乎地对社会保持乐观,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亲爱的妈妈,现在我觉得我是那么了解你。你也曾苦苦等待。男人有权去操社会,别拦着他。你就等他好了。你不等了,我接着等。自从知道我妈妈在和一个远在英国的男诗友网恋后,我就觉得接替妈妈等待爸爸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了。可是,妈妈,如果我真的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你,你会原谅我吗?
千真万确,妈妈,天才都是没心没肺的,随便你怎么爱他他也不会留意,总觉得全世界才是他的责任。一刹那,我不乏冷酷地决定此后就做个冷眼旁观的人了,只等他走投无路。世界上的他,只有一个我还在爱他,守候他。他应该知道的。我割腕自杀就是想让他知道。只有我,还有一个九十多平方米的一套房等待着他。我已经布置好了他的归宿。画室兼书房,他的所有手稿都收集在其中。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自然会回到我身边。我几乎是赌咒发誓地这样想着。
我也为我的冷酷感到害怕,有时会做起噩梦,梦见等他完全属于我的时候,已被世界折磨致死。
那真是一个令人全身冰凉的梦。他枯瘦苍白的身体是被水运来的。这是因莎士比亚的台词还是因矮子叔叔产生的联想?梦中,他像矮子叔叔一样被人溺毙,只不过之前他已被人剥光,而我,也是全身赤裸的,站在河边用我的怀抱接住了他。我不觉得可怕,只觉得冰冷。一切都是冰冷的。醒来之后--之后所有时间都是醒来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暗藏巨大真相的暗喻。
朱玲玲的判断也许是对的,香港人骗了我爸爸,这的确令人恼恨。可我又想,若是我爸借此彻底了结了心事,也未尝不好。他学生时候会以打架坐牢表达他的情绪,成了企业家,以上千万的钱去释放情绪,也未尝不可。他情感丰富,容易激昂,从来没有改变过。不过,现实地说,这次上千万地花费出去,我爸爸可就真没钱了。大约在他出卖达州地产公司后半年,2004年秋季,爸爸来成都看我。
如果不是想好以什么方式、什么话题和我见面,爸爸是不会来看我的。他必须控制局面,制止我和他之间的尴尬。我自杀的事至今未有解释,他非常害怕听到我说明其中原委。这,我肯定自己是知道的。爸爸来和我见面,只能说爸爸有事要告诉女儿。就是这样的。
他告诉我,他要去上海了,吴叔叔借钱给他,让他开办了一家服装公司。
“栀子,相信爸爸。爸爸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我像小时候那样说:“栀子在任何时候都相信爸爸。”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他心怀内疚,却又发誓,要我相信他能东山再起。相信他,咱们父女俩迟早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可这一天是哪一天呢?在过程中很少有过快乐,却妄谈最终的幸福。再说,他想的幸福也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幸福。我想要的幸福--有时候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的养女,除了融为一体的爱,我没有任何保证。我非常害怕被遗弃。
我完全可以反驳他,或者依照通常这个年龄的少女叛逆性,对他吵闹而发作。可是我没有。每次我都只能傻傻地说,“栀子任何时候都相信爸爸”,好像我和爸爸的关系就像普通正常的父女关系那样,需要这种无聊的保证。
然后他就觉得已经和栀子交代了,就安安心心地去了上海。不久我就开始画画了。画他,反复地画他,其次画画妈妈和矮子叔叔。
画成了就拍照片通过E-mail发给他看。他呢,也亲自动手设计服装了,而且每次都让刘秘书将他设计的服装图样发给我看。他喜欢在白衬衣上加一些小点缀,比如一小朵梅花,一抹墨迹,而这些都是男士的白衬衣。这种略带南宋意味的清新简洁风格的男士衬衣,也表达了他内心某种做人的愿望吧。
关于绘画和服装设计艺术的话题,我和爸爸能聊很久,并从谈话中时常产生重新认识对方的惊喜,那久违的父女间的亲密感觉又回来了。亲密,这是童年记忆,也是我现在退而求其次所急需的。爸爸,我经常欢呼,就像个小孩子,这才是我爸爸啊!而他欣然答应说,是啊,爸爸之前的生活真是太糟糕。
在这些聊天中,我爸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爸爸这次是故意离开重庆的,因为爸爸要和重庆生活一刀两断了。咱们的公司,不请啥设计师,要设计就爸爸自己动手设计。这不是什么做大公司的思路,不过呢,栀子,你该晓得,这才是爸爸想要干的事。爸爸要亲自动手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这样心灵才充实。你妈妈坚持写诗,就是这个原因,她对生活的理解远远超过爸爸了啊。创造性的事充满乐趣,肯定能帮助爸爸改掉些毛病。或者他汇报:爸爸现在不赌,也不吸毒了,连酒都不喝了。只有这样才配做栀子的父亲。他甚至提到一个久远的词,“诗的女儿”,记得么,我的宝贝。
我往往回答他:“爸爸,这可真好!”有一次他说:“栀子,爸爸现在逐渐恢复正常了。栀子呢,栀子是不是也该找个男朋友了?”他这话说得我心里又好笑又甜蜜,好像我们之前是一对经历了苦难恋爱的情侣,之前皆受伤害,之后,还相互体贴对方,巴望对方尽快恢复。这样想下去,似乎很不错,有一定的道理。我对他敷衍地“嗯”了一声,下了个决心,要为爸爸打一辈子单身。
不过在一年后,他的秘书,刘梦新,电话里听起来是个声音很不错的女孩,有一天夜里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栀子,你找一个男朋友吧,不然你爸爸也不敢结婚了。”她这样一说,我还真如梦初醒,爸爸自从和殷蕾离婚,已经七年了,就再没听说与哪个女的有关系。难道真的是因为我?
因为和刘秘书多次通电话,接收邮件,我和她已经很熟悉了。我压住心头狂跳,开玩笑地说:“刘秘书你可管得真宽!我可没拦着我爸爸不让他结婚。”“我--”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发现你爸爸全部心思都在你身上,这对你和他都不能说好耶。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嘛,我劝他好多次,可他就是丢不开。爸爸宠爱孩子也不能宠一辈子吧,况且还是父女。唉,我怎么说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小心翼翼地说:“爸爸老说起我么?”“说到没怎么说。他不多话的呀,不过老走神,老爱玩他的玉佩。玩起玉佩来人家说话他都听不见啦。”“那他一定是想我妈妈了。”“他说玉佩有个名字,叫栀子。”我不再说话,只觉得心里酸楚楚的。就算我爸爸爱我,像我爱他那样爱我,他也不敢啊。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他!
“我说呢这样不好。栀子,你别生气,你的生活不正常,让爸爸老担心。你应该去走走,交交男朋友,有个独立的事情做。你把自己独自关在家里,再是洒脱的父亲也丢不开啊。你爸爸说了,栀子要是不感到幸福,他也快乐不起来的。”她这样说时候,腔调都变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说的其他人是你吧?”她“嗯”了一声,说:“我和你爸爸--栀子,你爸爸不让张扬我和他的事,可是我--我,我喜欢你爸爸。你爸爸其实也蛮喜欢我的。
我和他做着很有意思的服装工作室,他负责设计,我负责推广,生意不大,可是非常有意思。我想一直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可以的。栀子,你明白吗?”我想我懂了,其实我只是一个哭闹着要爸爸爱的小女孩,其他一无是处。
又下雨了。我都有些厌烦这样的雨了,厌烦这样迷茫粘连的情绪了。为什么雨不是一滴、两滴,不是每次都很确切击响一样东西的雨呢?
我们听了好几次雨滴击打车顶的声音,然后,来了一股风,将竹枝上的水珠全都噼里啪啦地摔落下来。龙崽哈哈一笑,一放刹车,我们的汽车就从竹林那里滑开了。
“栀子姐,你知道绝境是什么么?”我摇摇头说:“我知道绝望是什么感觉,可是你说的绝境,我想的话,还有美不胜收、无法言喻、至死方休的意思吧?”“美不胜收,无法言喻,至死方休,说得好!之前我也揣摩出一个意思。”他放慢了车速,观察前面。前面大约四五里的半空,阴郁得发黑。显然又在下雨了,而且正在蔓延过来。“如果没有光,都被雨雾粘成一片,显然不会有绝境了。”“你还没说你的意思呢。”“嗯。我想的是,有些地方,美好得能让你什么都忘记了。事情被忘记了,自我就消失了吧。我想以一种消失的感觉自杀。没有任何意义了,消失了。但美好的感觉就在眼前,醉醉的,就像做梦一样就死了,这种感觉状态就是:在绝境消失。”到了成都,雨还没停。到了我住的地儿,我让龙崽进了我房间。请个男生进门帮忙,按说也没啥特别。不过我真还提醒了自己一句: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让一个男生进我家门。这提醒意味深长,和那年我独自穿过解放碑广场去爸爸宾馆房间的心情很相似。
进门后他捧着茶杯四处转了转,张嘴就说:“你家就是你爸爸的纪念馆。”是那样的。我爸爸的大幅照片、手稿、画架,他用过的各种东西,到处都是。显然我无意仅仅保存物品,而是随时随地在把玩,因此爸爸的东西散落到房间各处。之前我还没想到他留意这个,现在也没想要他留意这个,因此相当尴尬。尤其是卫生间,我赶紧去了卫生间,把爸爸的剃须刀啊啥的藏了起来。
几乎是为了干扰他,我连声要求他帮忙拿出留声机。他割掉胶带,打开纸箱,拿出留声机。正如我小时候看见的那样:它流光溢彩,神气活现。
“放在仓库很久了,灰尘蛮多的,包装之前我狠狠擦了一下。”“它坏掉了么?”“不知道。反正我在咖啡馆打工时没见过用它。”他插上电,放上树脂唱片,没动静,看来是坏掉了。它就像某些记忆,不开口说起,就没声音了。
“不知道哪里有修理的。”“算了,就这样,做个摆设,也挺好的。”然后,我想,然后呢?下一步应该做啥?下一步,我不知道怎么暗示一个男生我对他有意思了?怎么让一个男生心领神会又知晓不能操之过急主动留下来进一步培养感情呢?一时想不明白,我便有些焦躁了。我语气急促地说:“我要洗个澡。”他“哦”了一声,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告辞。我没理他,径直去了浴室。
在浴室里我朝他喊:“冰箱里还有喝的,你自己拿。”我想起这句话,似乎是从殷蕾那儿学来的。那次是她和爸爸在宾馆,她从浴室里朝外也是这样喊的。在那十分绝望的时刻,我甚至想过向殷蕾求助,求殷蕾想办法挽救我爸爸。她不是有办法把爸爸从贵州的牢房救出来么,也许也有能力唤醒我爸爸的理性。但我终究还是没有给殷蕾打电话。一方面觉得我对殷蕾的希望也许过高了,另一方面却是怕她嘲笑。显然,如果当年不是我把她写信的事告诉爸爸,他们就不会离婚,我爸爸也必定不会陷入之前以恶对恶的危险境地。
几乎是习惯成自然,我一进浴室,就变得多愁善感。若干次,我身体里的情绪是复杂难解的,全靠热水和自慰消解掉。今天,情况更加暧昧。我依然情不自禁,但并非完全独处,我似乎在对隔壁的龙崽表现出淫荡无耻的勾引?他真很可爱呢,而且,也很孤僻,就像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天才呢。我不知道他做一个男朋友会怎样。我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栀子姐,你像个姐姐。“姐姐”,我自己喊了自己一声,就把手搭在自己的乳房上,它的确沉甸甸的。还有臀部,也翘翘的,我情不自禁地以无名指在自己后腰沿着弧线划了一下。
羞臊出现时,你总是经历克制的。是,你并非在克制性欲,而是克制羞臊,而这反而令你完全失火,整个身体都泛着红晕。望着门后的镜子,爸爸,我真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呢。
等我费尽周章穿戴完毕走出浴室,见龙崽已移到阳台边画架跟前,遮光布已揭开了,他似已看了一阵,正因什么联想而发呆。看到他,我反而镇静多了。他就是他,而不是我需要的那个想象,也不是爸爸要求的那个女婿。
他问我:“这是谁?”
“矮子叔叔。”
他叫了一声:“朱矮子!”我点头。“他的红皮鞋可真滑稽!”矮子叔叔爱穿鲜艳皮鞋,尤其有双大红的特别耀眼。画上我又略有夸张,将皮鞋画得又长又尖,皮鞋头部向上卷曲。这也是不由自主的行为,小时候我就将他画成欢乐无比的侏儒,皮鞋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配合皮鞋的,则是他两手拉扯脸皮做出的伸舌鬼脸。
“这画传达出很恐怖的感觉。”龙崽认认真真地说。“啊!”我吃了一惊。我从不觉矮子叔叔可怕,也不曾按可怕的感觉描绘矮子叔叔留给我的印象。“你觉得这张画很恐怖?”他点点头,说:“就像是蝙蝠侠里面的邪恶小丑,冷酷无情地将全世界当玩具。”我沉下脸。他竟如此评价我心中的矮子叔叔!之前我还挖空心思想对你好呢,这一想,我真生气了。我一把将遮光布搭在画上,对他说:“不可理喻!”他一脸错愕。
我说:“矮子叔叔不邪恶,也不可怕。”他忙解释道:“我知道,你讲过的。我只是说你这幅画。”“你和全世界的蠢货一样不了解他,你们都把他当坏人!”“不是的,栀子姐,我只是说你画的画。”我朝他喊:“我的画咋恐怖啦!”我已是吵架了,他默然无语。
看起来他并不想改口,甚至不想假装认错挽回这僵局。我气极道:“蠢货!你走!快走!”他一脸张皇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