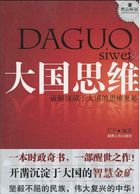1872年1月10日,达尔文校完了他的《物类由来》第六版的稿子。这部思想大革命的杰作,已出版了十三年了。他的《人类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也出版了一年了。《物类由来》出版以后,欧美的学术界都受了一个大震动。十二年的激烈争论,渐渐的把上帝创造的物种由来论打倒了,故赫胥黎(Huxley,1825—1895年)在1871年曾说,“在十二年中,《物类由来》在生物学上做到了一种完全的革命,就同牛顿的天文学上做到的革命一样”。但当时的生物学者及一般学者虽然承认了物种的演化,还有许多人不肯承认人类也是由別的物类演化出来的。人类由来的主旨只是老实指出人类也是从猴类演化出来的。这部书居然销售很广,而且很快:第一年就销了二千五百部。这时候,德国的赫克尔(Haeckel)也在他的《Naturliche Schopfungs Geschichte》(演化论与存疑主义)里极力主张同样的学说。当日关于这个问题——物类的演化——的争论,乃是学术史上第一场大战争。十年之后(1882年),达尔文死时,英国人把他葬在卫司敏德大寺里,与牛顿并列,这可见演化论当日的胜利了。
1872年的六版的《物类由来》,乃是最后修正本。达尔文在这一版的424页里,加了几句话:
前面的几段,以及別处,有几句话,隐隐的说自然学者相信物类是分別创造的。很有人说我这几句话不该说。但我不曾刪去他们,因为他们的保存可以记载一个过去时代的事实。当此书初版时,普通的信仰确是如此的。现在情形变了,差不多个个自然学者都承认演化的大原则了。(《达尔文传》二,三三二)
当1859年《物种由来》初出时,赫胥黎在《泰晤士报》上作了一篇有力的书评,最末的一节说:
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虚空的一样[“自然最怕虚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乃是谚语]。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个法学者搜求例案一样。他提出的原则,都可以用观察与实验来证明的。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网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那么,这条桥可以使我渡过许多知识界的陷坑;可以引我们到一个所在,那个所在没有那些虽娇艳动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作最后之因的——设下的陷人坑。古代寓言中说一个老人最后吩咐他的儿子的话是:“我的儿子,你们在这葡萄园中掘吧。”他们依着老人的话,把园子都掘遍了;他们虽不曾寻着窖藏的金,却把园地锄遍了,所以那年的葡萄大熟,他们也发财了。(《赫胥黎论文》,二,110页。)
这一段话最会形容达尔文的真精神。他在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后之因”的方法,使我们从实证的方面去解决生物界的根本问题。
达尔文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的学说在这五十年里的逐渐证实与修正——这都是五十年的科学史上的材料,我不必在这里详说了。我现在单说他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
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中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他的几部书都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一个大原则。在哲学史上,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单只那书名——《物类由来》——把“类”和“由来”连在一块,便是革命的表示。因为自古以来,哲学家总以为“类”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由来”了。例如一粒橡子,渐渐生芽发根,不久满一尺了,不久成小橡树了,不久成大橡树了。这虽是很大的变化,但变来变去还只是一株橡树。橡子不会变成鸭脚树,也不会变成枇杷树。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还如此。这个变而不变之中,好像有一条规定的路线,好像有一个前定的范围,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法式。这个法式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Eidos),平常译作“法”。中古的经院学者译作“斯比西斯”(Species),正译为“类”(关于“法”与“类”的关系,读者可参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206页)。这个变而不变的“类”的观念,成为欧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观念。学者不去研究变的现象,却去寻现象背后的那个不变的性。那变的,特殊的,个体的,都受人的轻视;哲学家很骄傲地说:“那不过是经验,算不得知识。”真知识须求那不变的法,求那统举的类,求那最后的因(亚里士多德的“法”即是最后之因)。
16、17世纪以来,物理的科学进步了,欧洲学术界渐渐的知道注重个体的事实与变迁的现象。三百年的科学进步,居然给我们一个动的变的宇宙观了。但关于生物、心理、政治的方面;仍然是“类不变”的观念独占优胜。偶然有一两个特別见识的人,如拉马克(Lamarck)之流,又都不能彻底。达尔文同时的地质学者、动物学者、植物学者,都不曾打破“类不变”的观念。最大的地质学家莱尔(Lyell)——达尔文的至好朋友,——何尝不知道大地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物?但他们总以为每一个地质的时代的末期必有一个大毀坏,把一切生物都扫去;到第二个时代里,另有许多新物类创造出来。他们始终打不破那传统的观念。
达尔文不但证明“类”是变的,而且指出“类”所以变的道理。这个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有几种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观念。如果一切生物全靠着时时变异和淘汰不适于生存竞争的变异,方才能适应环境,那就用不着一个有意志的主宰来计划规定了。况且生存的竞争是很惨酷的;若有一个有意志的主宰,何以生物界还有这种惨剧呢?当日植物学大家格雷(Asa Gray)始终坚持主宰的观念。达尔文曾答他道:
我看见了一只鸟,心想吃它,就开枪把它杀了:这是我有意做的事。一个无罪的人站在树下,触电而死,难道你相信那是上帝有意杀了他吗?有许多人竟能相信;我不能信,故不信。如果你相信这个,我再问你:当一只燕子吞了一个小虫,难道那也是上帝命定那只燕子应该在那时候吞下那个小虫吗?我相信那触电的人和那被吞的小虫是同类的案子。如果那人和那虫的死不是有意注定的,为什么我们偏要相信他们的“类”的出生是有意的呢?(《达尔文传》第一册,284页。)
我们读惯了《老子》“天地不仁”的话,《列子》鱼鸟之喻,王充的自然论——两千年来,把这种议论只当耳边风,故不觉得达尔文的议论的重要。但在那两千年的基督教威权底下,这种议论确是革命的议论;何况他还指出无数科学的事实做证据呢?
但是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Agnosticism)。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1860年9月,赫胥黎最钟爱的儿子死了,他的朋友金斯利(Charles Kinsley)写信来安慰他,信上提到人生的归宿与灵魂的不朽两个大问题。金斯利是英国文学家,很注意社会的改良,他的人格是极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地答了他一封几千字的信。(《赫胥黎传》,一,233~239页)这信是存疑主义的正式宣言,我们摘译几段如下:
灵魂不朽之说,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我拿不出什么理由来信仰他,但是我也没有法子可以否认他……我相信別的东西时,总要有证据;你若能给我同等的证据,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的话。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学上“质力不灭”的原则来,灵魂的不灭了也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我们既知道一块石头的落地含有多少奇妙的道理,决不会因为一个学说有点奇异就不相信他。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中说出和心中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种举动走的。这个宇宙,是到处一样的;如果我遇着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用比喻或猜想来同我谈,是没有用的,我若说,“我相信某条数学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够不上这样信仰的,不配做我的生命和希望的根据。
……科学好像教训我“坐在事实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拋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谦卑的跟着‘自然’走,无论他带你往什么危险地方去:若不如此,你决不会学到什么。”自从我决心冒险实行他的教训以来,我方才觉得心中知足与安静了……我很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要叫我作“无神主义者”(Atheist),或他种不好听的名字。照现在的法律,如果一个最下等的毛贼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诉是无效的(1869年以前,无神主义者的宣誓是无法律上的效用的)。但是我不得不如此。人家可以叫我种种名字,但总不能叫我“说谎的人”。
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叫作“存疑主义”的。对于宗教上的种种问题持这种态度的,就叫作“存疑论者”(Agnostic)。达尔文晚年也自称为“存疑论者”。他说:
科学与基督无关,不过科学研究的习惯使人对于承认证据一层格外慎重罢了,我自己是不信有什么“默示”(Revelation)的。至于死后灵魂是否存在,只好各人自己从那些矛盾而且空泛的种种猜想里去下一个判断了。(《达尔文传》,一,277页)
他又说:
我不能在这些深奧的问题上面贡献一点光明。万物缘起的奇秘是我们不能解决的。我个人只好自居于存疑论者了。(同书,一,282页)
这种存疑的态度,五十年来,影响于无数的人。当我们这五十年开幕时,“存疑主义”还是一个新名词;到了1888年至1889年,还有许多卫道的宗教家作论攻击这种破坏宗教的邪说,所以赫胥黎不能不正式答辩他们。他那年做了四篇关于存疑主义的大文章:
(1)《论存疑主义》;
(2)《再论存疑主义》;
(3)《存疑主义与基督教》;
(4)《关于灵异事迹的证据的价值》。
此外,他还有许多批评基督教的文字,后来编成两厚册,一册名为《科学与希伯来传说》,一册名为《科学与基督教传说》(《赫胥黎论文》,卷四,卷五)。这些文章在当日思想界很有廓清摧陷的大功劳。基督教当16、17世纪时,势焰还大,故能用威力压迫当日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受了刑罚之后,笛卡儿(Descartes)就赶紧把他自己的《天论》毀了。从此以后,科学家往往避开宗教,不敢同他直接冲突。他们说,科学的对象是物质,宗教的对象是精神,这两个世界是不相侵犯的。三百年的科学家忍气吞声地“敬宗教而远之”,所以宗教也不十分侵犯科学的发展。但是到了达尔文出来,演进的宇宙观首先和上帝创造的宇宙观起了一个大冲突,于是三百年来不相侵犯的两国就不能不宣战了。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来的证据,三十年搜集的科学证据,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传说!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遂使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因为达尔文身体多病,不喜欢纷争),从战场上的经验中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地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叫人们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19世纪前半的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一变而为19纪末年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了。
(收入1930年12月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