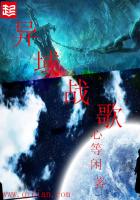同样阴沉的夜,墨色夜空似乎下一刻就要倾倒下大雨来。夜幕下是漆黑一片的春神塞,没有强者交手,也没有破开的城门。长夜无声,唯有秋风。如果是夏夜,徐林肯定挨不了这种悸动,那颗心脏里的种子半天就伸探出了根芽,慢慢挤压着心脏壁。
徐林翻到最后一页音标,嘴巴却发不出声音,只能预想着读音,将音标压在喉咙里默念一遍。心脏的躁动似乎蔓延到了全身,连骨缝间都似乎被激地错了位,徐林感觉自己快疯了。一时间,奇异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徐林不自觉地留着泪,嘴角却咧得极大,状若疯癫。
苦了那么久,通彻却在一瞬间,徐林一眨眼收拢心神,只感觉心脏处流转着一股暖流,慢慢呵护着这块维持全身血脉运行的肉球。成了?!徐林不敢置信地坐起身来,感受着慢慢引导这股十分薄弱的真气。牵一发而动全身,意念似乎与徐林设想相违背,那股环绕的真气极快地流窜于左手,顺势发了出去。
哈!徐林只有一瞬间的反应时间,匆匆将手抬起,气劲擦了窗户下沿,飞出一块木屑。徐林低喝一声,无力地倒了回去。这一天瘫的次数可比以前十几年都多。这次仰躺在床,徐林是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了,挥霍完全身的一击竟只有这点威力,徐林不免有些失望。
眼皮开合,徐林渐渐感觉眼皮上压着千金之重,每次睁开都十分艰难。也顾不得窗户没关,力竭气乏的徐林再未睁开眼睛,沉沉睡去。耳畔却传来一阵破空声,接着是什么重物磕碰床头的声音,再接着一个重物就猛然压在了徐林腹部。未等徐林睁眼,眼前彻底黑了,他昏了过去…
秋夜,树枝上仰躺着一个受伤的人,倚靠着树干低声喘息着。若是知道范哲西死讯,埃文就会发现他与范哲西当时情景是如此相似,除了埃文背后没有一个想让他当弃子的阿道夫。仔细瞧会发现他身上不止大腿洞穿,更是鼻青脸肿,好不凄惨。骨马当时载着埃文狂奔进林子,伸手不见五指的四周加之恍恍惚惚的神志,埃文一个没注意就驾着骨马撞上了树干。
埃文微微喘息,艰难地拖着大腿,挪了个身位。他始终不敢毕业,惶恐地警觉着四周。恐惧源于未知,周围鲜有生物,就连虫豸也也很少出现在埃文的精神力探测范围内。死灵魔法源于将死生物被剥夺的活力,并不是有骨头就可以释放。所以埃文需要活物,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他就如同被戳瞎了双目,精神力感知的距离不过五米,死亡如影随形。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一路毁坏了不知多少民房,殃及多少人家。全城都颤抖雌伏,等待着战斗的结束。在城内巨大声响过去许久后,战栗如抽风的艾丁侯爵才在仆人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几对卫兵聚在一起,瞧瞧接近主街道。长街如同刚被巨人蹂躏一般,两侧房屋尽毁,地上全身散落的断骨还有血腥的肉糜。沿街人家里慢慢随着台阶渗出血液,一滴滴随着沿着台阶下汇聚成小溪,汇聚成见到这一幕的众多卫兵们最可怕的噩梦。
恩佐舍开骨山,兀自前往埃文所在。埃文按精神力应该算得上魔导士,但似乎徒有境界,却缺战斗经验。死灵巫师战斗风格诡异阴险,随法师单独战斗都要损色些,但不至于如此不堪。恩佐仔细回忆着是否在大陆上听闻过这号人物,但没人对得上号。这人应该蛰伏很久了!那为什么现在会出来?恩佐猜测应该与前几日遇见的范哲西有关,但太过牵强,联系不足,只得悄悄靠近了埃文。他隐于一颗树下,静静坐了下来,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仿佛稳坐钓鱼台。
夜深,酒馆里还点着橘黄色的小油灯,暖意熏红了布莱尔的脸,大汉埂着脖子使劲拽住葛文。葛文也是微醺,急忙撇开斗圣的大手,付了酒钱,背过身去无奈笑笑。大汉撇撇嘴,大声吼道:“没意思,你还是不是男人,喝酒都这么不痛快。”
葛文扯扯嘴角说道:“斗圣大人,在下明日还要尽早启程回国,实在不宜多久,我付够酒钱了,您随意吧。”说罢,忙不迭地闪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嗳…”布莱尔站起身来,打了个酒嗝,却没拦下葛文,于是大汉闷闷地坐了回去,一杯接着一杯。在这萧索的夜里,阿黛尔与佐伊一样在房间里冥想。突然她心头闪过一丝心悸,阿黛尔蹙着眉毛,葇荑变幻了个手势,却还是有丝不安。被单独至于一间的独角兽,突然抬起头来,担忧地望了望阿黛尔的房间,蓄满威能的长角流动着莹莹光彩,仿佛裹上了银白色的丝绸。半晌,它低回了头,似有似无地一声叹息,让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圣洁的晶莹。
长夜终将过去。
徐林先是用了三层力气睁开眼,然后花了五层力气昂起脑袋,瞧着压在他腹部害他差点喘不过气来的那具胴体,然后就再无作为。徐林顺着身下看去,只见一件黑袍,兜帽两边有些小突起,裹住脑袋顺便也正好遮挡了徐林的视线。但腹部隔着几层衣服传来的紧滑质感,和空气弥漫的幽香都让徐林揣测这会是个怎样的可人。
肚皮上的可人幽幽醒来,反应却比徐林快了许多,他刚以手肘撑着,半直起身来,就与对方四目相对上了。对面是个穿着清凉的美人,上身皮甲只裹着胸部,下半身也是露着大腿,精致而不夸张的身材,迸发着清新可爱的活力。但她腹部却被几圈绷带紧紧缠住,绷带染红了一片,应该是腹部受创。一张隐在兜帽里的瓜子小脸,樱桃小嘴,直挺小巧的琼鼻,肤色白皙如同美玉,但一双美眸却泛着杀意。略过眉毛,徐林吃惊地瞧着兜帽那两处突起,对方耳朵并不在脸旁,而是在脑袋上,是一对十分可爱的折耳。
猫女?!
肆无忌惮的视线早就惹怒了对方,一股香气扑鼻,猫女抽出腰间小刀,俯身架在了徐林脖颈上,低声道:“别叫,把钱拿出来。”软绵绵的声音让徐林激不起敌意,脖子上的锋利却迫在眉睫。
“在...在那个包里。”没多想,徐林便缴械投降了,“能不能给我留点。”
猫女回头给了他一个鄙夷的眼神,目光闪烁似乎有些动摇。她迅速抽身挑起了那个包裹打开翻看。里面是恩佐留给徐林路费还有地图,猫女捡走大部分,只留了五枚,然后匆匆攀出窗户。现在是早晨,人流还不多,琳达灵活地攀到了房顶。她深吸一口气,恼怒地想起昨日情形:本来受伤严重,还强行拖着日夜遁逃,昨夜到达春神塞时,路经旅馆看见徐林大开的窗户便想跳进去,制服房客稍作休息。结果跃进来时后力不济,拌到了床头和徐林昏迷到一块去了。
一番动作扯着伤口,琳达强忍着疼痛,俯着身子沿着屋顶往南去了。她好恨,恨自己不敢回头,父母的惨烈死相还历历在目,她的背后似乎恶魔的身影始终相随。
那么恶魔在哪?
埃文被参差的阳光照醒,随机是一股股痛处涌上心头。他轻嘶一口气,挣扎着直起身来,茫然地瞧着四周。埃文能吸收树木的活力,但单独一棵树木只是杯水车薪,若是吸的多了在林子里却太过显眼。埃文知道恩佐还在追捕他,死灵巫师是过街老鼠,但在埃文看来,这是因为世人害怕,他们太过畏惧死亡。埃文不怕死,但他还有事要做,他现在还不能死。
埃文伴着簌簌落叶跳了下来,一瘸一拐地往西去了。昨夜刚出城门就甩开恩佐显得极为不正常。当时只顾逃命,埃文还未及细想,现在看来必是另有所图。但无论如何,只要让他找到一所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胜负之数就还未可知!
就在埃文自以为尚有胜算时,恩佐紧随其后,如同一条毒蛇,悄然追踪着被注射过毒液的猎物,静静候着他死去。
窗外的人声逐渐变大,徐林僵硬地坐了起来,感受着心脏旁环绕的气息。真气经过一夜,似乎恢复了一半,浅浅地流动着。恩佐还未教授冥想之法,徐林也只能任其自生自灭。手里只有五枚硬币,而翻开地图,他细细比划着春神塞到文莱的距离。路途尚远,瞧着依旧没放晴的天色,想起没顶盖的马车,徐林嘴里发苦,默默地收拾起行李。
探查士兵换班,士兵甲今日从北门调到了南门,照旧与搭档士兵乙闲扯着胡话。不多时,徐林驾着车赶了过来,士兵甲还认得这个法师老爷,昨天还一副凶神恶煞,急不可耐的模样,今日却像是换了个人,病怏怏地舞着马鞭。被榨干了?士兵甲一边放行,一边恶意地揣测着徐林昨晚如何如何。
徐林哪会知道一个守城士兵所想,直接出门去了。离了城门,芳草幽香,莫名让他想起早晨伏在身上的猫女,毕竟美人曾经在怀也算幸事。徐林一时忘了烦恼,驱车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