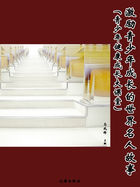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就跟着去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勒非常幸福地用“群体状况”这个词来警告我们——他认为这种东西会扼杀人类个体的珍贵价值。“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莫勒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是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的。”
“美国的立国精神除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假如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他们就有权力起来反对政府。”
莫勒在文章最后辛辣地指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也并不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难以讳言的是,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在这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装配线教育的发达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比方说,我们便常以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别人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对顺应群体与否的问题曾做过专题研究。他在1955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以《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性》的题目发表了即席演讲: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使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但只要你是个具有独立个性气质的人,便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想用理性的方法向环境投降,你仍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资产——自尊。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屈尊附就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可一时得到某种情绪上的满足,却也会使自己的心情难以宁静。”
达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人们只有在找到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些基本的问题。”
1955年6月,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曾经指出:
“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是要把我们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发挥出来。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家庭,都具有责任。这是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理由,也能使我们活得更有用处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些义务,社会便不会有秩序,我们的天赋和独立性也不能发挥——我们有权利也应有一个神圣的机会去培养自己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达到永远的快乐和幸福。”
退一步海阔天空
游览黄石公园的人,都在晚上出来,与其他观光客一起坐在露天座位上,面对着茂密的森林,静待着森林杀手灰熊的出现。的森林管理员口中可知,大灰熊大概能够击倒西方所有的动物,除了美洲野牛及阿拉斯加熊。
灰熊走出森林到森林旅馆丢出的垃圾中去翻找食物。从没有哪种动物会和森林杀手同伍,除了一种小动物。大灰熊不但让它从森林里出来,并且和它在灯光下一起共食。那是一种叫臭鼬。而且大灰熊很清楚,它的巨灵之掌,可以一掌把这只臭鼬毁掉。可是它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因为它从自己的经验里意识到那样做不合算。
在人的一生中,既可以碰到四只脚的臭鼬,又可以碰到两只脚的“臭鼬”。但从很多不幸的经验中可知,无论招惹哪一种臭鼬,都得不偿失。
当我们恨我们的仇人时,就等于给了他们制胜的力量,给他机会妨碍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胃口,使我们的血压增高,使我们忧虑,让我们的健康受损。要是我们的仇人知道他们如何令我们担心,令我们苦恼,令我们一心报复的话,他们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记住:憎恨根本伤不了对方一根毫毛,相反,却能把自己的日子弄成炼狱。
有人这样说过:“要是自私的人想占你的便宜,就不要去理会他们,更不要想着去报复。当你想跟他扯平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伤害绝对比对别人的伤害大得多……”
这段话听起来好象是哪位理想主义者所说的,其实不然。这段话出自一份由纽约警察局所发出的通告上。
你可能不明白报复为什么能伤害到自己,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报复甚至会损害你的健康。“高血压患者主要的特征就是容易愤慨,”《生活》杂志说,“长期的愤怒容易引发持续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现在你该明白耶稣所谓“爱你的仇人”,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而且是在宣扬一种20世纪的医学。在耶稣说“要原谅他们70个7次”的时候,他是在教我们怎样避免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和许多其他的疾病。
查理·马卡洛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医生给他的唯一忠告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生气”。医生说,心脏衰弱的人,一发脾气就可能送掉性命。
真的如此吗?在华盛顿,一个饭馆老板就是因为生气而死去的。警方报告说:“威廉·法卡伯曾是咖啡店老板,因为他的厨子一定要用茶碟喝咖啡,而使他活活被气死。”
当时那位老板非常生气,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去追那个厨子。结果,没追上厨子,他自己却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倒地死去,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把枪。验尸官的报告上写道:“他因为愤怒而引起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当耶稣说“爱你的仇人”的时候,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怎样改进我们的外表。有一些人因为怨恨而有皱纹,因为悔恨而使脸色难看,表情僵硬;不管怎么美容,都难以改变。其实,只要他们心中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爱,脸上马上就能生动美丽起来。这种仇视的心理,还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圣经里说:“怀着爱心吃菜,也比怀着怨恨吃牛肉好得多。”
假若我们的仇人知道我们对他的怨恨使我们筋疲力竭,使我们紧张不安,使我们的外表受到伤害,使我们得心脏病,甚至可能使我们短命的时候,他们不是更称心如愿吗?
也许“爱你们的仇人”你很难办到,但至少我们要爱我们自己。我们要使仇人不能控制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外表。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将你自己烧伤。”
当耶稣要求我们原谅敌人70个7次次时,他也在谈生意。举例来说,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乔治·罗纳先生几年来在维也纳从事律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回到瑞典。
当时他身无分文,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他能说写好几种语言,所以他想找个进出口公司担任文书工作。大多数公司都回信说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目前不需要这种服务,但他们会保留他的资料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却回信给罗纳说:“你对我公司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你实在很愚蠢。我一点都不需要文书。即使我真的需要,我也不会雇用你,你连瑞典文字都写不好,而且你的信错误百出。”
罗纳收到这封信时,气得暴跳如雷。这个瑞典人居然敢说他不懂瑞典话!他自己呢,他的回信才是错误百出呢!于是罗纳写了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可是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对自己说:“等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不对呀?我学过瑞典文,但它并非我的母语。也许我犯的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再加强学习。这个人可能给我帮了一个大忙,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并不能抵消我欠他的人情。我决定写一封信感谢他。”
罗纳把他写好的信揉掉,另外写了一封:“你根本不需要文书员,还不厌其烦地回信给我,真是太好了。我对贵公司判断错误,实在很抱歉。我写那封信是因为我查询时,别人告诉我你是这一行的领袖。我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错误,我很抱歉并觉得惭愧。我会再努力学好瑞典文,减少错误。我要谢谢你帮助我成长。”
几天后,罗纳又收到回信,对方请他去办公室见面。罗纳如约前往,并得到了工作。罗纳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以柔和驱退愤怒。”
我们或许不能像圣人般去爱我们的仇人,可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快乐,我们至少要原谅他们,忘记他们。这样做才是聪明之举。
当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约翰,他父亲会不会一直怀恨别人。“不会,”他回答,“我父亲才不会浪费时间去想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有句俗话说得好:不会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智者。
前纽约州长威廉·盖伦就是一个这样的聪明人。他被一份内幕小报攻击得体无完肤之后,又被一个疯子打了一枪,几乎因此送命。当他躺在医院挣扎求生的时候,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原谅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呢?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也就是“悲观论”的作者叔本华认为:生命就是一种毫无价值而又痛苦的冒险,当他走过的时候好象全身都散发着痛苦。可是在叔本华绝望的深处,却大叫道:“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对任何人有怨恨之心。”
伯纳·巴洛克曾做过威尔逊、哈丁、柯立芝、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等六位总统的顾问。有一次我问他会不会因为他的敌人攻击他而感到困扰。“没有一个人能够羞辱我或者干扰我,”他回答说,“我不让他们这样做。”
没有任何人能侮辱我们或困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允许。棍子和石头也许能打断我们的骨头,可是言语永远也不能伤害我们,除非我们同意。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总是景仰不怀恨仇敌的人。我常常站在加拿大杰斯帕国家公园里,仰望那座名叫伊笛丝·卡韦尔的山。这或许是西方最美丽的山了。
1915年10月12日,一位名叫伊笛丝·卡韦尔的护士在德军行刑队的枪口下慷慨赴死。她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她在比利时的家里收容和看护了很多受伤的法国士兵和英国士兵,还协助他们逃到荷兰。
在十月的那天早晨,一位英国教士走进军人监狱——她的牢房里,为她做临终祈祷的时候,爱迪丝·卡韦尔说了两句不朽的话语:“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后来,这两句话刻在了卡韦尔的纪念碑上。四年之后,她的遗体转移到英国,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安葬大典。
原谅和忘记敌视自己的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些绝对超出我们能力以外的大事,这样我们所碰到的侮辱和敌意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时间计较理想之外的事了。
1918年,密西西比州发生了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情——有一位黑人教师兼传教士劳伦斯·琼斯即将被处以火刑。有必要提一下,琼斯亲手创办的学校现在它已成为一所全国有名的学校。但这里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很早以前的事。
当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的谣言说,德军将策动黑人叛变。琼斯被控策动叛乱,并将被处以火刑。一群白人在教堂外听到琼斯在教堂内说道:“生命是一场战斗,黑人们应拿起武器,为争取生存与成功而战。”
“战斗!”“武器!”够了!这些激动的白人青年冲入教堂,用绳索套上琼斯,把他拖了一英里远,推上绞台,燃起木柴,准备绞死他,同时也并烧掉他的尸体。这时,有人叫道:“叫他说话!说话!说啊!”于是琼斯站在绞台上,脖子套着绳索,开始谈他的人生与理想。他1907年由爱达荷大学毕业。他谈到自己的个性、学位,以及令他在教职员中受人欢迎的音乐才能。毕业时,有人请他加入旅馆业,有人愿出钱资助他接受音乐教育,都被他拒绝了。
为什么?因为他热衷于一个理想。受到布克·华盛顿的故事的影响,他立志去教育他贫困的同胞兄弟。于是他前往美国南方所能找到的最落后地方,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偏僻地方,把他的手表当了1.65美元,他就在野外树林里开始办学校。
琼斯面对这些准备处死他的愤怒的人们,诉说自己如何奋斗——教育这些失学的孩子,想将他们训练成有用的农人、工人、厨子与管家。他也告诉这些白人,在他兴学的过程中,谁曾经帮助过他——一些白人曾经送他土地、木材、猪、牛,还有钱,协助他完成教育工作。
听了琼斯如此真诚动人的谈话,特别是当人们听到他不为自己求情,只为自己的使命求情时,暴民们开始软化了。最后有个老人说:“我相信这年轻人说的是真的,我认得他提到的几个人。他在做善事。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吊死他,而应该帮助他。”老人开始在人群中传帽子,向那些想吊死琼斯的人募了52美元,并交给琼斯。
事后,有人问琼斯恨不恨那些拖他准备绞死、烧死他的人?他的回答是,他当时忙着诉说比自己更重大的事,以致无暇憎恨。他说:“我没空争吵,也没时间反悔,没有人能强迫我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