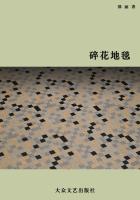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碎锦”门外,一辆八抬大轿静静停着,华轿的金穗随风飘扬,车夫们穿着得体,行为有规有矩,不像其他小户人家,个个横七竖八不说,嘴里还得叼一只当地的大烟枪,云里雾里享受着。一个穿着长褂的人站在轿旁,戴一副金丝圆框眼睛,而且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儒雅的气息,不认识的人,大部分都以为他应该是哪个私塾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但他眼神中透着一股光,这让他看起来精明能干。此人名叫何自闲,是华府几十年的老管家,做事大方得体,深得华家上上下下的尊敬,尤其是华老爷,不论是家事还是外头的事情,都要询问询问他的意见,深得信任。他身旁站着一个剽形大汉,身材魁梧,浓眉剑眼,比普通人高了半个头不止,看起来不是一个好惹的人,街上的人看到了都饶边走,这种人一个拳头都能把人揍死。
沈佩佩由一个小厮领着,一路走到门口,何自闲瞧见这个女子衣着不凡,面容姣好,眼神之中透出一股灵气,眼尖心灵,猜想这个人十有八九便是华筵派他来接的客人。
“何管家,这就是沈小姐。”那小厮走到何自闲的跟前,恭恭敬敬地汇报到。何管家对那小厮点了点头,“辛苦你了,下去领赏钱去吧。”身旁的那个大汉站出来,带着他走开。
“沈小姐,我是华府的管家何自闲,华筵少爷派我来接您去华府,请上轿吧。”何自闲躬身,亲自给社佩佩拉开轿帘。
“多谢何管家,我沈佩佩只是一介戏子,不知道何管家知不知道华长官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沈佩佩看这些下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猜想他定然在华府有一定的地位,就想先探一些口风,所谓名将不打无准备之仗,到时候华筵问自己话时,也好有个准备,不至于被他刁难住。
“华筵少爷请小姐过去,自然有他的道理,我虽然是华家的管家,但是也只是一个下人,少爷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呢。沈小姐你放心去罢,我们家少爷绝对不会为难你的。”何自闲看了一眼轿子,示意她进去。沈佩佩没想到这管家口风这么严,有些无奈。轿夫们见正主来了,一个个都不敢怠慢,连忙低下轿头,请沈佩佩进去。
“多谢了。”无奈,沈佩佩只好从命,乖乖地走了进去。
抬地到是平稳,沈佩佩坐在轿子里面,掀开旁边的轿帘,只见人群都望着这边,纷纷议论,华筵竟然派人用八台大轿请沈佩佩进门,这件事足以成为整个吴县的饭后谈资,之所以影响这么大,还得从这华家说起,近几十年来,这华家可谓是称霸整个苏州地区,华老爷担任政府高官,影响力自然不凡,更重要的是,他又掌管着这一地区的苏绣贸易,要知道苏绣名满天下,之前还是皇家御用贡品,各地当然也是供不应求,中转商们倒腾着玩意,个个都富得流油,更别提华家了,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垄断了整个吴县的苏绣交易,可谓是富甲一方,再加上他的儿子华筵最近又出任了新军统领,如此横跨政商军三界,除了长洲县的杨家,恐怕是无人敢惹。
“这华筵不会是看上碎锦那小花旦了吧?这年头,有点姿色果然就是不一样,上次那个丫头铁了心要嫁进华家,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最后死得可惨了,哎,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这是何必呢!华家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沈佩佩这回可算是飞上枝头了,哪怕是给华筵做小也是不一样......”一些刺耳的声音传到沈佩佩耳朵里。
“沈小姐,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何管家走在轿子的旁边,见沈佩佩拉开轿帘,微笑着问道。
“不不不,没有。”沈佩佩默默放下轿帘,感到有些不高兴,这何管家明明听到了这些人乱嚼舌根,竟然装得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看他长得这般讨人缘,却不是什么好人。“那丫头?”沈佩佩坐在轿中,默默地念叨,他们说的,可是昨日那个女鬼吗?沈佩佩眼前浮现出她那张容颜尽毁的脸,可很归可恨,也只怕是有什么苦衷难以言说,弄得死都不得安宁吧。听这些人说起来,是为了嫁进华家?最后落得这般下场,不知道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可曾后悔过。沈佩佩坐在轿中,不停地回忆起昨日的事情,最后那女鬼去哪里还不知道,恐怕是被徐踵羽收了吧。
轿子摇摇晃晃地,到也算平稳,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停了下来。“沈小姐,到了。请下轿吧。”沈佩佩整理整理了一下裙子,掀开轿帘往下走。
“这边请。”何管家伸出右手,示意她往这这个方向走。沈佩佩抬眼一看,果然是朱门大户,大门都比别家阔气不少,上面挂着一张匾牌,用楷书工整地雕刻着“华府”两个大字,门边蹲着两只威武的石狮子,面目狰狞,青面獠牙,连那看门的都随身斜挎着长枪,个个精神抖擞,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沈佩佩也算是见过了大世面,没想到还是被华府这气派吓到,她定了定神,强装镇定地跟着何管家往里面走。
进门便看到一块高大的石墙屏风,挡住来客的视线,其实这也不稀奇,苏州地带的园林特色一向便是如此,只是那石墙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镂空装饰,花式复杂,呈现出暗金色,整个边框地区还有一圈青绿色,沈佩佩仔细看了一下,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上面好像是金镶玉,用整块玉石雕刻而成镂空,配以暗金,这也太大胆了。沈佩佩心中不禁想起今天那些闲人说的话,但她到不是普通女子,心中从来没有阔太太的梦,有的人撞破头也想来这些地方,好像生活没有了这些依靠就活不下去,想着想着,沈佩佩不觉挺直了肩膀,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何管家后面。
要说这华府,从前面来看,倒也是一个典型的园林,布局和普通园林差别不大,只是规模大了不止一点两点,内部结构也是非常复杂,回廊弯弯曲曲,岔路众多,要不是有人在前面带路,沈佩佩想自己非得迷路不可。穿过石墙屏风,是一条通向议事厅的回廊,旁边有一条竹林小径,何管家带着沈佩佩,径直往那小径走去。
“沈小姐,这边请。”何管家低声说道。沈佩佩心下有些奇怪,走小路不说,都折腾了这么大阵仗,难道还怕别人看到不成?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老实跟着何管家走,心里像水桶一样,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不知待会儿还会遇见什么事情,毕竟沈佩佩还未曾独自一人遇见这些事,没有顾新元罩着自己,沈佩佩感觉有些力不从心,她还应付不来这些事情。竹林茂密,阳光大部分都被竹叶挡在外面,只有些光线穿过缝隙照进来,好看是挺好看的,只是显得有些阴暗,小路两旁堆着黄色的竹叶,层层叠叠地不知道要经历几回春秋才会有现在这么厚。昨日刚刚经历一场春雨,一些新鲜的竹笋纷纷从地上冒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鲜的世界。
“沈小姐你可是跟华筵少爷认识?”一路上默默不做声的何自闲突然问道。
“啊,没有。昨天才第一次见面。”沈佩佩如实回答道,也许,这何管家想的跟其他人一样吧。
竹林小径尽头,一扇墙阻绝开来,中间有一扇圆形拱门,写着“兰园”二字,穿过竹林,阴晦一下消失不见,视觉和尺度感极度收敛,沈佩佩觉得此刻仿佛不是她自己了,面对着眼前之境,她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怪不得叫兰园”沈佩佩嘴里默默地念着,迎面而来的是满园的玉兰,繁花锦簇,一眼望不到边,这可比“碎锦”后院那棵玉兰的花多多了,除了白色,也有粉色的玉兰,沈佩佩觉得好看极了,她自小喜欢玉兰,但从不知道这华府之中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好地方。
“我就带您到这里了,沈小姐若是喜欢这园子,可以慢慢看,不着急。”说完,何管家就从原来那竹林小径回去了。沈佩佩欲言又止,她不知道这华筵搞的是什么名堂,派人带到这里就丢下了她一个人,好歹也是送佛送到西,这算什么回事。但好歹现在可以一个人看花,沈佩佩也就没有说些什么,有外人在,她反而不自在,就一个人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小径慢慢前进。玉兰开花的时候不长树叶,没有绿的杂色,满树都是开的玉兰,显得特别纯粹干净,每棵玉兰下面都堆着一堆黄色的树叶,泥土也是新翻过,看起来这园子的主人对这些花打理地颇为上心,花园中间修建了一个休憩亭,沈佩佩抬眼看去,那亭上又有一块匾,写着“等兰亭”,“等兰亭”,沈佩佩默念着,这名字倒是有意思,她猜测着是否为等待玉兰花开的意思?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这园子也是异常精致,不禁让她想起从前的事情,“等来年春天,我们就种一大片地,全都是玉兰好不好。”沈佩佩的耳边仿佛又想起那小孩的声音,只是时光久远,这个心愿竟然被其他的人达成了,要是他在这里,看到这满园开得正好的玉兰,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沈佩佩坐在等兰亭的座椅上,想着今日的事情,总是感觉有些奇怪,本以为是华筵向她追究徐踵羽的事情,可管家带她到这里来就走了,华筵连个人影都没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隐约间,沈佩佩的耳朵动了动,似乎又听见了那些飘飘渺渺的歌声,顿时,她感觉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一阵疲惫感随之袭来,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竟然靠着柱子,慢慢睡了起来。
迷糊之中,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向她靠近,那人来到她的面前,叹了叹一口气。“师姐,你真是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徐踵羽叹了一口气,顺势坐在沈佩佩的旁边,摇了摇头。
“她这样不会受风寒吗?”徐踵羽旁边显现出一个模糊的影子,声音里满是关心。
徐踵羽看了一眼靠在柱子上的沈佩佩,有些无奈,他感觉自己现在俨然变成了沈佩佩的奶妈,从小便是师姐照顾自己,他未曾这样关心过别人,暂时还不太适应这个角色扮演,可是想到毕竟是自己亏欠于她,随身也未带些什么,便摘掉自己脖子上戴的围巾,轻轻抬起沈佩佩的头,枕在她的头下。初春时节,虽是艳阳天气,还是有些春寒料峭,注意一些总是好的,要是她受了风寒,也许计划就要推迟,想到这里,徐踵羽不禁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女孩子也不注意些,他哪里知道沈佩佩可是那种上房揭瓦的“莽汉”。此时的沈佩佩正睡得香甜,不知不觉,她梦见自己变成了玉兰树上开着的一朵花,想喊却喊不出来,使出浑身力气,像风吹过树梢,最后也只是摇了摇。树下坐着一个青衫少年,沈佩佩看不清他的脸,只是觉得异常奇怪,他身边没有人,少年转过头去,好似在对着空气说话。
徐踵羽看着沈佩佩,眉头紧皱。“师姐,如果我说出实话,这丫头可能会答应帮助我们吗?”
“凡事都有代价,师弟,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虚空中那女子叹了一口气。徐踵羽想象着,此时的她,该是以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望着自己,好像在劝自己不要再苦苦挣扎,但徐踵羽摇了摇头,坚定地说,“不,相信我,我一定会救你。”长久以来,与他相伴的只有师姐,那些在山上的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他的脑海,那些事情他都不能忘,只是时间久了,他慢慢地忘了那张脸的长相,只是心里面还怀着一份执着,为此,他寻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找到了方法,就这一线生机,他不想这样轻易地放弃。
不一会,花园里响起一阵脚步声,皮鞋踩在地面,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听起来不拖沓,甚是干练,徐踵羽立即起身,跑到围墙那里,只余一阵风,轻轻翻身而过。
一个军装青年,脚下飒飒生风,大步流星地来到“等兰亭”前,徐踵羽猜得没错,果然是华筵,他头上戴着军绿色的军帽,但还是掩不住鬓角露出的白发,看来被那女鬼折磨之后还未恢复过来。华筵静静矗立在沈佩佩跟前,见她已经睡着,冷峻的脸竟然如冰雪融化一般,眼神中荡漾着一股喜悦,轻轻地笑了一声。徐踵羽趴在围墙上,静静地观察着这边,心里冷笑一声,他从怀里掏出那颗珠子,叹了一口气,“你知道他为何不能接受你了吧?”那颗珠子发出一阵微弱的柔光,珠身隐隐约约,竟然慢慢出现一些细细的裂痕,徐踵羽用手指抚摸着,只笑世上痴人多,只是自己跟她又有什么区别呢?
华筵脱下自己的披风,轻轻给沈佩佩盖上,斜眼看见她头下枕的围巾,瞧这颜色和款式,尾处还破了一个洞,显然不是沈佩佩自己的,刚刚只有何管家带她进来,除非,这里还有别人,他皱了皱眉,手慢慢放在自己的腰间,拔出手枪,起身四处观察,徐踵羽心里喊了一句不好,便跳下围墙,一瞬间,华筵发现这边的踪迹,正准备追出去,但转过头看了看熟睡的沈佩佩,跑到一半又走了回来。
不一会,何管家和那副官走进兰园,“少爷,我们有事禀报......”那副官粗声粗气,大嗓门,打仗是个好手,可就是缺个心眼,也忒不会看事了,还未说完,华筵怕吵醒沈佩佩,便瞪了他一眼,示意他们在等兰亭外面等候,何管家和那副官相对望了一眼,觉得眼前的的华筵,不太像他平时的作风,他哪里是对女子这么上心的人,即便是堂堂张司令的女儿,大家都想法设法撮合他们两个,那姑娘对他也有意思,长相也算是钟灵毓秀,可华筵却没有正眼相待过,最后搞得不欢而散,还差点得罪人家张司令,可他今天对沈佩佩竟然如此细致入微,着实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奇怪归奇怪,还是副官还是乖乖地闭嘴,规规矩矩地走到外面去。华筵替沈佩佩掖了掖披风,起身轻轻走出去。
“什么事?”华筵背着手,冷漠地问道。
“刚刚......”副官还是粗着个嗓子,正准备汇报,何管家眼见他不知情况,赶忙阻止道,“副官在外巡查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影,看方向似乎就是从这兰园跑出去的,不知华筵少爷看到那贼没有。”见何管家打断他的话,他心里未明白,还有些不太痛快,便皱着眉头看着何自闲,何管家不动声色,心里面直骂他是木头脑袋,不解风情。
“不妨事,加强巡逻。”华筵简单丢下几个字,转头回去,看着正在酣睡的沈佩佩,宁静而安详。其实华筵已经猜到刚刚那人的身份,有这样的身手,还在沈佩佩的周围,除了徐踵羽,碎锦应该没有其他的人能做到,只是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华筵还猜不透。
“少爷,要追吗?”何管家望了望那边的围墙,轻声请示华筵,华筵摇了摇头,招手示意他们出去。何管家和副官相视一望,双双退去。出了兰园,副官停了下来,粗声大气地问何管家,刚刚为何要阻拦自己,何管家先是一愣,没好气地笑了,“你啊你啊,真不会看事,你没有发现华筵少爷对那沈小姐,和对其他的女子,有些不同吗?”,何管家自小便在华府管事,不论大小事务,皆是十分有分寸,看人眼色更是不在话下,做人行事干净利落,颇有王熙凤的作风,除了没有她那般泼辣,何管家在华府的人缘那都是时间积累起来的。“啊?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哪会看这些玩意。不过”副官顿了一顿,心里面仔细一想,华筵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追求者自然众多,但他何曾看过华长官对其他女子正眼相待过,哪次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唯有这沈佩佩,华筵竟亲自请她来自己精心照管的兰园。“不过这回华长官,好像真的不一样。”副官抓了抓自己的头,苦恼地说到,他还不太习惯华筵对其他女子这样。
“无妨无妨,这是一件好事。能让咱们华筵少爷这样对待,相必那沈小姐也有过人之处。再说了,少爷年纪也不小了。”何管家转头望向兰园,默默地站立着,心里不知道在沉思一些什么。副官看着他点点头,觉得何管家在这些方面还真是比自己强些。
兰园,沉睡中的沈佩佩正觉得冷的时候,身上忽然一阵袭来一阵温暖。想要睁开眼睛看看,但她觉得眼皮实在是沉重极了,便继续靠着睡觉,梦里面自己还是那朵不会说话的玉兰,但树下竟多了一个莽孩,灿烂地笑着,盯着自己。他认得自己?沈佩佩吃惊极了。黄昏渐渐来临,沈佩佩慢慢睁开眼睛,瞧天色已经不早了,一下惊地跳起来,身上的披风滑了下去,沈佩佩有些疑惑,这军绿色的披风是从哪里来的?怪不得刚刚一点都不冷,沈佩佩拿着这大衣,坐在等兰亭中,正疑惑着,又在旁边发现一条青色围巾,沈佩佩摸了摸,质地粗糙,与这披风明显不一样。
“你醒了。”华筵的声音传过来。沈佩佩抬头一惊,她没想到华筵在这里。
“你在这里多久了?”沈佩佩瞧见华筵的头发还是跟昨日一样,一头银白,有些像少年白头。
“从你睡着的时候。”华筵淡淡地说,沈佩佩脸有些红,一夜之间,她竟然被两个人看到自己睡着的样子,要知道在这片地区,黄花大闺女的睡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的,在加上自己的确.....不怎么好看......便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还好没有什么邋遢的东西,比如,口水。华筵虽然没有潘安卫阶那般容貌,但好歹也是长相俊秀,眉宇之间透露出一股军人独有的英气,再加上沈佩佩正是少女怀春之时,要说没有怀什么龌蹉心思,那也是不可能的。华筵像是猜出来她的心事一般,忍不住笑了笑。
“不知道今天华长官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沈佩佩看华筵一直盯着自己,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转移话题。
“没什么事情,我今天找你来,只是为了感谢你昨天给我的手帕。”说着,华筵从怀里掏出一方丝帕,沈佩佩又不自觉地想到昨日,徐踵羽把他丢在地上的一下,不知他的头现在怎么样,沈佩佩耳朵里面回响着当时“咚”的一声,后脑勺竟然感觉有些疼。
“没事。”沈佩佩非常奇怪,她为何不问徐踵羽的事情,还是仅仅因为救了他一命,所以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其次,今日华筵专门寻她而来,欲言又止,到最后就掏出一方手帕给她,“华长官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沈佩佩相信他应该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打算继续追问。
“你以为我要对你说什么?我说我是专门请你来我花园参观这玉兰花,你信么?”华筵把那块手帕丢给她,不巧此时一阵风吹过来,那方刺绣手帕展开,半途掉在了地上,但奇怪的是,地上手帕里面竟然包着一颗红纸包裹的酥糖,瞧这包装,是七里山唐街桥头的那家李记酥糖,住在张老太的对面,历史悠久,是用传统手艺制作的,味道非常好,沈佩佩自小贪吃,嘴巴一刻也闲不下来,还经常在后院给戏班的姐妹们派发零嘴,认肯定不会认错,但问题是,华筵这般冷酷的人,怎么会随身携带这种姑娘喜欢的东西,难不成他看起来高冷,其实内心还跟小孩一样?但她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想法,只是被自己排除掉,她猜想今日华筵又是派八抬大轿,又是请她赏花,还给自己盖披风,这糖说不定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只是他位居高官,不好意思亲自给自己,就想出这个办法,但真要是这样,华筵未免也太呆了一点,要是这手帕还留在他这里,日后也方便有借口来找自己,沈佩佩心里暗暗笑道。恍然间,她记起来昨晚的事情,误会华筵给自己遮雨是不安好心,对自己有点儿意思,心里面便不停地骂自己不要脸,“沈佩佩啊沈佩佩,你真是丢脸。”
“花挺美的,谢谢了。”沈佩佩连忙捡起地上的手帕和糖,“呃呃,还有这个。”沈佩佩一本正经地伸出手,把糖递给华筵。华筵冷冷地瞥了她一眼,淡然地说,“无妨,你拿去吃吧。”沈佩佩心一沉,觉得他果然是这样的人,还好自己刚刚没有乱说什么,否则丢人就丢大了。
耽搁了许久,此时天色已晚,沈佩佩琢磨着是时候该回去了,徐踵羽在碎锦,今后还不知道怎么安顿,再说了,华筵一直站在等兰亭亭口,一句话也不说,两个人显得尴尬无比,便说了句,“现在天色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华筵点了点头,“走吧。”沈佩佩见他也没有送自己的意思,便一个人悻悻地走了,心里觉得他这个人也忒无趣了,但转念一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还好回去的路只有这一条,只要不迷路就好。华筵望着她的背影,默默站立着没有说话,半顷,一个人影从等兰亭上跳跃下来,样子有些奇怪,像猴子一样蹲在华筵身后,披头散发,一直蹭着华筵的脚,华筵叹了口气,蹲下去,温柔地摸摸它的头,“以后我不在了,把你托付给你沈姐姐可不可以?”那影子使劲摇头,嘴里面发出哼哼的叫声,它越抓越紧,指甲刺破皮肉,鲜血顺着脚腕流下,一阵剧痛传上来,华筵忍着疼,把大衣掀开,从里面掏出一把红纸包着的酥糖,递给它,“吃吧。”那人一见这糖,像饿狗扑食一样,一把从华筵手中抢完所有的东西,跑到亭角呲牙咧嘴地咬起来,就是不会撕包装,华筵走过去,耐心地替它一颗一颗地打开......
半顷,后面传出一个声音,“少爷,您以前认识沈小姐吗?”何管家站在他身后,华筵拍了拍手上的糖渣,站起来,“恩,认识。”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您身边,寸步不离,从未见您结交过戏楼里的女子,这个沈小姐是您回来之前认识的吗?”何管家直勾勾地盯着华筵。
“恩,我小时候认识她。”华筵眼前又浮现出沈佩佩年少时稚嫩的脸庞,十年过去了,她现在还是和以前一样,脸吧圆嘟嘟,性格大大咧咧地,除了更美,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自己如今这幅模样,恐怕连她也认不出来了,想着想着,华筵叹了一口气。
“少爷,您说您昨晚,是沈小姐帮的您?”何管家问道。
“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记得她小的时候就有些奇怪,老是偷偷跟我跟我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华筵的眼前浮现出十年之前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