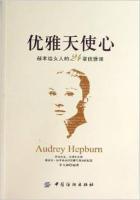有一学生向在台大演讲的王永庆请教:“您能告诉我,您的成功,到底是勤奋重要还是运气重要?”王永庆答:“我负责地告诉你,年轻人,我用一生的勤奋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运气比别人好……”
拾煤鬻茶,生计维艰勤字诀
1917年1月9号,旧历的腊月廿四,这一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年,距离龙年的除夕还有6天时间。就在这一天,在台湾新店一个小山村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和所有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哭声有些不同,有点像新年的鞭炮声。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海军损失惨重,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朝割让台湾岛归日本所有。从此,日本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台湾人也遭受了长期的摧残。
1917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久,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在亚洲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由于台湾远离主战场,因此并没有遭受战火的威胁。然而因资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以供战争之需,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战争结束了,王家希望这个抓着龙年尾巴出生的男孩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于是祖父给他起名叫:永庆。
新店的直潭里四面环山,没有平整的土地,只有低矮的丘陵,贫瘠的红土地里净是碎小的石块。这寸草不生的土地却是种植茶树的好地方,人们便以此为生,在开荒出来的山坡上种植茶叶,这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生活,辛苦可想而知。
父亲王长庚也是个穷苦的茶农,以耕作几亩贫瘠的茶田,卖茶叶维持生计。茶叶每年只有春季到秋季大约半年的生意好做,其余半年时间赋闲在家,只得找点零工贴补家用。
直潭里分散住着数百户人家,没有别的生计,生活都很困难。人们害怕走出山林,就这样艰难度日。那时候,日本人在附近的山上开采石矿,需要一些有力气的男人,那是一项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危险的活,然而这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到,还要四处托人情才行,主要是那时候工业很少,靠力气打工的人很多。
男人们上山打工要住在那里,家里的一切就全靠女人们来做。她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米不够吃,当发现米缸里的米所剩不多时,她们就急切地盼望山上的丈夫能够早些把钱寄回来。如果钱寄慢了,没米下锅,她们就只好先向邻居借一些,熬很稀很稀的粥,勉强度日。一直等到丈夫把钱寄回来,再买米还给邻居。所以,那时候虽然很穷困,但是邻里之间感情是很好的。
在王永庆的记忆里,那时候家里的粮食从来没有充裕过,一日三餐往往只有稀饭,里面可以照见人影。就是这样,母亲还总是把碗里可怜的几粒米捞出来,喂到儿子的嘴里,希望儿子能够吃饱。母爱是伟大的,永庆那时候还小,只知道贪婪地吃,顾不上体会母亲的情。
稀饭总是很快就消化光了,一顿饭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那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时候都在挨饿,日子过得相当苦。村民们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改善一下生活,预备一些米饭和猪肉,慰劳一下缺油水的肠胃。等年节一过,又开始了吃稀饭的生活。
在当时的社会,百姓生活大多如此,王永庆家自然也不例外。一年辛辛苦苦劳作,只能勉强度日,有时候连肚子都填不饱。孩子们稍大一点的时候,就要帮助家里做点事,而捡煤屑算是一件力所能及的活了,对孩子们来说,也算是最有意思的一项活动。
村子附近有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有专门从狮仔头山运送木材或煤的台车经过,王永庆母子俩像别人一样等在旁,捡拾从车上掉下来的木材或煤块,从中挑出一些好的去卖钱,不好的就自己带回家以备生火烧饭用。
狮仔头山位于台北新店广兴山区,海拔约857公尺,属插天山系,因山形特殊,由远处眺望,极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大狮子,而且狮头的部位刚好有一个石洞,像狮口一样,因而得名;由于“狮仔头山”与七星山、土库岳、大栋山并列为北部郊山的“四大名山”。
狮仔头山产煤也同时给直潭里的村民带来了一项副业,村中大部分时间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居住,他们没有什么营生能做,而捡煤屑和木材正好不用花什么本钱,而且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大家等在车道旁边,远远地望着有没有车会过来,犹如望穿秋水的恋人。即使每天过一千辆车,人们也不会嫌多,也不会觉得吵。母亲拉着永庆的手,也同样等在道旁。
然而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竞争,也许王永庆就是那时候开始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和母亲捡煤屑并不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煤块还没掉在地上,就已经被人牢牢地抓在手里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他们要比你高大一点,比你灵活。也有运气好的时候,恰好有木材掉到你的脚边,别人虽然不会再伸手过来抢,但还是会多盯几眼,眼神就不那么友好了,然而这样幸运的事情是不多的,很少碰到。
为了捡到煤块,能够卖一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不得不很早就带着小永庆出门,抢在别人的前面,就能够多得一点。也许就是那时候,他懂得了勤快的意义。晚上有些车经过,因为天晚了看不清楚路面,所以有的时候会掉很多煤块或木材。谁去得早,先看到了,就是谁的。运气好的话,一个早晨捡的煤块会比一天捡的还要多,所以很多人都去得很早。
如果去晚了,就要多走路,去很远的地方捡。顺着台车道,慢慢上山,或者走得更远。太远了,那里没多少人愿意去,而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生活就是这样,你只有比别人走得远才能领略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如今的人们会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别墅,欣赏优美的风景,过清静的生活,直潭里就是这样的地方,然而那里的人们却并不为此而感到快乐。
那里群山环绕,绿水潺潺,小山上还有成片的树林,一些不知名的鸟在树林间蹦蹦跳跳地叫着。然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小永庆并不十分开心,他没有多少时间去那里玩耍,也没有心情注意那些风景。他只是希望山路变得更陡峭一点,这样过路的车就会掉下更多的煤或是木材,他就可以多卖一点钱。能够吃饱肚子,就是那时候小永庆心里最大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母亲拉着他的手经常要走很远的路,直到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饿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
最发愁的还是母亲,她要不断地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算计。
母亲开垦了荒地,种上了各色的蔬菜,这样就有了自己的菜园,吃的蔬菜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母亲总能算计着不让地闲下来,会一茬接一茬地长出不同的菜,如果米不够,就可以用菜充一下饥。
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猪油比金子还贵,做菜的时候只能用一两滴。这样做出来的菜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难吃的菜,母亲吃剩了也舍不得倒掉,要留到下一顿热热再吃。
那时候,小永庆就知道了:只有靠劳动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道理在他那儿已根深蒂固,他时刻不会忘记劳动。如果没有事情做了,他就扫扫地,搞一下卫生,总之要找一点事情做,从来不让自己懒惰,他觉得这样才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有时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要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养成一种习惯。
母亲虽然很少告诉他要勤劳,却是用实际行动来教导他们的。
因为浮现在王永庆眼前的,时常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5岁那年,有一次,出生没多久的二弟永在在床上哭闹,小小的永庆就跳上床,带着好奇与惊慌看着哭闹的弟弟,等待着母亲来哄。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母亲也没有来看一下哭泣的弟弟。这一幕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很久后他才想通,那是因为母亲太忙了,解决一家的生计是比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在父亲上山打工的日子里,母亲要负担家中所有的劳动,地里的茶树要收拾,菜要种,家里还有一堆人的饭要做,母亲每天都在脚不粘地地忙碌着。
通常在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家人都相继睡去了,母亲还是不能休息,她还要把地瓜切成条加上水煮,做成猪饲料,然后把它倒在猪的饲料桶里喂猪。所有这些都做完以后,母亲才能梳洗睡觉,往往是头一挨枕头,马上就睡着了。母亲甚至都没有发牢骚的时间和精力,要安排的事情太多了,只有坚持和忍耐。
在贫困的山村里,找到一个能够解决家庭温饱的途径犹如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艰难。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家里所有人只能省吃俭用,互相帮助。也多亏了母亲忘我地劳作,每年都能卖一次猪来赚一点钱,钱虽然不多,但能够使全家勉强生活下去。
多年以后,在王永庆的记忆中抹不去的还有那满山的茶树和采茶的艰辛。
王永庆的父亲种植的是“铁观音”,“铁观音”素有“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之佳称,驰名于海内外。然而,种植茶叶本身却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再加上父亲的体质天生很差,所以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在了作为长子的永庆身上。
铁观音,又被称红心观音。天性娇弱,抗逆性较差,产量较低,有“好喝不好栽”之说。“红芽歪尾桃”是纯种铁观音的特征之一,是制作乌龙茶的特优品种。
铁观音制作严谨,技艺精巧。3月下旬萌芽,5月上旬开采,一年可采制春、夏、暑、秋四季。茶叶品质以秋茶为最好,春茶产量最多;秋茶香气最浓,俗称“秋香”。
每年春茶采摘,都像一场战争。从清明前开始也只有20来天。赶着好天气,每天摘下的青叶,通宵都要炒完。王永庆的记忆里,随地可见的大小“簸篮”、“竹筛”,里面盛着刚刚摘来的青叶,嫩绿初青,碧碧的叶像无数双青眼在眨动。几口大锅前,父亲则忙着炒茶。杀青有下马威,初时火温有120℃,炒茶人斜坐高凳,一只手抚锅边,一只手下锅飞快翻动,然后两手轮流换岗。
待青叶炒“燠”了,立即起锅,杀青毕。接下来炒第二轮,一锅可炒杀过青的叶子四五两,炒制香茶的秘诀更在这第二回合上。
只见那青叶入锅渐渐变身,丝丝缕缕的香魂飞将出来,那只炒手既要翻云覆雨,又要怜香惜玉,一掌掌压下去,不能断了青叶的好身材,也不能让茶香全部消散了。时间、火候、动作、香气、干湿……全在一双手啊。只有熬得不老不嫩,不温不火,如玉如金,如刺如针,才算有模有样,有脸有面,谓之香茶。
除此之外,父亲还和爷爷一起做茶叶买卖。春天和夏天,每天早上4点父亲就出了家门,和雇工一起去茶叶地收购村民们前一天采摘的干茶叶,然后回家。
收购的茶叶有很多种,质量上乘的茶叶为银黄色,质量一般的茶叶略带黑色,质量最好的为银白色。在收购的茶叶中,挑选出黄色的茶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银黄色的茶叶干了以后很容易破碎。所以还必须再次和黑色的茶叶混合包装,然后把包装好的茶叶装到渡船上,顺直潭里的山谷直接运送到台北大桥附近的批发市场。其中这运送的活儿就是永庆父亲的工作。
然而,忙过了这一阵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特别是到了秋天和冬天,去山上打工还要托关系,这样大家就想做点其他的事情。这里的土地,除了长茶树之外,还有一种洋槐树可以生存,父辈们种下的已经长成了树林。然后村民们把年龄老的树伐掉,然后做成木炭,拿到城里去买。有钱人要用木炭取暖,要用木炭暖屋子,煮火锅,所以销量还不错。但是小永庆的家里从来都舍不得用。到了春天,在那些地上种上茶树,仍旧靠卖茶业来维持艰难的生活。茶叶生意的利润是很高的,但是茶农和这种小生意的利润是很低的。
为减少成本,每到春天茶叶生长的季节,永庆家就把平时用来装面粉的袋子改装一下,用来装茶叶。但是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要用传统的方式染包。由于父亲体弱多病,这样的事情就全部由母亲一人承担。就连挑选茶叶的事情也常常得母亲亲自过问才行,可以说母亲就是家里另外一个父亲。
赤足荒学,老大徒伤悔字诀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孩子都会慢慢长大。
孩子小的时候,总会想等大一点了就不会这么累人了,可是长大一点了,就会发现还会有新的麻烦,特别是对那些穷困的人家来说。
首先一个问题是,孩子大了饭量就会增加,今天我们可能不能体会到,有了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多吃一点,而穷苦的人家往往会因为吃饭发愁。孩子要长身体,需要营养,但是环境不允许,家里没有钱给他们补身子,甚至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衣服穿呢?孩子多的人家往往一件衣服会穿好多年,老大穿了,老二穿,甚至缝缝补补一直穿到老小,大家都不能穿了的时候已经都成破布条了,也舍不得扔掉,留作补衣服用。
更麻烦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大了要上学。
当时的台湾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大家讲日语,灌输对天皇以及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思想。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面对日本人的这种奴化教育,中国人多数只能忍受,却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日本人的学校。
况且,家里把孩子养大了,刚刚能够做个帮手,却要送进学校,生活本来就很艰辛,这样学费先不说,岂不是又少了一个干活的,生活会更加艰辛。
所以,一般的人家都是要孩子帮忙下田或者看牛,不送去学校。当时,一个孩子看一个月的牛,就可以挣到一两块钱,也可以解决许多的事情了。下田还可以帮着多收一点粮食,农闲了还可以上山做一点苦工,或就待在家里帮一点忙,减轻一下父母家务的重担,让他们腾出手来做别的事。
1923年,王永庆7岁了,祖父开始念叨该是上学的年龄了。祖父曾经是教书先生,多少有一点学问,他懂得,家里总要有个识字记账的人,总要有一点文化才能有出息。况且,虽然是日本人的学校,却有中国的教员,这些教员经常也会挨家挨户地劝说家长送孩子进学校。
那些教员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怎样才能成为富有的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的处境,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但多数是对牛弹琴,村民们并不懂得将来会怎样,因为生存还有困难,他们认为怎样做总归是要娶老婆生孩子,而这一切是看有没有钱,不是看有没有上过学。
为了一个孩子,教员往往要走上很远的路,反复来好几次。
然而,王永庆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第一次教员路过他家门口,觉得他还小,却看上去很聪明,便顺便进了他家。恰好母亲在家,教员说明了来意,母亲不置可否,她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因为大女儿也到了读书的年龄,然而他们之中只能有一个去上学。
母亲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要送孩子去读书,但是只能让永庆去,他毕竟是个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小永庆幸运地进入了小学。在穷苦的环境里,男孩子总是要比女孩子幸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