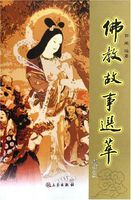为此,他的住房、工资和坐骑,都不如他的助手。为了帮助他人,他一掷千金,“割自己的肉都愿意”,对自己和家人的花费却相当苛刻。看去俨然像梁山头领及时雨宋江那样替天行道,济困扶危。
刘备靠“人和”而获胜;牛根生则靠“人缘”而成功。
刘备爱民如子,不肯丢弃随他逃难的百姓,甚至把他钟爱的独子摔在地上,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在“收买人心”。
牛根生爱他的铁哥们和蒙牛品牌,他也在“经营人心”。
但不论是“收买人心”也罢,“经营人心”也罢,似乎都是一种生意,结果也都是为了“得人心者得天下”。牛根生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坦承地说:
宁愿大家把它视作一次“一本万利”的精明投资,而不愿人们单纯把它视为“道德牺牲”。
当然,任何一种比喻都是蹩脚的。
牛根生既不是宋江,也不是刘备,他就是他独特的“这一个”,一个最具有潜能也最能充分释放潜能的当代罕见的成功企业家,一个最有可能率先成为大陆李嘉诚式的一代企业领袖。
这,主要体现在我在下面要重点讲的牛氏哲理禅机和“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人生境界上。
(二)
在这方面,牛根生与李嘉诚似乎有出奇的相似之处,甚至还棋高一着,更为超前。
“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本来就是儒释道诸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尤其是佛道二家讲得更为精妙绝伦。
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开头就讲: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去。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但以老子为宗祖的道家在讲“无与有”时,说来说去始终没有超越二元对立,依然在辩证法的框架之中。而佛家则不然,它包容了也超越了有与无的二元对立状态,而升华为一个新的“空”的意象形态,即:
亦有亦非有,亦无亦非无。
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
有与无,正如色与空一样,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既是存在,又不是存在。既不存在,又是存在。实际上它已构建为一个气吞宇宙,包容一切的“无”或“空”的圆形符号。其“圆心”,就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禅机”。
我还不能断定牛根生是不是佛门中人,但从《蒙牛内幕》一书中,不时看到这样的说法:
今天,人们从牛根生的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佛性”,或者说“哲学性”。
牛根生和其他与会的知名企业家一起参禅。老牛说了一句话:“命和运其实是两码事。企业做好了就是运,而做不好就是命。”是不是充满了禅机?
这倒多少充满了一点佛光禅影了。
但不论老牛是与不是,仅从蒙牛文化的最大特点“博”字看,它“纵取今古,横征中西,萃百花蜜,摄千家魂,前人已有的,点睛之,前人没有的,创造之”。
而老牛本人则更是一个容纳百川,采撷百家之长的高手。他像一个好“猎手”,自己需要什么就“猎”取什么。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凡是他需要的,通通拿过来,为我所用。
《蒙牛内幕》的两位作者说,他们“之所以将牛根生跟佛祖牵到一起,也不是为了‘僧借佛光’,实在是因为他念的是一部‘苦经’,与佛教的苦尽甘来、凤凰涅盘异曲同工,又与道家的有无相生、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脉相承,可谓‘天——地——人’三三相通。”二位作者说:
从创立蒙牛,到身价数亿(按照《福布斯》的排名,上市时牛根生身价1.35亿美元),再到捐出全部股份,从个人角度看,牛根生挥写的是一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财富轮回故事。
“富而行善”,凡是成功的商人企业家都会这么做。但像牛根生这样捐出全部股份,几乎散尽家财为大家的,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是现在,他还是全球第一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从“金本位到人本位”和“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禅机佛法的体验与领悟。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像帝王将相那样把钱财带进坟墓,但迟早也会被人挖出来。
可见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而金钱倒可以将人送入坟墓。金钱对牛根生来说,不在乎“所拥有”,而重在乎“所用”。他说:
我现在是自己让它从有趋于无,这才是支配金钱的最高境界。
找钱是花钱的因,花钱是找钱的果。
牛根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找到了源头的“因”,而且还找到了尽头的“果”,同时又从尽头推到了源头的“因”,再回归到尽头的“果”。
人们之所以不敢散财,是因为害怕千金散尽不复来,自己又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但牛根生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大有”与“大无”是相通的。他用自己的“小有、少有和短有”,换来的却是蒙牛公司和广大奶农的“大有、多有和长有”。
牛根生对此作了符号性的解读:
代表无。
“1”代表“一己之有”。
“肄”代表“无穷大”,即无穷大的社会财富。
有形之物,毕竟有限,只能是越分越少。
无形之物,却是无穷大,因而只会越分越多。
这个“无形之物”,实际上指的是精神财富,即李嘉诚说的“内心财富”。它的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量化的,而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佛”的光辉,或人文精神。
至此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牛是用他的“一己之有”,换来的却是利益人群、温暖人间的一种更大更美的精神之光。而他自己看去是又穷了,空了,但实际上他却因此而更富、更美和更充实了。因为他在人格人性的修炼中,完成了、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超越和“从有到无”的回归。
按佛家的符号表述则是:
正如禅师说的:
山——非山——山后一个或山,看去与原来的或山一样,但实际上经过人生磨难的一番九死一生的“整合”打磨之后,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者既包容了前者,又超越了前者。它看去是、是空、是无、是小,但实质上却是最充实、最富有、最圆满的无穷大,就像天空、大海、宇宙,而且能超越时空、乃至超越一切,进入无穷的最高境界。
从东方人格金字塔看,老牛已从“功利需要、伦理需要、归属需要、品学需要”,正在向最高一层“禅的境界”攀登。
只有像佛祖那样大智大慧的人,才有希望登上人格金字塔的顶峰,从而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难怪许多人都在说他“老牛已多镀了一层金,逐渐修炼成佛”了。
牛根生自己也说:
很少有人从无到有以后,又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快感,来自你的价值被承认,但是缺少尊重。而从有到无的过程,是世间所有人对你不明白之后,变成所有人尊重你,这种快感是金钱、权力远远不能带来的。
王侯将相未必就贵;平民百姓未必就贱。
富豪未必就幸福快乐,为人所尊;穷人未必就无喜无福,为人所厌。
其中的“因”与“果”的奥秘,全在于人生境界的“高”与“低”。
为牛根生所钟爱的“尊重”,在人格金字塔上属于第四层,即“尊重需要”(“学品需要”)。
当老牛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超越和“从有到无”的回归之后,开始人们非但不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脑子进水了一时昏了头,患了癔症、癌症,是作秀炒作……然而一旦明白过来之后,这才转而对他“尊重有加”,无限崇敬。这是用金钱和炒作买不来的一大笔无穷大的“无形财富”,远远超过了他的“捐股”。这才是真正的“一本万利”。因此,老牛感到从未有过的富有与充实,也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甚至可以说,他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还富有和快乐。
禅师们常说,施者比受者更快乐,救者比被救者更幸运。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老牛的这种快感与幸福,一般人难以理解悟透,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种快感是金钱、权力远远不能带来的”。
“安贫乐道”的人文学者,在常人的眼里,无疑是呆与傻、笨与拙。
特别是在今天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经济中,在天下尽“市道之交”的社会里,则更被人看成是可笑而可怜的“苦行僧”。但安贫乐道者却义无反顾,乐此不倦。他们依然要苦苦地支撑起人类文明的这片蓝天,因为这既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也是个体人格学品、尊重的需要。
在我看来,牛根生不是一般的企业家,而俨然是一位“安贫乐道”
的哲学家、禅学家。但凡是成功的金融家、经济家和企业家,乃至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大鳄”,也大多是哲学家、禅学家和人文主义者。
更令人拍案惊奇的还是,牛根生虽然不及索罗斯、李嘉诚们那么富可敌国,但他却敢为天下先,超越他们而率先散财捐股,完成了人格的自我实现,更接近于人格金字塔的顶峰,几乎成了“逐渐修炼”成功的“如来佛祖”。
但佛祖再崇高再伟大,他的双脚仍然踏在人间大地上。他依然要在滚滚红尘中,托钵化缘,他照样还要普度众生。
伟大来自平凡。从平凡到伟大易,从伟大回归于平凡却难。入佛界易,进魔界难。
“高才非智,智者不显。”
“大智知止。”
老牛离人格金字塔的颠峰还差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不知他能否越过这道“坎”?
因为,我从老牛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中,隐隐看到一些“入佛界易、进魔界难”(此句名言为日本一休大师所说)的不利因素。
(三)
人们都在说,牛根生是整合各类资源的行家高手。其思维之灵活,其手法之高超,足以令人“观止矣”。
别的不用多说,单是对“奶源”自然之源的开发和对媒体资源的整合,就足以使那些成功的企业家、策划家和经济家们黯然失色,望而却步。
总之,牛根生成功了,胜利了。
但这又如何?
内蒙草原是大自然赐予内蒙古人民的一笔最大的无形资产,天然财富,是打造“中国乳都”的“命门”血脉。但那又怎样?
我在《禅林清音》一书里,曾引过媒体关于内蒙草原的一段报道,不妨先转录如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也许是人们向往的北国风光,一片净土吧?
然而,据《凤凰周刊》近期报道:
2004年8月,记者应邀跟随曾经是内蒙古知青的数十人,从北京驱车近千公里来到世界着名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深处。令人意外的是,前几年没膝的草场已风光不再,如今多是一片枯黄或者灰暗,不少地区的草更是连脚背都遮不住。
当年水草丰美,如今满目疮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实在是令人吃惊。
……锡林郭勒这个中国最大的天然牧场退化面积已经超过50豫,连草原最美丽的夏天,见到的也只是稀疏小草点缀着裸露的土地。草原已被手指甲大的沙砾覆盖,过去用舌头揽草吃的牛,现在也不得不用嘴皮啃草吃了。由于草场不好,其他一些牧民已经告别了蒙古包,外出到他乡打工。
草没了,人走了,这自然不是一方净土。
如今的假新闻太多,不少记者都在靠炒新闻混饭吃,一张口便胡说八道。因此我不能断定这里说的是否合乎事实。
那位百岁高龄的禅师曾说我与内蒙尚有一段“因缘”,但机缘未至,我还没有来得及到内蒙草原观光考察,自然无从断定是否就像记者说的那样“风吹草低无牛羊”了。
走笔至此,恰好家人取回刚到的报刊杂志,见《南风窗》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抗议对自然的暴力》的文章,说的正是绿色环保的问题。
作者是现年55岁的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文章中说:
根据绿色和平的全球森林地图,目前中国未受侵扰的森林仅占国内森林总面的2豫,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些最珍贵的生态系统受到严格保护的只占0.1豫。
至于像APP(金光集团)那样毁坏原始森林的情况,则更是惨不忍睹。
《新京报》也登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的一段话:
环保总局对20个江河水域附近的化工石化大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显示我国江河水域存在较大的布局性环境风险,相应的防范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在排查的20个大项目中,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河流岸边,有重大环境隐患的就有12个。
在两大水系排查的20个开发大项目中,竟有一大半项目存在着重大的环境隐患。
内蒙草原虽然不是长江黄河,但在开发草场时,是否就没有“隐患”呢?
众所周知,内蒙古粮食以玉米为主,除草种玉米曾给草原带来最大冲击。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畜牧业,蒙牛尽管发出了“还我草原”
的呼吁,鼓励农户退耕还草,为此还颁发了种草补贴,免费提供草种,但这样是否就使“大量耕地都变成了绿油油的苜蓿草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