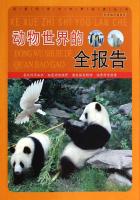即使忙的不可开交,我还是要停下来,让眼睛歇歇脚。曾很多次,我都问过母亲,那个卷眼角膜的恩人是谁,我想去看看。每次母亲总是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还有,还有,父亲。母亲说,他去了广州,可能一年半载都回不来。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想打个电话。”餐桌上,我说。
母亲的手忽然抖了一下,她有些哀怨的望了一眼,然后拿起旁边的碗,盛了一碗汤。
“把这个吃了,然后去写作业。”
“妈,爸爸的电话拿给我。”我撒起了娇,缠住母亲。
继父别有用意的咳嗽了两声,递了个空碗过来,“柳州,给我添点饭。”
隐瞒,哄骗。
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一点搞不清楚,即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减少我受伤的最好办法。但,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2006年的元旦,我碰到了许久未见面的老邻居,她一五一十的倾其所有,包括之前赶我出来,还有在医院接受治疗,后来又,种种种种的。时隔2个多月,我从奇怪的掩盖中醒了过来。
“柳州,你也别难过了,活着的还不是要活着。”身后的安抚声异常的别扭,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最后跟我说的话。
“柳州,不怕,有我呢?”
我现在很害怕,你在哪里呀,爸爸。
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起来了,捂着眼睛哭了。
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了,擦干眼泪,佯装毫不知情。可同时,脱掉了那件粉红色羽绒服,灰色的衣服裤子,灰色的棉靴。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父亲的最爱---酒和烟,还有他喝酒时最爱吃的花生米。
所有的离去都是一个模样,冰冷的墓碑前,野草早已枯黄,风声早已吹完。这样的石头块,一排排的陈列着,仰望着,静默在时间的尽头之中。我知道,他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我了,虽然,以前,因为很多事,我们发生过很多不愉快。
“爸,柳州来看你了,你还好吗?”
倒了酒,也点了烟。坐在他身边,坐了很久。
我不能哭,我哭了,就是爸爸哭了,我不能让他这么不安心。笑,对,笑,倘若他知道我这么的爱他,他会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