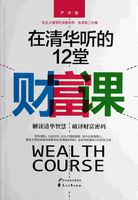从草原回来的时候,秋凉已经悄然而至了,而暑热仍在好客的人家里徘徊。在草原上生活了两三个月后回到京城总觉得有点不习惯,而且思念成为了一种习惯,思念草原的自由自在,思念容若。此情何计可消除呀,除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外,便是把一天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练字上。
洒金的信笺上飘逸而不失端庄的字是我这些天来练字的范本。想到它的来历不禁又是一阵出神。
还是在草原的时候。那天恰好不用侍驾,在营帐里练字。自从来到古代后,我每天都在练书法,此时已写得有那么点样子了,但离娟秀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练着练着,感觉有人走近,心想定是卢夫人来了。“娘——”边抬头边说,待我看清眼前的人不禁大吃一惊,那人是容若。他饶有兴趣地看我写的字,我连忙把那张纸扯下来,先发制人地说:“不许笑。”
他听了立即揉揉脸说:“没有笑呢。”看他装作严肃的样子我不禁笑了起来。他走到我身边,提起笔,蘸了墨递到我的面前。我拿起笔,他扶起我枕在桌上的手腕,说:“腰要坐直,手腕要抬起来。”边说,右手握在我手外,我的手随着他的手动。传说他的字写的很好,现在看来果然不虚传,飘逸而不轻浮,端庄而不板滞,字字顾盼相应,锋骨存而不露。
“菩,萨,蛮。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我随着一字一字地念。
菩萨蛮
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
翠衾孤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写完了,他站直身端详了几下说:“就这样天天来练就好了。记住,你练的是字又不是字。”他认真地嘱咐我。
是字又不是字?我想了想豁然开朗说:“是要领会笔意吗?”
他点头笑道:“真是聪明。”
门外的敲门声打断我的神游,“小姐,小的是守门的李贵。”听罢晓芙走到门前闪身到门外,片刻她回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和一个小小的黑色木盒,看着我甜甜地笑道:“小姐的信。”
信?我疑惑地接过信封抽出其中的信笺,看那笔迹便知是谁了,心里是按捺不住的欢喜。
芊儿:
草原别后弥日不思卿。思念之苦非春水之物可拟……
古文?!看信笺上的文字既暗暗庆幸又感到不幸。庆幸我大学时是中文系的,清代的古文阅读尚难不到我,但是在白话文被提倡之前要用文言行文,就恕我学艺不精了。
带着如此矛盾的心情继续努力的读这信。
别后数度提笔欲笺心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尺素难载余之底事,独自伤神。偶得数句聊表心思,不知所云。
落花时
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依依。
笺书直恁无凭据,休说相思。劝伊好向红窗醉,须莫及,落花时。
灵动的字化成一缕清风,把我吹得轻飘飘的。无意间瞧见晓芙双手托腮看着我笑。这鬼丫头,边想边佯怒向她嗔了一眼。她看了我的眼色笑得更欢了。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看信。容若在信里说他镌了“执子之手”图章两方,他执阳文,我执阴文。我打开那个小木盒,果然是一方精巧的图章,通透的白玉雕成一只可爱的兔子。
我提笔构思着给他的回信,这时一个自草原回来后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又开始出现在脑海:我究竟是因为寂寞才思念还是喜欢他才思念呢?
草原的天永远是蔚蓝蔚蓝的,风永远带着原野的清冽。看着碧空的云卷云舒,一天的十二个时辰里,与容若一起的时光是最令我期待,也是过得最快的,一眨眼,便暮气东来红日西沉。对自己这种期待,我常想是因为来到这个时空过于寂寞,而豁达不羁的容若恰是一个可以放开胸怀地聊天消除寂寞的人,还是因为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呢?
“……芊儿……”容若抓着我的双臂盯着我说,说:“芊儿,看着我、看着我……”
“什么事吗?”我回过神有点不安地说。
“知道吗,你看着天空神游的样子让我觉得你离天很近而离我很远,我有一种抓不住摸不着的感觉。即使你现在看着我,我也感觉若即若离。”
我浅浅一笑说:“什么远啊近的,我不是坐在你身边吗?”
“你知道你跟草原上的兔子很象吗?”他讪讪一笑,说:“它们只要听得一点声响便躲得远远的,永远是那样的难以接近。”
我无言以对,还没有人可以走进我的心底,也不相信有,因为连我也无法看透自己心底究竟装的是什么。
他翻身上马,向我伸出手来,借他的力我也上马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挥鞭,马便在原野上奔跑起来。胁下双翼骤然张开在绿色的海洋上御风翱翔,雪白的羽毛在风的逆拂下轻轻颤动,在夕阳的映照下泛出淡淡粉色。
风拂过脸的爽快犹在,他炙热的鼻息扫过耳背的感觉依旧,耳畔响起下马后他牵住我的手说:“芊儿,相信我终会叩开你的心扉。”记得我当时看着他远去的翩翩身影发了好一会儿的呆,真不敢相信在讲求含蓄的年代竟有如此主动追求的人。
容若:
自草原别后,我把我们在草原上共同度过的时光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图章上的兔子很可爱,你说过我象草原上的兔子,你也说过终有一天会叩响我的心扉。我也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心是一个小小的寂寞的城,里面春帷不揭,蛩音不响。我渴望归人达达的马蹄声。
写信时,我不断地思考着对容若的感情,是对自己寂寞的慰藉?是来自现代时对他文采的仰慕?抑或……他的风度翩翩坦率不羁真的叩开了我的心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呀。不过,转念又觉得这是自寻烦恼,既然不可思议地来到这里,无可奈何地代入一个已定的命运中,为什么不尝试接受呢?既然在这不自由底时代里遇到了一个在乎我的人,为什么还要紧闭重门独守空城呢?眼前掠过那双琉璃般的眸子,亮亮的,从那双眸子里我真切地看到他说我是他知己时的欢欣,说我象草原兔子时的痛,说要叩开我心扉时的真诚,这些都纯净得如空谷幽兰上的露珠,如珠峰之颠的冰雪,如草原广阔的晴空。
刚罢笔,敲门声又起,我忙把写好的信收起来。进来的是卢夫人,她捡起我桌面上的纸看我练的字。听晓芙说卢夫人出身书香门第通文墨。她轻轻地纸放下,浅笑着说:“芊儿的字越发的洒脱了,真有点你外祖父的遗风。”
我听了一惊,不知作何回答只纯纯地一笑,心里想我可是照着容若的字来写的呀,竟会有多尔衮的遗风,是该说歪打正着还是该说画犬不成呢?
卢夫人看了看窗外的天色说:“陪娘到园子里走走好吗?”
我顺从地答应了,随她走向园子,此时正是时近黄昏,抬眼向晚霞看去,霞光耀得我顿时双眼发黑,脚步一踉跄,身旁的卢夫人忙把我扶住,“芊儿,你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眼前渐明亮起来,看见卢夫人那双眼里满是紧张。“没事,可能今天在房里呆太久了。”
卢夫人双眉蹙了起来,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的说:“芊儿,等过了年你就要嫁作人妻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看她的神情,听她的话语,我有种错觉,面前的不是与我毫无关系的卢夫人,而是家里的妈妈。想我从小多病,妈妈经常软硬兼施地劝说我锻炼。后悔呀,如果我听话就不会在那个潮湿的晚上来到这里了,再也回不去了。想着想着眼眶一阵灼痛,面颊上滚过一阵温热。
“哟,真是傻孩子。”卢夫人边用手帕帮我拭泪边说:“别哭啊,以后注意就好了。”
“记住了……”我有点哽咽地说。
“对了,刚才宫里来人说老祖宗要见你了,让你明儿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