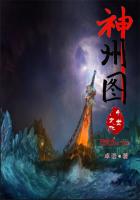“南北社诗?”路上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犯嘀咕,便故作饮茶,听他二人讲来。
“何兄,此次南北社诗照例由书容姐做我北方代表,且地点就设在我龙阳城,如此一来,不日书容姐就会归来,你恐怕……”李升却是哈哈笑了起来。
何东成面色泛苦:“所以我才说完了嘛。”
想来他那位极富文名的姐姐回来,定要他多作文章写字,以他这动兔性格,虽不至于讨厌,可时间长了,定然无异于煎熬,这才大叹特叹:“恐怕再过几日,我便没这么空闲与两位喝酒了。”
陆远摆摆手:“无妨的,何兄,大不了我与李升在贵府墙门外饮酒,你在墙内饮酒,不过是隔了堵墙,话还是照样能说的。”
他这一本正经的笑话,让李升顿时笑的更厉害。
何东成白了白眼。
“对了路兄,此次南北社诗你去不去。”李升问道。
何东成道:“路兄自然去了,往年我北诗都被南诗压住一头,我还以为北方才子太少,如今得见路兄,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路兄,这次你定要为我北派诗挣个脸面!”
路远摆摆手:“家师曾有言,读书之人当不争名不夺利,只求图个书中自在,所以怕是无法前去。”
一听此话,李升与何东CD有些遗憾:“这……倒是可惜了。”
何东成随即又道:“不过路兄,社诗你不参加,但家姐素来仰慕有才华之人,到时请你来府上小坐,你可别拒绝兄弟我。”
路远知道何东成姐姐——何书容有“易安转世”的美誉,之前也曾听李升大肆褒扬,想来定有不凡处,也实不忍拒绝他,便点点头。
他三人正攀谈间,窗外有阵美妙琴声传来,扭头一看,但见大厅中央,有一女子口戴白纱,正抚琴演奏,她穿一身丝袍,上头点缀了几多细梅。
三人顿被琴声吸引。
“此女是谁,竟有这等琴技。”
大厅内越来越多人聚拢过去。
只听这琴音时而洒脱欢快,时而又缠绵低语,高亢时又如山间泉水,恣意不凡,有动有静,意味深长。
一时间路远也是被琴声陶醉,好像见一白衣女子乘船弹琴,渡于岸上,有少女心性,却又藏有心事。
待琴声停下,众人还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这时,一个丫鬟从旁走出,抱拳道:“诸位公子小姐,我家小姐素闻半闲堂人才济济,恰此南北社诗举办在即,我家小姐为振我北诗士气,所以今日前来,一则是拜见诸位才华,二来也是想出一题,考考诸位青年才俊,不知诸位可否兴趣接题。”
这丫鬟伶牙俐齿,十分灵动,且打扮相貌都是上上之选,不遑寻常闺秀,能出如此丫鬟,可见背后主家势力定也不凡,众人再看那女子气质十分高雅,虽带了厚厚的白纱,但双眼间的神采,也能倾倒众人,这等娇丽要出题,底下人还不是跃跃欲试。
果然,下面人纷纷附和,尤其是男性:“小姐有何题,但出无妨!”
丫鬟道:“感谢诸位参与,此题其实简单,就是方才那首音律,不知哪位公子小姐能作诗一首,展现琴中意境,最佳者,稍后可与我家小姐帐后交谈一番。”
“哗!”
此话一出,底下人更是有些激动起来。
雅间内,何东成最是兴奋,路远倒还好,毕竟他是务实的人!
蒙面这种做法,其中美丑概率实在分化太厉害,路远素来不好这种手段,所以很淡定,但最淡定的还要属李升,这家伙一直呵呵笑,也不知笑啥,但看得出来,他兴趣不大。
“路兄。”何东成激动死了:“此女我好中意!”
路远:“……”
“何兄果真性情中人,好啊,人已出题,以何兄才华不妨作首诗,来技压群雄一番。”路远道。
“路兄这是取笑我呢,我这点墨水,都是从**出来的,能有几斤几两。“他苦笑了下,忽然凑近身:“路兄可有意?”
路远淡淡看着他,笑着摇头。
“那太好了,路兄,兄弟的幸福可要寄托你了。”他一本正经,十分虔诚:“路兄帮我个忙吧!”
“你的意思……”
“路兄,一定拜托了!”
“这……怕是不好吧。”
这时李升道:“路兄,你便帮他一忙。何兄情场屡败屡战,这等孜孜不懈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我要是有路兄一半才华,定要豁出命帮他!”说完,他又大笑,何有个绰号,叫:落花公子。
路远不知,李升是知道的。
何解,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
何东成登时白了他一眼:“你这厮,守住你家小玲就好,嘲笑我做什么,若小玲日后跟别人走了,看不伤心死你!”
他此话一出,李升脸色立刻红成一片,赶紧反驳:“小玲定要做我媳妇的!”
何东成老神在在,一副那可不一定的模样。
李升登时不说话了,似乎生怕何东成这张破嘴一语成谶。
另一边,路远实在架不住何东成殷切期盼的眼神,心里那个郁闷,前世读书帮人写过不少情书,结果穿越了还得帮人写“情诗”,他娘的命运总是惊人的相似。
不过话说回来,何东成同志有这么一颗骚哄哄的赤子之心,还算符合路远的胃口。
毕竟泡妞也是路远最爱,可惜他已经在两人面前树立了文人形象,所谓自己装的比,跪着也要装下去。说实话,路远这货,骨子里就是浪的。
算了,帮就帮吧。
他一敛袖子:“笔墨伺候!”
何东成立马俯冲出去,呼吸之间,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半闲堂别的不多,文房四宝和酒,要多少有多少。
路远闭上眼睛,回忆刚才的琴声,那琴声最大特点,就是轻灵欢快,但欢快中又浮出诸多情绪。
要做这样的诗……
路远在自己仅剩不多的唐诗宋词中苦苦搜索。
“有了!”他骤然睁眼,挥毫泼墨。
“有琴声,当有词意,华朝诗风很浓,我便反其道而行,以词来铸句!”他心中暗道,同时手起笔落,宣纸上字字显现,不多时一首新词,便热火出炉,粉墨登场。
何东成一看“诗名”:“如梦令?”
他嘴里念叨: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诗……”何东成读来朗朗上口,但以结构来说,这首诗,却根本算不得诗。
李升也道:“这是什么诗?”
路远将笔搁下,摇头笑道:“此乃词也。”
“词?”两人相觑,一副不懂。
路远将宣纸给他:“何兄,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自己了,祝你马到功成吗。在下尚有事情,得先走一步。”路远起身,拱手抱拳。
“既如此,何兄,我也祝你成功。”李升也起来。
“哎,你们,都不等我嘛!”
见两位损友一走,何东成手里拿着宣纸,心中对二人如此不仗义,还是深深鄙视了一下。
不过这所谓的“词”倒是十分新鲜,读来气场十足,十分吸引眼球,是部好文章。
这就够了!
何东成一时踌踔满志:“小娘子,我何某人这就来了!!”
————
而此时路远已经走到楼梯旁,迎面有位老者,正佝偻身子,靠着墙壁眼神半眯,睡意深沉。
路远登时止步,心中一惊:“王管事,他怎么在这!”
便在二人擦肩而过时,王伯倏地睁开双眼,打量了他一眼。
“此人……”王伯眉头微皱,只觉路远背影有些眼熟,却又无从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