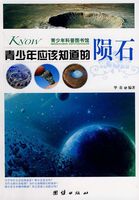月亮,像刚刚充了电,晃得我有点胆颤!我希望它暗点。可暗了,又看不见割草。我心里充满着矛盾。
父亲在月光里蹲着割草,让我“打更”,要是远处来了人,就扔过去一个土块子,父亲就躲在树丛里。父亲说,实际晚上割草,没耽误白天干活,也没什么。怕就怕两个人:生产队长和看山的。别人谁管这事?这两个人也倒不一定管,但还是不看到好。我就不同了,我谁都怕。我还在上学,学校团总支书记整天教育我们,要同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划清界限,父亲割草卖钱,算不算资本主义?我已经写了入团申请书了,背地里却干这事儿,要传到学校去还得了么我谁都怕。
但父亲又说,你不是喜欢运动服回力鞋么?等卖了草,就给你买。
父亲的承诺,对我诱惑太大了。
我站在一棵柳树后边。我能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我。
借着月光,能看出去挺远。
我总觉得远处有人走过来,那黑影在动,在慢慢地朝前移动,只是走得太慢。我的心,也在黑影移动里砰砰乱跳。眼睛看酸了,我闭上一会儿眼睛,再睁开,黑影还同刚才一样。
已是秋冬时节,山还封着,不让人去动一草一木。但父亲割草这地方,是个沟膛里的荒草甸子,大概地力没劲吧,草只长到半尺或尺把高。父亲只好蹲着割。我说,这草太矮了,要是长高些多好!父亲说,多亏它长得矮。父亲又说,长得矮,队里才没人管。长得矮,别人不屑割。我感到挺有意思,有时缺点也恰恰是优点了。但只是苦了父亲,“脱节”放,草就显得高了。草太矮,稍不小心,就会割到手,父亲雪亮的镰刀频频在手指前切割,发出“刷刷刷”的声响,真让人捏一把汗,我要帮着割,父亲不让,怕我割到手。再说,他也怕我割得茬高了,割瞎了草。父亲告诉我,山上和地上高草很多,但那不让割,也就不属于我们,而这种草,才是我们得施展地方,这很不容易呀,要格外珍惜它。我说,这是什么草,长得这么不起眼?父亲说,你可别小瞧它,那年闹饥荒,村里人全靠这草救命了,大家叫它“还阳草”哩。父亲告诉我,这种草长得快,割一茬在四五天就又长出来了。只是,它就长尺把高,不往高长。那一年,村里人足足割了有20茬啊!我说,不是有很多种草么?父亲说,只有这种草长得嫩,嚼起来甜丝丝的,而且养人。别的草都试过,不是老根咬不动,就是吃了胃疼、排不出大便。
我顺手拽了几根草嚼嚼,虽然已经老了,但仍品出丝丝甜味来。我不禁对这草肃然起敬。我又突然对父亲说,这种草救过命,就别割了吧?父亲的话又令我大出意料:孩子,草的寿命只有一年,你不割,它也瞎了。割了,明天它才发得旺呢!我只记着这草的往日功劳,才提出这个建议,却不知差点帮了倒忙。看来,干什么事,光想得好不行,还得对。
只要是有点月亮,父亲就去割草,每天都割回来一扛。我看着家里的草垛一天比一天大,想着父亲的承诺,情绪也随着草垛往高长。
这天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给我买的白色回力牌运动鞋和一套带金属拉链的腈纶运动服,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迅速回想着,我们班60多名同学里,我是第三个有这些新潮东西的这天晚上,月亮好极了!我提议也去割草,父亲却瞪我一眼,说,你好好读书,别管这事我很不理解。
一连许多天,父亲吃完晚饭就出去,很晚才回来,却没扛回来草。
我很想提割草的事,但见父亲天天晚上早出晚归,也就没提。
这天放学后,同学刘德昆问我,你爹割草卖多少钱,天天晚上挨斗哇!我急忙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刘德昆伸伸舌头,不说了。
父亲被人“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穿白回力鞋和运动服了。我感觉它们像偷来的,怕让丢东西的人认出来。还不仅仅是这样——我感觉它们像囚服一样,穿上就是一种不光彩的标志!我真想把它扔了,但我没敢,也舍不得。
我将它们放进地下的木箱子里。
我再也不想穿它们了。
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学校可别知道我父亲卖草的事……那天在校门口,女同学徐丽文指着前边一个高个子老人说,你看,就这老头儿,昨晚上在俺村里检讨,因为割草卖。我一看,连忙低下了头。我同父亲走个对面,父亲刚要张嘴,我却扭过脸去。徐丽文问,哎,你们认识?我说,不认识。
回到家里,我和父亲谁也没提这事。
父亲说,孩子,你还记得还阳草的故事么我说:快别提什么草了我父亲愣了老半天,说,对对对,不提了第二年,父亲和许多人,都被平了反。
我想起曾经对父亲……父亲说,孩子别提了,你小,我不怪你。
我想起了回力鞋和运动服,我特别想穿它们。我甚至暗暗地想:省点穿,多穿些年,它们记载了我未成年时期一段难忘的往事。
我打开了木箱后,发现它们已让老鼠咬得所剩无几了。运动服除了几块不成形的边角,就是一堆破棉絮。回力鞋还有半只完好,鞋窠里边是鼠窝,还有四五只小鼠崽在蠕动。
感悟箴言只要是有点月亮,父亲就去割草,每天都割回来一扛。我看着家里的草垛一天比一天大,想着父亲的承诺,情绪也随着草垛往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