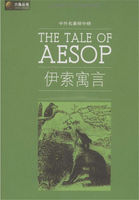天暖些了,但那是很有限的暖。屋里,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微小的尘粒就在光柱里旋转,融融暖意只进不出,让人幸福地感到:天暖了。但一出屋,这种感叹就变味了——冷风嗖嗖地吹过来,脚跟着脚,一会儿工夫,我就得缩着脖子,手操袖筒里,或干脆倒退着走。
这也抗不住。
我的胳膊和膝盖处,棉花没了,就剩两层布了,还是抗不住凉风。要是遇上一堵墙,背背风,就暖和多了。但我不能这样,我得和大兰子去捡地浆皮。而地浆皮全长在河边柳树毛甸子里,那里怎么会有墙啊风不是总刮,有时也歇歇。但它歇了,我们也不感到暖和。地表层虽然化了,还没化透。地肉里的冰已经憋一冬了,不想再憋了,一鼓劲儿,让融化的寒气冒出来,寒气一股接着一股,我们就受不了啦。
但得挺,挺住,才能采回地浆皮呀平地积雪全化了。远远望去,地上还浮着一层淡淡的气体,气体里闪着光。细看,又不像光。再细看,又像了。走到近处,又什么都没有。而再往远处看,还能看到像气又像光的东西。我感到挺有意思。但我却不去深想——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有意思而又弄不明白的东西太多啦,想也白想。不白想时也有,却很少。
大兰子见我总朝前看,而且不时还现出专注的样子,说,你看什么呢?我说不看什么。她又问你想什么呢,我说想地浆皮。大兰子一乐,说还没到柳毛甸子,你想也白想。
地浆皮只长在柳毛甸子里。它色泽形状像黑木耳,吃起来感觉也像黑木耳。但它们不一样。黑木耳长在腐树枝上,地浆皮长在地皮上;黑木耳有时长成堆,地浆皮却一张张平铺在地上;黑木耳较厚,地浆皮较薄。它们也有共同处:喜潮湿。
我对地浆皮不是太喜欢,嫌它有一股淡淡的土味儿。我曾埋怨母亲说没洗净,母亲说,傻孩子,地浆皮就是这股味儿,你想,它紧紧趴在地皮上,能不熏出土味儿吗?我并不觉得母亲说得特别有道理,但一时又想不出特别有道理的话,就不吭声了。但大兰子说地浆皮好,说它有什么什么树(素),我挺信。人家大兰子家是沈阳下放户,光书就拉来一汽车,什么不懂?大兰子一说,我才想起母亲说过,吃地浆皮去火,宽肠。吃地浆皮可以不放豆油,吃地浆皮下饭。仅凭省油这一点,就不简单——我们常年(除了过年过节外)也很少见到油珠呀!不过,我捡地浆皮,却不是为这个,而想着大兰子家里那副军棋。
我从没见过那东西,而且也买不起。再说,我们夹在山褶纹里,能买得起也买不到哇两双鞋在柳毛甸里铺着腐叶的地上踩。看上去是腐叶,一踩一个坑,水就出来了。一抬脚,腐叶又弹起来,却看不到水。这些无形无色的东西,比掩藏的特务都狡猾呀。它悄悄浸在大兰子胶鞋底上,被挡回来了。浸在我的家做布鞋底上,就润进去了。虽然水没淌进去,但鞋底已悄然湿透,冰凉冰凉。我却顾不上这些,只想快点找到地浆皮。我知道,腐叶太厚的地方不长地浆皮,而没有腐叶的地方也不长地浆皮,只有有点腐叶又偶然长点青苔的湿润处,才长地浆皮啊我终于找到这样的地方了地浆皮已被湿地气给鼓动起来,铜钱大小起伏无致地躺在那里,连成一片。它们像被泡起来的木耳,湿润而亮泽。一找到它们,心里蓦然涌起一股热情,但抓到手里,却是凉凉的。我和大兰子捡完一小片再去找,找了再去捡,总因为找不到而东跑西跑。春天虽然来了,但除了“缓阳”而生的地浆皮,什么菜都没下来,捡地浆皮的人也很多。偶尔在树根朝阳处,我看到一小撮刚发芽的绿草,就说它们是“大头菜”,用木棍抠半天,却找不到蒜头。大兰子格格笑一阵,说她知道是什么了,我侧耳细听,她却说是标准的青草。我们就乐一阵子。
大兰子捡地浆皮不如我。我每回都给她一些,她先是不要,我坚持给,她就要了。以后,我再给她,她也不说不要了。大兰子问我,你家人爱吃地浆皮吗?我说不爱吃。她要得就更坦然了。我也问她家人爱吃吗?大兰子一歪脑袋,两个小羊角辫一甩,说当然爱吃啦实际上,捡地浆皮也就那么十几天时间。阳气转回来,山和地一泛青,野菜出来了,谁还捡地浆皮但我和大兰子的交往,却只是捡地浆皮。
一放学,我就找她去。
一天,我眼见柳树细枝小手一划拉,大兰子头绫子蝴蝶般飘地上了,像一团火。我捡起来递给她,她却说,我手湿,你把我那只也摘下来吧。我照办了。她又说,你先揣兜里吧回家的路上,大兰子说,她爸爸的右派问题没办完,明天她就要回沈阳了。明天?我问。大兰子点点头。大兰子还说,我知道你喜欢那副军棋,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赶紧说不要——我没想到大兰子明天就会走,我不要她的军棋,她也许会不走吧!我一着急,就抓住大兰子的手,说:“那、那你别走了”。大兰子脸红了。我突然想起什么,就松开了手。
大兰子跑远了。
当晚,大兰子同我告别,我仍然没要那副军棋,却说,你已经给我纪念品了。大兰子没明白。我倒害怕她明白过来,就说,你走了,能给我写封信吗?她说能。
我悄悄留下了那副红绫子。
后来,我们相互通了几封信,只提到各自干什么,共同话题只有地浆皮。信就越写越短。我曾经想写长点,或者来点什么花样翻新,但一提笔,眼前却只有或清晰或模糊或满世界旋转的黑里略略染点绿意的地浆皮……我想大兰子是大城市人,当然不会像我这么没出息,她摆弄汉字像我摆弄泥土一样随心所欲吧?可是,她写给我的信居然也越写越短。终于——我们各自消失在对方的视线里。现在,我倒是偶尔还想起这件往事,不知道大兰子是不是也有这个偶尔我回到老家去,看到一群男孩女孩们在一起玩,就想起了大兰子,当然只是想想而已。
我突然想问问地浆皮的事,又突然觉得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些孩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地浆皮为何物吧感悟箴言看上去是腐叶,一踩一个坑,水就出来了。一抬脚,腐叶又弹起来,却看不到水。这些无形无色的东西,比掩藏的特务都狡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