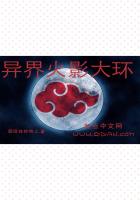要要要与唐晓峰先生商榷名分问题
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在《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上发表一篇《名分问题》的文章。该文从《商君书》谈起,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对人间世象每每有独到发见,读来兴味盎然,好像嚼一枚非常爽口的橄榄。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再找不到比唐先生更详尽的引文、更生动的例证和更全面的观点。稍稍感到遗憾的是:文章虽然一一区分人们对名分看法的异同,提到不少有关名分的趣事,关于名分根源的剖析却不是那么透彻,很多部分拿文明这个词来搪塞敷衍,不愿触及问题的核心,绕了很大一个圈子,仍徘徊于问题之外,仿佛一位没有鼓足勇气约女友出来约会在门外转悠的小男生。
我猜想,唐先生可能没读过——或者写文章时没能想起——“洁白的像羔羊一样的邪书”《白鲸》中第89章的内容(可以作为法学系入门生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也可作为法学院教授级人物常备的醒脑剂),里面对所有权的问题,阐述得既明白又深刻,先从美国捕鲸者以“既是立法者又是律师”立场出发制订的一套制度谈起:“1.有主鲸属于将鲸拴上的一方。2.无主鲸是谁先捉到就归谁的合法猎物。”然后引用一则英国事实案件(限于篇幅省略),援证“这两条涉及有主鲸与无主鲸的法律条文,仔细想想,原来就是人类所有法律体系的基础”,由此得出“从这一切看来,不正好说明,谁有所有权,法律就整个儿向着谁吗?”惊世骇俗的结论!我们的引用应当到此为止,按照“不过,假如有主鲸原则应用范围相当广的话,那同出一源的无主鲸原则就更广,那是全世界都通用的”的逻辑,麦尔维尔先生把“无主鲸”的概念推而广之,一番恣意妄为的比喻后,仿佛被他冰凉的手指着鼻心发问:“还有你,亲爱的读者,不也无非是无主鲸和有主鲸二者兼于一身吗?”到这里,就不单单是围绕所有权展开的题外话啦!
《商君书》中被一百多号人赶得疲于奔命的倒霉“兔子”,正是“无主鲸”的意思,只是不如其意思显豁罢了。就像“名花有主”的女人,除了有心勾引的登徒子,是没人愿意染指的。有趣的是,《白鲸》中律师为说服法官所举的例子,恰恰是整体物化了──即所有权化了──的女人。我想,历朝历代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看到这则“没有名分的兔子”的比喻,估计更有感同身受的体会。
“从‘野的’东西变成有‘名分’的东西”“建立名分是确定秩序的需要”,名分的本质是所有权,是“性本私”的人性面对社会资源确定的根本性基础,给“有主鲸”添加了详尽可靠的刻度,把所有社会的、“野的”(即自然的)可供支配的事物都给予一定分配形式。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正是这项原则具体法律条文上的体现,是小我的观念社会意义的认可与财产上的确立,在所有权问题上划分出人性得以施展的空间与平台。正因为是所有权,名分才不能“借用”,而只能“专用”,应当看到,有了名分,自私的本性才像葡萄藤一样有了得以攀附向上的竹竿。拿唐先生文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例子来说,这当中名分的变化,已经从“无主鲸”变成超市明码标价正待出售的鲸肉,“得其价高者售之”,从占有阶段进入到分配阶段,这个变化是惊心动魄的。统治者先将无主鲸据为己有,然后将一切无主鲸明码标价,按照等级制的方式分配下去。正是在无主鲸转为有主鲸的过程中,法律没有渗透到的角落,出现各种形式与实质上的空当,投机者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孟锦云问过毛泽东这个问题:“《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呢?”毛泽东的回答是这样的:“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为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也就是说,周朝给擅自脱离组织的韩、魏、赵三家名分,自坏纲常,非法变成合法,“名不正言不顺”变成顺理成章。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刘备自认“中山靖王”之后,都为了从名分上取得优先权,在名分上认个正统,要在“无主鲸”的身体上插上一点与己有关的标记,这个标记物就是《白鲸》中提到的“一根桅杆,一叶桨,一节九英尺长的缆索,一根电线,或者一块蛛网状织物都可以”,在现代社会,这种媒介物当然地带有了现代气息:一张相片,一纸契约,一份DNA鉴定报告。
据说历史学家分析李闯王失败原因有重要一条:李闯王取得革命阶段性胜利后,没有重新建立起相应合乎秩序的税收制度,没有将各种东西的所有权与等级制挂起钩来,没有建立起名分及有关的一套游戏规则,依旧打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还像“打土豪,分田地”时期一样征敛革命经费,最终导致财政拮据,根基不稳,兵败京城。这是“有主鲸”把自己当做“无主鲸”的例子,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坏纲常。逮住了无主鲸,却不使“无主鲸”变成“有主鲸”,听凭它像一匹烈性子野马一样狂奔乱跑,忘了打下烙印,套上缰笼。这样子自毁长城的举动,真令从事税务工作的本人大惑不解,大惑不解之余又唏嘘不已,就像饥肠辘辘时错失好一块肥肉时的怅惘。
将山岳纳为正统,则是帝王将相在将无主鲸占为“有主鲸”后,洗干净手,披上餐巾,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美餐时玩的把戏。至于为何挑上名山大川,只不过使人的卑微渺小有个宏大神秘的彼岸性参照物,借以迷惑被等级制式的名分训练得失去了天然嗅觉的愚众大脑。他无法把从左手抢来的政权交给右手,只好寻求一位莫须有的更高教主递到自己手中,希望有条“君权神授”的无主鲸归到自己名下,使老百姓有个一望而知、超越逻辑之上的心理认同,保持仰望的姿态,他本人则站在圣像肩膀上一同接受膜拜顶礼。
唐先生所说“名分是笼套”不错,可我不大同意“绝大多数随俗入世的人还是喜欢名分,争取名分”看似清高的观点。除非他能像陶渊明一样超脱,“久在樊笼里”后,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亩三分地垫底,挺直腰杆,“不向五斗米折腰”,守着老妻愚子过日子;或者像孙悟空一样看不起小到不能参加蟠桃会“弼马温”的职位,愤然大闹起天宫来。除了以上两者,我看不出两条路之外还有其他道路存在的可能。这个“名分”的樊笼,不单遍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人间,还有拘禁人们可以量化具体化的食欲性欲,还有无法量化具体化的求知欲、表现欲等大小不等的欲望,内外结合把我们牢牢地控制其中。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谁会愿像鲁宾孙一样到孤岛上过与世隔绝兽一般的生活。真正套牢我们的,并不是外化了的名分,而是深植于内心的大小欲望,欲望是主谋,名分只是帮凶。你不会看着别人入有房、出有车不眼红,发现有人娇妻美妾、左拥右抱不心动,大冷天冻得瑟瑟发抖、眼瞧着那位身着裘皮大衣招摇过市,一点岌岌可危的清高还要坚守阵地。那个时节,一句“知足常乐”万金油般的良药是会失去最后一点效用的。
唐先生在人的定义上补充了一条“人喜欢名分”,人当然有很多区别于动物的方面。可是列出一条,不说是大树主干,至少应当是主要分支。“人喜欢名分”不错,可是这个说法,只是“人性自私”加上虚荣心的结合反应而已,列出这条,同样可以列出千万条类似的说辞,人这个定义会变得不胜负荷。社会的总资源与人的欲望的总和相比,总是那样的有限和微不足道,任何多的资源都仅像一滴水渗入大海一样不见踪影,人喜欢名分,只不过是欲望在所有权有限的情况下,在虚荣的共同作用下的分支与显影。
人可以到宗教中寻求寄托,在膨胀的虚荣心里守望着无限延伸的自我,但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子,大多数人不服名分,不过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怯懦表现而已。至于“死了也还要个名分”的,无非是“我”的概念深层次的延续,是人的求生欲望与虚荣心在社会层面根深蒂固的反映罢了。
《红楼梦》里贾珍为贾蓉谋到一个官职,只是为了秦可卿葬礼的灵幡经榜上有个叫得响的名分。没有名分的人在社会上的状态,就像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赤条条地没有包裹,会格外地感到寒冷,政治状况一栏中的“清白”仿佛直指家庭经济状况“一清二白”般的一语双关。我认识一位官场小人物,常在冬天调侃没有谋到一官半职的人:“大冬天来啦,没有顶帽子怎么行,有顶草帽也好。”“有了草帽,当然想搞顶皮帽戴戴”,寓怒骂于嬉笑,究其根本,还算话糙理不糙。
名分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从来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只要有个主要名分,其他名分都会接踵而来,成为主要名分的点缀,像一群小星星簇拥在月亮的周围,共演星月争辉的胜景。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许多领导,一定是学者型,一定是客座教授,一定是书法协会的主席,都是自然而然、舍我其谁的。有些人会嫌帽子太多而记不住,名片上的职位与头衔,会夸张到连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中书本大小的名片都无法印制明白,不得不像纳粹时代一则笑话所说的那样,勋章无数的戈林先生在正面衣服挂不下勋章时,居然在衣角下添上“转背面”的字样,好让瞻仰者参观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