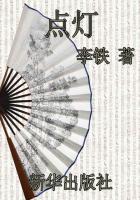树林村除了几家大户外,天灾欠收的今年,收下的粮食,不够半年吃。王二叔三口人,两个劳力,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只够半年食用。村里人们说二叔好管闲事。的确他走着站着,都在琢磨:“穷哥们的穷日子,得好好盘算盘算呢。冬天都闲着,把点粮食吃完,开了春,既没种子,也没撑肚皮的,怎能饿着肚子闹春耕呢?俗话说穷汉盼来年,春不种则秋不收,到时候又是旧病重犯——揭不开锅。岂不是越来越穷,穷根子越扎越深,致使一些穷人外逃,妻离子散。到那时,后悔也晚了。”
为这,二叔、老树找到严成和刘二元商量过,他说:“从秋收、秋打完工之日起,开展粮食不够,莜麦秩子、玉米轴子、豆皮、秩秩草草代。家家户户把莜麦秩子、玉米轴子碾碎、压烂,掺粮混吃,这叫老鹰吃鸡毛——胡乱撑肚皮哩。到了春暖花开,草青,菜绿。挖点野菜呀,捋点树叶儿,就能胡乱塞饱肚子,也就饿不死人了。”
“你这主张挺好。”严成抓了王二婶的烧火板凳坐下来,“挺及时,常言道:‘饿死老娘,不吃种子’。穷人有穷法,冬闲不动弹,就可少吃俭用,掺糠、和菜,秩秩草草也能代粮。人本来都姓‘制’嘛,‘制’到你吃秩草的地步,你非吃不可,不吃就没命了。就得走这条路,不走不行,姑且吧。明春要提早动手,多种,种好,秋天就能多收点儿。人们不是常说,不种百亩,不打百石。嘿嘿……”他说完,拿铜瓢舀上凉水咕咕喝了。
“玉米轴、莜麦秩、山药蔓子可吃。没有任何味儿。”是刘二元咳嗽完深有体会地给大伙介绍,“一斤掺上三两粮,也可充饥。凑乎吧,谈不上讲究,将就着饿不死人就行了。”他说着呵呵冷笑了。
“咱这伙穷人,一说就说到一起了,”老树插嘴说,“够合套的。团结起来就是胜利,我们的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啊。”
“爷,房上有两只喜鹊哩,我想要它呢!花花的,好看!”小枝说着拉住王二爷的手,要他去捉喜鹊。妈妈见他们有事商量、讨论,就把小枝领去。
梁生见群众起来搞渡荒自救,就让王二叔、严成、刘二元、老树和张金枝,组成一个临时“穷人会”,公开组织穷人节约渡荒。二叔亲自跑上街去,满街鸣了锣,说是穷苦大众都到十字街,共商渡荒大计,要安全顺利去渡灾荒,争取来年多种多收夺得丰收。村民们一会儿满满挤了一街,都说王二叔是个好人,想了穷办法,也是好办法,不这样办就得挨饿等死。他们说:“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可走!不管吃的好坏撑了肚子就能保命。”那个白胡白鬓的刘财把旱烟袋一扬一扬地说。“凑乎吧,有啥好法子呢,把冬天渡过去,一开春水流草青就饿不死了。”拄着弯头拐杖的刘奶大声说。
但也有的人不赞成这个渡荒的办法,吴长梅和她妈妈老梅,还有她妹玉梅,娘们三人听了大伙酝酿讨论,就觉得稀奇可笑,她们笑了又笑,笑弯了腰。
她娘们的性格大致有所仿佛,因为有血缘关系的遗传。共同的特点是少笑,即使笑也是嘲笑他人。她们躲在暗处窃窃私语,要不就干脆跑出来搞挑恤去叫骂。还有什么的有滋有味地咂吧着嘴,洋洋得意地眯缝着那双不安分的眼睛……
人们都盯着她娘们的傻笑,很讨厌——讨厌她们的冷笑,因为冷笑是无情的,冷笑是嘲弄,冷笑是……
“畜牲才吃那东西,人莫非是畜牲?”老梅笑得两手捂拄了嘴巴。她这污辱人格的话,真引人生气,让人讨厌极了。
“没法过日子的穷人,不怕笑话,因为这不是做了什么丑事,受人耻笑。”金枝忍不住心中的恼火,大胆大声在人群中说。但她瞅见老梅娘们三个,顿时变得怒目而视,对金枝的说法不满。认为她是化子,是外地人,外地的“孤狗”还想咬“在地虎”哩。她娘们觉得金枝话中有刺,则反唇相讥起来。
“我笑你哩?化子!王八蛋!呸!你是啥人,还想欺负我娘们?”老梅动着火性骂金枝。其实她娘们是嫉妒着她,黑眼着她。“讲理,别骂!咱们素不相识,有啥过不去的,谁有粮就别吃,还用生气动性了呢?”金枝辩解说。老梅说:“金枝,我问你,你说‘丑事’,‘丑事’!谁有啥‘丑’事哩,讲!”她说着,就跑过去撕扯她的衣服,抓着她的头发,就咦咦地哭起来。二闺女也跑上去耍泼,张嘴咬,伸手打。金枝既不张嘴,也不动手,只是防备、躲退,——自己保护自己。她躲到丈夫跟前。老树见下不了摊场,忍着性儿憋着气,一手吊溜一个,款款把她娘们放回原地去。
金枝两眼泪汪汪地哭了,老树不让她跟她娘们争吵。王二叔、严成走过来,要金枝回家去,她听着二叔的话,就慢慢地离开她们到另一边去。她娘们总算不言语了,像窝狗一样,老狗不叫,群狗都不吱了。散会的第二天,村里的穷户,很快就行动起来,有的用碾子碾,有的用磨子磨,昼夜不停地加工代食。老树手勤、腿勤、力气大又吃苦,把王二叔准备好的代食原料,抽早搭晚全部磨成面。
张金枝给打工干活的丈夫和两个娃吃点掺粮的两掺面,自己每日三顿饭,全吃些纯代食,没多长时间,她消瘦成个皮包骨头架架,脸上、身上,肿得明光明光——得了浮肿病。丈夫见她每日就吃些代食品,就与她换饭吃,要不,强迫她吃些粮食饭,可她坚决不肯,她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就够了。我清楚,我在家里,不会饿死的,现在是困难时期呀,过些时粮食会多起来的,还用吃两样饭呢?”她说完,两眼盯着他,像是要他答应她的请求。
“你别看我,我不会答应你,一万个不答应!今天吃好,明天讨吃要饭,我也心甘情愿!”他说着,抓着她的双手心痛地不放。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他生怕——他清楚,她的善良与诚实。金枝她哭了,她接受了丈夫的恳求,此后她与全家人吃了同样的饭。她也领教了丈夫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共挡”的夫妻关系。
洗完锅,她坐在锅台上一声不吭,心里着实难受:受苦人吃不好,怎能扛工干活呢?幼年的孩子吃不好,要哭要闹;全家人都吃好,粮食从哪里来呢?她唉声叹气地站起来,摸摸粮袋袋,看看面缸缸,曲着手指思忖着,像是盘算着日月,哪月开始挖野菜?何时开始吃新粮?盼日熬月的穷光景,过一日如同一年。她常说穷日子难过,穷光景难熬。
她以为,穷人生来就是受罪。降生时是哭着来的;幼年、少年跟着妈妈吃糠咽菜;成年时携儿带女生活不如牛马。何时可摆脱这苦难的深渊呢?何时自己能给自己做主,取得人生自由呢?丈夫扛工要走了,抓起铜瓢要喝生水。因为扛苦工太累,须要多喝水。“老三!你不想活了?”她夺去了瓢把。批评他不注意身体的坏习惯。他说:“穷人讲究少,因为讲也没用。”他又说:“我喝惯了,没事儿。”他笑了。
“你不怕,我可怕呢!”她说完泡了碗哄孩子的糖水,她心痛他又当牛变马作苦工去。她所以要照顾他,心痛他是……
他喝着,她看着,胖胖的他成了个骨头架架,她的眼泪偷偷地又涌了出来。这苦,啥时能吃够呢?这牛马车何时可拉到头呢?他不喝了,他觉得不是喝糖水,而是喝伤心的泪水。他叫了声“金枝,”两人紧紧贴在一起不动了。
忽然,大门外有人吆喊王二叔,说是刘二元家里哭哭啼啼。二叔一听就知道他家里出事了,就忙从瓮里装了些粮食跑了去。金枝让老树也装了一嘟噜。
二叔和老树走出大街,只见闹饥荒的贫苦农民已漫沿上了街头。他们东躺三个,西睡两个,遍布满街。群群伙伙的老弱病残,睡在土混混的墙脚下,不住地呻呤,不时地喊着“救人救人”哀词苦调;大街小巷的破屋里传出了不懂事孩子的哭声与吼叫声。这叫饥喊饿的痛苦声此起彼伏,吞噬了人们的灵魂;这尖厉痛心、饥饿声的聒噪,引起了好心的二叔、老树以及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对地主剥削阶级的愤恨。使他们肝肠寸断,心肺碎裂。
忽然一股狂风带着沙土掀动着人们的衣服,撕扯着人们的头发,扑打着人们的身躯,仿佛在告诉着人们:起来,起来……深受苦难的人们!
“妈妈,呜……”三岁的江兰撅着屁股嚎着,妈妈用手指往出掏屎,掏出的不是粪便,而是干沙沙的糠皮、莜麦秩子和玉米轴皮皮……吃上这些东西,孩子们怎能便出去呢?
粪便掏完了,孩子也不哭了,可是红艳艳的直肠从肛门拉出了一堆。人们说,没吃没喝的穷人,孩子缺营养常见的病变——女儿嚎啕、喊叫,母亲陪着去掉伤心的眼泪。不足六岁的大闺女兰兰躺在院里喊着,叫着,拼命地号啕:“便不下去疼呀!妈妈!妈……”
妈妈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谁嚎叫,去看谁。当母亲的为儿女着急,为儿女流泪,为儿女揪心裂肺!如能替,真想替她俩……她半点办法也没了,办法在哪里呢?她只能去掉泪。刘二元肺气肿加浮肿病,躺在炕上成天不起,也不说话。二叔送来了粮,忙去磨了面。二元慢慢地爬起来抓住二叔的手咳嗽完,上气不接下气地掉着眼泪,不说话。二叔责备他说:“家里出了攸关性命的大事儿,你为啥不说话?唉,太多心啦。以后可别这样,穷朋友有难共挡嘛。”
老树麻利地两手帮助二元嫂做了小米粥。刘二元从内心里发出了笑声,他要下地了,他觉得他没病了,他要帮老树做饭去。老树见他摇摇摆摆,忙把他扶上炕去。此时的二元真的像似没病了——显然心理反映有时也可代替生理作用。他依然像家兔那样嬉戏,像家犬那样逗闹。他坐在烧火板凳上,大口大口地吃着小米粥,觉得怪香,香得无法形容,无法相比。他啧啧着嘴,品尝着滋味儿,说:“二叔,我又死不掉啦。”
老树略加思索地说:社会上的富翁吃啥都不香,而只有贫穷知困苦,而困苦知甜蜜,是千真万确的。
两个女娃娃一边吃,一边占住一些,不让别人吃。妈妈说孩儿们饿草了,不懂饥饱。吃得太多会憋死的。妈妈就把多余的粥藏起来,以免出事。这是他家的常规。
“二叔,”老树说,“穷因好找,可摆脱就不易啦,我认为。”二叔点点头,表示赞成。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两个娃娃吃饱了,跑出了院去,玩着捉迷藏。因为他们是无知的孩子。
“老三,你穷还是我穷?”二元拍着老树的肩问。
“都穷。”老树说完看了看二元——他以为他又开玩笑了。
“是都穷,但你穷而有志,有很大的力气,又有较高的文化。”
“你呢?”老树盯着他问。
二元拉着他的手,哈哈笑着,“我一无所有,只有声(身)半(一身虱子,半声咳嗽)!”他说完,真的捧腹半声半声地咳嗽起来,又咳嗽又笑,斗得大伙都笑起来。他又打开了话匣:“长梅会装神变鬼,我会占卜相面!”他看了他的眉面五官,又细细地瞅着他的指纹说:“你虽遭了大难,但有贵人搭照;你你可报国恨家仇,因为你是个不平凡之人,你后继有人,你要当官呢。”“谢谢你的福口。”老树笑眯眯地回答。“只要我作了官,不会忘记你的。”二元把手伸得老长向老树要八块白银,还说他比长梅少要的多哩。
“等以后再给行吗?”老树恳求他说。
“不行!咱这个行头不搞赊欠——人常说赊三不如现二哩。”老树推着他的两手说,等有了多给点。二元说不行,向二叔借上。二叔说他也没有,只能给中间当保人。不失风趣说话诙谐的他斗得大伙笑了。言归正转。
“卖命挣下的那些粮要了多次不给,就算白干了。”老树说。
“他说啥来?”二叔不解地问。
“他说县里没有钱——有人说那虎皮还在他家存放着。”
“你动硬的,他就不敢不给。”二元挑动说。
“不行,动硬的我就得与你们分别,我不想走。你给去试试看行吗?”他看着二元说。
“我更不行,做正事我做不了,开玩笑说没的我感兴趣。”他又说,“我斗不了他,方围百里他出了名,谁说起他来都很头疼,他的外号叫‘害断根’,又叫‘引魂帆子’。听了他的外号就知道他的人品。因为外号就是代号,代号是人们根据他的特征取的。你说你不能跟他斗,我看你跟他斗定啦,因为你不与它斗,他要与你斗哩。而且只有你才能把他干倒。”二元将他的军说。“嗯……”老树犹豫了——但他认为条件不成熟。又说:“那不行,慢慢来嘛。”二叔磕去旱烟锅里的烟灰,“我看看你砍树挣粮的数据。”
老树解开裤带从很深的裤袋里往出掏,不防把两个证件落在炕上,二元忙捡起来一看是“党员证”,他喝了声,吃惊的说:“这是什么证件?”他己变成另一个他了,两眼圆睁,脸颊红。“这……这……”老树慌了,灵机一动把两个证件抢到手里。“对不起朋友们!”他说完要急忙逃走,二元抢先动手了,他说:“什么对起对不起的!把他捆起来!妈的,共产党杀人如割草,这还了得!”他说着就站起来要收拾他。他的态度强烈而严厉。二叔看看二元,又看看老树,就暗暗笑了——老树两眼通红,呼地站了起来,“嚓”地扯下一扇破窗就打刘二元。在场的娃娃女人“哇”地惊哭了,哭他要干人命了。“住手,住手!”二叔见老树要打二元,他把毡帽摔在炕上,忙站起来拉住那扇破窗,掏出自己的党员证给老树看,“我们是一家人!别误会!二元是与你开玩笑哩。”二叔在着急中去解释。那刘二元也昏过去了,他慢慢地也掏出自己的党员证给老树看,意在证明,他不是敌人,是同志。而老树呢,他“啊”地一声抱着二元不动了。“我认同志为敌了。”二叔指着二元说:“你呀……你差点送了命啊。”二元哈哈一笑,“我呀试试他的党性。明知死,也得这样做。”
二叔说:“嘿,试哩,你拿脑袋去试法哩!你心里清楚,而他呢?“我试他在敌人面前……”他说着伸出一个大拇指,说:“我算服你啦,树弟。”老树说:“我在鼓里,你明白,你考验我,我……正说着,严成和金枝进来。二叔把刚才所发生的一场误会向他俩细说了遍。金枝笑了,严成异常高兴,说:“他是我党难得的人才。”说完拉着他的手只是嘿嘿地笑着。“永不叛党”是你的誓言。在回家的路上,二叔提议要老树用最省钱的办法,碹间属于他自己的新窑洞。有了家,才会安心地住下去。寻房住院不是久记。老树高兴起来,因为做为一家人说来,须有自己的房住。“二叔说得正是我心里想的。”说着,走着,他俩各自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