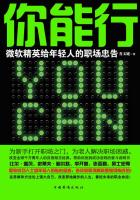“知道,你们这会儿有点时间,早点接管起来好,我也不搁挂在心上了。”她果断地说着,并忙伸出食指指着地下角落说:“搬掉风匣,去掉泥土,就看见木盖,便是地下室的入口。砖碹窑洞里,分别装着几小缸银洋,还有几瓮铜币。”她边说边从衣袋里摸了摸,哗得把钥匙扔给了小枝。
郝白、江国和几个村民,三下五除二把坚固的地下室打开了。大伙重复地过了数,正好两万块。小枝提议,大伙决定,让出一千块,给王氏留下养老。她高兴地收了下来。其余银洋,原地保存,只是新增加了三把坚固的锁子,分别把守不提。
一切安顿停当,江国打来温水,大伙洗手、擦完脸,小枝当场提议:两万块银洋留下扩大再生产,恢复、重新建设新的家园。
“嘿嘿,提得好,提得及时。”是严爷思忖了思忖,抓着烟锅使劲吸了几口,烟锅里吐出了浓烈的烟气,“树林村的穷人,要想彻底翻身,在分了土地的大好形势下,用这些钱,把河里白白流去的水引上山去。旱地变成水浇地,不就富了吗?”
“说得好,有理。”是老年代表郝永常赞成地说。“我同意。不能分光花尽,要发展生产嘛!”刘三元说。大伙你一言他一语,一致同意把有数的钱用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梁老师笑微微地看着大伙,说:“你们提出来的是长远的打算,很好,很好,你们提了宝贵的意见。但是,你们的意见虽很好,还得让全体村民加以讨论,因为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须得大家讨论通过,大家共同起来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计划就一定能够实现。”
末了,江国让郝三给王氏拿来了行李铺盖和一些另用物品。“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别归还了。”
说时迟,那时快,转眼到了一九四八年。阴历十五的月色分外明媚。今晚轮郝白、江国站岗放哨。小枝巡查夜哨过来,郝白踏着月光,喜冲冲地走来,说:“梁老师和严爷在一号洞里。其余在野外二号洞安全地休息了,请放心!”
“村民们呢?”小枝问。
“有的去了一号洞,有的在家里——人家说不害怕。”
“咱们把责任尽到就是。”小枝说:“但今儿站岗放哨责任重大,丝毫不敢粗心大意,发现敌情上庙打钟嘛。”
初春的夜是那么长,长得使人感到难熬而又讨厌;夜,又如此地静,静得使人感到有点害怕;夜,是那样的明,明得使人感到刺眼。小枝踏着月光月色转街过巷,观了星辰,听了鸡鸣犬吠,想着生虎兄弟心不死,竟然痴心妄想,参加了残余的匪军还乡团和复仇队反攻倒算,东山再起。“可恶可恶。”他想。
回想起父亲与李小狗长期的斗争,母亲与日寇的血战,兄弟俩幼年时所处的困境以及被生虎兄弟无端的污辱,欺负,嘲弄等等。他的心情顿时就难受起来,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吃人与被吃的斗争。他认为人生难,人生就是斗争再斗争,还有……建设家园也不就是斗争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梁老师说,将来还要与科学技术斗,没有斗争就没有人类,没有世界。
夜,已消逝。天蒙胧亮了,冷风儿凉冰冰,冻得使人发慌。小枝脸如针刺,浑身抖动。他向铁架山大路眺望了眺望,回了自家。只见奶奶和小叶没脱衣服,甜睡着。他坐在炕头上,刚打了盹,忽然庙钟响起来。他忙把奶奶藏在地窨,加了盖子,顶面堆了不少的山柴。正要拉小叶往出跑,忽地院里脚步声“咚咚,”生虎气势汹汹地喊:
“快点灯!活抓的留命!”瞬间,嘎嚓!嘎嚓!枪声大作。小枝惊慌而不乱,他毫不犹豫地从腰间抽了枚手榴弹,拉开导火线拴在小指上,说:“生虎,生虎别急,遵令去点灯呢!”说完,他用左手拉了小叶,低声说:“叶子,跑啊,随我跑,跑的越快越好……”
他把断了线的手榴弹往院里扔去,敌人怕死都唰地爬倒了。兄弟俩趁机冲了出去。待手榴弹爆炸时,江国领着民兵冲过来,小枝兄弟有救了。江国一手抓了小枝,另一手抓了小叶,高兴地庆贺了他一家安全无恙。小叶忙插嘴备细地说“……”
民兵们听了小叶与复仇队所进行的机智而又勇敢的殊死搏斗,庆贺他兄弟们又一次赢得了死里求生。因此,他们是那么高兴而又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说:“好。”他们用一个“好”字,代替了千言万语。可是那伙复仇队员见生虎被炸死,又听得生龙那边枪声大作,以为是民兵,就连忙溜跑,风声鹤唳,跑得无影无踪了。生龙领着另一股敌人向区公所的房间,放了排子枪。
“生虎!生龙!”王氏尖叫了几声,躺在血泊里去。乱枪之下,殃及了池鱼。生龙一听是母亲的声音,就惊奇地高叫:
“妈!你?”他正发着愣,小枝、江国带领民兵冲杀上来。霎时手榴弹声,喊杀声震天动地。仇人相见,份外眼红,生龙一甩手照准小枝打了一枪,小枝的帽子被打掉。但他毫不惧怕,持红樱枪一个踏步,从他的大腿捅了进去。他尖叫了声,摔下墙去,被众民兵三下五除二捆成个疙疸。
“活捉!活捉!活捉的不杀!”民兵们呼喊,手榴弹轰轰响,敌人死得死,逃得逃,逃跑不了的就举起手来要投降了。民兵们一个个地把敌人捆绑与看管起来。
一场复仇与反复仇的战斗结束了。打死敌人五人,活捉四人,缴获枪支十件,弹药多多。树林村激烈的阶级斗争,暂告结束。
小枝脸上糊满了鲜血,像个红脸关公。左耳朵被枪弹扯去半片。兰兰忙给打水洗了脸,洗了衣服上的血迹。她一边包扎着伤口,一边流着眼泪。小枝取镜子照了照,笑了,说:“看把你吓的,这防啥事?离心远着哩。”说着推开了她的手。
小枝上炕休息了,兰兰给轻轻地盖了毯子,郝白红着两眼要找小枝,兰兰说:“你长着眼不管用,你不知他挂花吗?”今天他不上班。找严爷去。”郝白点头示意而扭头走了。
小叶、兰兰回家去看奶奶,奶早站在堂门旁边,等待他们的回来。“奶!敌人进家吗?”小叶远远边走边叫。“生虎死了!生虎死了!”奶奶答非所问地说,她拄着棍子,迈着碎步,一走三摇三摆。小叶和嫂嫂把奶搀回家,让她款款睡在炕头边,小叶取了存放的专用药,说:“奶奶受惊了。嫂,煎药吧。越快越好,不可延迟。”
嫂嫂煎药,小叶站在奶奶面前,摸奶的脸颊,奶迷迷糊糊,不声不响。他又无声地扳抡着奶的手指,长长地流下两道眼泪。低声自语:“奶,别病,我……”他的眼泪如滚豆,把奶纷乱的头发梳理通顺,用毛巾擦去脸上的灰尘,拨拉着花白的发根,捉着头虱……
他对奶奶经常复发的病变是那么同情、关心、心痛,无微不至。奶的病就是他自己的病。家里人说,叶子对奶比对他自己还重视几倍。兰兰以为他是最孝顺不过的子弟。
“奶,”他给奶往高衬了衬枕头说,“我替您病……”奶奶出着粗气,没表情,没动作,无精打采地半闭着眼儿,像疲劳,又像沉思什么她笑了,微微笑着,两片嘴唇一张一张的。
她又哭了,无声地哭着,她只是瘪着嘴儿,连眼泪也没有,只轻轻地唏嘘,抽搭。然而突然她伸手推小叶说,要他离去自家,赶快躲去藏好,把手榴弹、地雷放好。“枝儿!枝儿!”她坐起来,扬着手势气忿地喊叫起来,她说:“坏小子生龙!你别杀人,生虎杀不得,你杀得吗?你是凶手,不是吗?”她两眼睁得那么大且圆,望着窗外说。只见她从锅台上取了把铁刀。小叶也被吓得跑出院去。她把那刀“堂”地扔在地上,使劲欠起屁股瞅着小叶说:“你要把那些刀呀斧的牢牢地藏去,对吗?”她还是重复地抬高嗓门胡说乱道:“叶子!叶子!你千万别把刀让生虎兄弟抢去。嗯……”
忽然江国进来忙说:“群众要求王氏的出灵要”排排场场举办葬礼仪式呢。“可以。”小枝不加考虑地说。村民们的意见要按古规旧俗去送王氏的终。满村人对王氏很同情,在她不幸与世长辞之际,是那么悲痛,他们有所不忍心,决定用她生前留下的钱做了崭新的寿衣和寿材。
出殡定为两天,雇了艺术高强的吹鼓手两班,笙吹呐奏,是那么红火热闹。灵堂设在她的旧居。宽敞的三进院铁炮三响,标志着出殡之始时。严爷是出殡的主持人。糕匠、厨师、端盘的应有的都有。所用的物品一应俱全。
灵前布满了花圈、纸扎、花色的筵供。小枝、严爷的花圈摆设在显眼的前面,亲朋的,江国的还有郝白的……
王氏生前的亲朋都前来送她的终。他们说王氏尽管是地主家的成员,但共认她确是个善良的女人。说王氏是他们敬佩与怀念的人。他们个个含着眼泪缅怀她追悼他。
三进院里挤满了送殡的,助忙的,看热闹的,是那样熙攘而又拥挤。出殡时,王氏一生老实善良,拥护共产党,保护我党组织的安全,不惜暗地用银钱救了党员干部的生命……党组织决定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小枝致了悼词。人们把拴铐子的生龙放出来,让他去送母亲的终。人们替他编了粗粗的麻辫让他戴在头上,拴在腰中,还穿了白色孝袍,也像个孝顺的儿子。
起灵时,戴着铐子的生龙给母亲拉了灵柩,也算没白养了他。他呢,不知是痛心还是装模作样,痛哭流涕地一边号啕,一边使劲弯腰去拉。看客们窃窃私语在纷纷议论说:“他妈没白养他——吃了一肚子弹。”“……”
王氏安葬完毕。生龙怎办?这是大伙关心而来处理的事。对生龙的问题争论不一。严成主张立即将他处死。小枝说李家只有他一个人了,如把他处死,李家就绝了后。严爷批评小枝,说他心慈手软,实属姑息养奸。他说:“我不同意小枝的意见。你既然知道生龙是敌人,就不能给他留情。嘿,凡是敌人就必须把他处死!”他把腰里拴着的烟袋取下来挥着,“对阶级敌人让步,就是对人民、对革命不负责任。人常说‘有礼必还’——我们寸步不让。”
小枝没做声。严爷指着他的耳朵说:“嘿,小枝呀小枝,你还年轻,你你你的半片耳朵呢?”他张嘴吭吭地咳嗽着,“嘿,共产党人不能凭感情运事,要铁面无情。”他嘿嘿着,动感情地去批评了小枝,说生龙兄弟肆无忌惮地去反攻倒算,去屠杀我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他兄弟太心毒手辣呀。”他出着粗气浑身颤抖着。
“是呀!严爷说得对,坚决处死他。”是刘江国扬着手说。“处死他!他是我们的死敌!”是刘三元举着两个拳头说。
正说着,梁老师“砰”地推门进来。小枝站起来,要让梁老师坐在独一无二的椅子上。而梁老师为他在写材料,伸手把他推上了座位去。
人们你一言,他一语给梁老师汇报了关于如何处理生龙问题的分歧。他要群众讨论,再作决定。
严爷今天的态度反常,过去凡梁老师说得的,不管大事、小事,他都无条件地照办。但他今天很反对他的意见,伸出烟锅“叭叭”地敲着办公桌。“嘿!生龙的问题不能让群众讨论,他明明是我们的死敌——明明向我们搞反攻倒算,反革命分子怎么去讨论?讨论啥哩?”
他说完提着旱烟袋气呼呼地走了。梁老师叫回了他,心平气和地讲了自己的观点。“严叔,我既不同意您的意见,也不同意小枝的意见。我们党的政策是,如果在战场中杀死他,是我们的目的,是必要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战斗结束了,那些俘虏不能随便杀去,只能依法处理。”
“嘿,那不行!”他火了,“若要留他的活命,就先把我处决死吧。”说完,他拉了江国把,要他和郝白将生龙押到大街路口用棒子去往死处他,他还叫来几个年轻人,梁老师没吭声。
百依百顺的江国和郝白,把生龙牵出大街路口绑在一棵粗树上。严爷取出不少的棍棒,见人给一根,要他们狠狠地打,使劲地捶,将他打死重重有奖。
郝白人年轻,虽有想法,但没办法——因为他胆小又是心软的人。从他懂事以来,曾没与人们吵过架,他一见打架斗殴的就躲得老远。此时他怎能打死人呢?他拿着棍只守着看而不去打。严爷喊他,他暗暗在笑。他笑打那个部呢?头上怕打死,四肢怕打折,把大棒落在屁股上,没有响声,只是拍去了些尘土。
江国与生龙是父辈结了怨仇的。他从内心里是恨他的,真想一棍了结他的命,才能解除他心中的恨。但是,他想的与亲手干的,又是两码事。只见他恨着眉头,喊声那么高,但放着脑袋不打,偏偏打其臀部、背部。“咚咚”的打击声,像击在自己的身上,使他提心吊胆,怕把他打死、打残。他没那个胆量。有人说他杀只鸡还提心吊胆地闭着眼,长时间没把鸡头割下来。鸡子飞去了,他也从此再不敢当屠手了。他呢,虽然过去打过他兄弟们,但毕竟只是几个耳光。而此时此刻装死复活的生龙,像似岸上的等刀猪,拼命地嚎啕着。
“救人!救人呀!”生龙在喊叫。
“杀人的人还让被杀者救呢?”在场的人们说。
严爷生气地喊江国、叫郝白,就连围观的村民们责备起来,骂他们一个个都是“松包”。只管让他杀人,而我们却不去还礼。“嘿嘿,李家的贼人是我们穷人接代传辈的敌人!”
他把郝白的大棒夺下,照生龙的头部打下去,结果,连个蝇子也没拍死。他生气地说他自己放屁都没声啦,哪里干得了这差事儿。他第二次举起那棒时只见一阵巨咳,就蹲下喘气了。
小枝跑出来为此事与严爷恳求。他涨着红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真的要留他的活命吗?”小枝没敢顶撞,只是看着他和言而低语与他解释,但他一气之下猛地昏倒于地。小枝、江国把严爷抬回养伤不提。
太阳从东海洗了个澡红得那么纯正。五一劳动节小枝和兰兰要在区公所举行结婚典礼。随着流逝的光阴,小枝、兰兰的爱情越来越饱满丰盈。刚刚进入新社会的俪影双双,从爱情步入结婚的神圣殿堂,是人生中弥足珍贵的时刻。
黄土高原传统的婚礼,原本是古朴,隆重,热烈,充满兴味,什么的花冠霞帔洞房花烛,一派喜庆。尽管如此,然而与新社会新婚新办,则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省钱而热闹。
兰兰母亲给闺女做了身鲜艳的红底紫花新上衣,红色花鞋,买了双喜字红袜、红头巾。小枝穿了身翠蓝色中山服,戴了八棱新式帽子。
梁老师是介绍人,他又是婚事典礼的总管。亲朋和区、村里的干部都来参加了。三进院的正庭里设了婚礼台,正面挂了毛主席相,两侧插了红旗,前面搁了只大方桌,再靠前摆了两排饭菜桌,桌上放着纸烟、糖果……
中午十二点大麻炮三响,村里的男女老少跑来看新婚的新郎、新娘来。黑鸦鸦地挤了一院。聂双双站在婚礼台上喊叫了:“新郎新娘就位!”
小枝、兰兰端端正正,分上下手站在婚礼台上。梁老师介绍完,他俩也分别介绍了恋爱的经过。耍笑开始了,小叶挥笔写了新诗一首,叫《花与蜂》,要哥与嫂嫂一递一句吟咏:
兰兰像是一枝花,
小枝若蜂去戏它。
春花喜迎蜂儿到,
而蜂采花花在笑。
兰兰臊红了脸儿。小枝咯咯笑出了声。江兰也赠姐姐与姐夫诗一首,叫《松与梅》:
小枝比做傲寒松,
兰兰是梅何畏冷?
冬梅去伴长青松,
双双笑傲严寒冬。
小枝捅了兰兰一拳,兰兰一看,是小妹的新作,就放心了许多。“我小妹不愧为高材生,诗的情意多美呢。”兰兰想。一刹那,那间区里一个年轻小伙子叫小黄,他风风火火地跑来,手里捧着张用大红纸书写的叫做《腌菜》的笑话,忙贴在婚礼台前。他笑声哈哈地要新郎和新娘一递一句地去对:
小枝的萝卜没处放,
兰兰带来了腌菜缸。
一条萝卜腌满缸,
两只蔓菁呀挂两旁。
菜缸发酵叽叽响,
沿着萝卜溢了汤。
小枝和兰兰一看便跑,但又被几个参加婚礼的小伙子追回来。不得已,他俩被迫把逗人发笑的趣句一一地对答起来。小枝红着脸笑,兰兰用两手捂着脸部笑,观众们也大笑。有的咯咯咯地笑出了声,有的笑弯了腰,也有的因笑得过度,流了激动的泪水。小枝被众弟兄们逼着说:“请你们别笑呀,俺响俺的,与你们有何妨?”
正在热闹地采拳喝酒时,忽然邮递员第一次送来报纸、文件。——县城解放了,地下党组织公开了。梁老师被调任中共县委任副书记,聂双双任区委书记,小枝任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