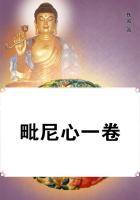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本故事,在一步一叹的黄昏漫谈中,它便是我神游的开场白。
每一个名字,都似曾相识。暮色中,还能分清生前或身后,需要极大的意志力。
残破的石碑,依稀的字,我和非我的界限,灵与肉的分野……一一混沌到逐渐失去颜色、逐渐苍茫、逐渐寒冷的黎明的胎中。
什么是升华呢?什么是熄灭呢?
有一次,我梦见跟朋友在一片断瓦残垣的墓地里走着。
荒草,异常的青绿。几株小叶菩提,乖乖地立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小径旁。一只白尾棕毛的野兔跳来跳去,我们因为追它,笑得不知死活。
完全不知死活,有时候,在我们最愚蠢最快乐最不清醒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人生的高度与深度,难道就正是这完全忘却了死活的那一瞬间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忽然想起了一段“空城计”来唱。
空城是一种计谋。死亡是一种计谋。
坟墓与空城,两种意象,在我醒后空虚的心里交缠不去。
又是黎明。孔明的胜利也许只因为他不知死活的愚昧吧?死亡是空呢,是实呢?我们又该如何计谋呢?
我躺在床上,努力告诉自己:这是黎明,不是傍晚;这是油盐柴米,不是风花雪月;这是不该聪明的时候,糊涂是福。
解构主义者的笔下,应当不这么感情用事的。但我的陷阱清清楚楚,不论是黄昏,不论是黎明,不论解构与否……
一只野生的兔子跳来跳去,我追过、笑过,不知天高,不知地厚……统统消失到一片空城里去。
跟阿亮喝茶
阿亮带着他新婚的妻来柏克莱,我请他吃饭,他请我喝茶,在我山坡上的家。
那天夜晚,窗外清明,难得海上没有浓雾,在落日中如同燃烧着的旧金山,正灯火灿然地悬在我的窗景中。没有云雾的山居,好像缺了那么一份情调。然而,阿亮的皮箱一打开,什么都关在门外了。
屋里,我们围着餐桌,看阿亮魔术一般演出一场“茶道”。
我本有一把东坡提梁壶,方正的壶身上刻着白色的梅花,宜兴陶土制的。
阿亮送我一把壶,圆胖的壶身上写着:“云深不知处 戊辰年 阿亮刻”。红土黑字。
曾在某本书上读到:意大利的大理石,带青色,是冷的;而希腊的大理石,带黄色,是暖的。我看宜兴壶,也是冷的;而阿亮的红土壶,越看越温暖。
云深不知处
采茶不知云深
喝茶不知身何处
好茶 好壶 好月当空
一生能得几回如此良宵
我心中这样呢喃。阿亮的茶经,却才说到:水质的甜滑与浓稠,水沸时的鼓浪腾波。
我想起一则禅门公案:
某日,赵州禅师问一位新来参学的和尚说:“你过去来过此地没有?”
那位和尚答说:“来过。”
赵州说:“既然来过的话,请进来喝杯茶好了。”
后来,来了另一位和尚。赵州又问:“你过去来过此地没有?”
那位和尚答说:“没有,这次是初来参学。”
赵州说:“既然没有来过,那么请进来喝杯茶吧!”
管理僧堂的院主问赵州:“你对来过和没来过的僧人,都请喝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赵州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答应说:“是。”
赵州说:“喔!是院主啊!那么,请进来喝杯茶好了。”
故事不及说起,已被阿亮的壶经打断。他说:
“一把好壶,流水要顺,盖子要密,手感要牢——除了造型要美之外……”
被阿亮摆了一夜乌龙,喝掉了极上品的茶叶无数,学到中式“茶道”的温良恭“简”让——“俭”不起来,讲究的东西向来涉及奢侈。
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有朋自远方来”的夜晚。
寻找雨树
日本当代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写过《头脑好的雨树》、《听雨树的女人们》及《倒立的雨树》。我在他混乱的夏威夷雨树与神话纠缠不清的森林里迷途了两次,终于决定:放弃。现代小说,好像与我无缘。
然而,他那又像暗喻又像是真实的一棵种在精神病院里的百年古树,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叫它雨树,是因为若遇到夜里下了骤雨,到次晨甚至晌午以后,它还一直从所有的叶子上把水滴落个不停,就像下雨似的;而别的树,早已干了呢。它那叶片长得手指头大小,但却繁繁密密,存了许许多多的水滴。它好聪明,是吧?”书中,一个酒会上的女人这么解释。
为什么存了许多水滴,到别的树都干了的时候,它却还下着雨似的,就是聪明呢?雨声是那精神病院里女人哭泣声的暗喻吗?雨的延长、树的聪明……它带给我的“想象的空间”太大了,以至于我出门一见了树就想及雨树。
真正的雨树,在哪里呢?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柏克莱的王子街上有三十几棵,美国人又叫它琥珀树(LiquidAmber)。我真高兴,地图上一比画,就开车寻树去。
你当然知道:结局只可能有两种——一是大喜过望,久仰了的雨树;一是非常伤心,它完全不像你要的样子。不幸,我落入的是后一种的心情。
一点也不王子的那条街上的雨树,并不是我所知道的琥珀树。因为琥珀树,我曾经深爱过。以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上班时,生物大楼那儿有一棵,每到秋天,树叶变成金黄金黄的,美得使我分心。我进办公室前,时常一步三回头,嫌自己除了多看它几眼,没法子再给那树多些爱意。
也许,雨树下雨后才有诗意;而琥珀树,要到秋天才能“迷眼流金”。它们的确“聪明”,因为它们并不为了人类所赋予的名号而生,也不靠人类错综复杂的爱憎而活。
自然,是一种“反占有”。约翰·柏格说得对。我想,雨树的魅力,只存在于被人羡慕的快乐中吧。
叶落
季节到了,叶子便辞枝而去,落了一地。有的枯过,有的缩过,有的病过;但是,也有的却像金箔一般美丽。不是所有的结束都面目全非。
一叶叶无声的安息,像一页页沾满秋天的颜彩写就的诗篇,随风翻过。不是所有的死亡我们都能读得懂。
如果叶子不落,它永远只在一棵树上。一旦随风躺下,它才能成为泥土、成为大气、成为无处不在的自由——真正被释放了。倘若我们可以选择,我想,也不是人人都愿意不落。
母亲的墓上,刚刚植下一排守墓的常青树。秋叶纷飞的季节,有的结束了,有的却才开始。请原谅我,母亲,我曾在您的墓前,将那原本轻柔安静的死亡哭成不堪……
也许,当我们的寂寞,由绿转黄,变成无边的寂静时,便是我们的季节到了。愿我们也能像叶子一样无怨无哀,悄悄落下。更愿我们有足够的智能,能清楚地预知季节的来临。
太阳底下摇滚乐
这是星期天。八月温煦的礼拜天。
坐在旧金山一个靠海的地方,我不期然地参与了一场露天的音乐会。
台上是摇滚的歌手,一声声嘶吼的爱,猛力敲打在众人的耳鼓上。除去了爱,这世界将是一片荒芜。快乐的爱、失望的爱,痛苦的爱、凄楚的爱,失而复得的爱、得而复失的爱,迷离的爱、恨与罪过的爱……摇滚乐的世界,除去了爱,也将是一片荒芜。然而,那无限的爱,在这有限的音乐里,显得多么的局促、多么的无能为力。怎么能够不怒吼般地嘶叫起来?怎么能够还慢悠悠提琴月光似的安详?交响乐属于无惊的岁月。摇滚乐则是属于那些跟在时代巨轮后头,一路吃着灰尘,一路又不甘心地咆哮着的一群。
台下纷纷的青年与少女,夹杂着心中依旧年少的白发与红颜,恨不得一把抓住一个爱。这爱,或许只是理念上的爱,可以与人无关。是的,我们爱我们的情人,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爱我们的国家,目之所及,力之所逮我都要去爱。然而,谁来爱我?神以外,我们有没有其他共通的爱呢?有的,就是现在,此地此刻,这音乐会,会场里的群众以及那传播着无信仰的爱的音乐。用我蒲柳似的腰身,作蛇般的扭曲,让宇宙缩小,让家园变成无形,让我在我那无着无落的爱里先找到我自己;忘形的音乐里,一个个孤独的游离的我。
这是另一种教堂。无神,并且露天。
每一个人都仿佛是挤在“愚人船”上的旅人,在心上狂喊着:爱我吧,不论我是否可爱;爱我吧,不论我爱不爱你;爱我吧,不论这世上是否真有爱的存在……
“这是我的绝望,你们大家拿去吃。这是我的希望,你们大家拿去喝。”基督,请原谅。我们并不缺乏献身的血肉,我们只是看管不了我们的灵魂。
平安的人在地上享受主爱。主爱的人却不一定得以享受平安。我羞惭地欢喜着,因为偷偷享受了一个平安的个人主义的音乐会。
扇子
记得报上曾刊登大鹏剧团演出《红娘》国剧,有张大千先生给女主角画扇题字之雅事,并附有女主角和她的团扇的新闻图片——当然,现在那面“团扇”比人面可值钱多了。
提起团扇,据记载,明以前唯妓女用折扇(可收可开之扇),良家妇女皆用团扇。
我有一本月历,用了六张扇面画作图,张张都不是画在团扇上的。虽然全是清以后的作品,可是我仍然不免想到:不知道历来所传下的团扇画会不会比折扇画少得多?仿佛文人是不大给良家妇女的扇子涂鸦的——后来把扇子当做画材,自是例外。
不过,无论如何,女人放弃了团扇与折扇之分界,是相当聪明的。
其实我对于扇子的特殊敏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拿“秋扇见捐”来譬喻遭遗弃,大概要收到箱子里去的扇子大抵总是团扇吧?折扇一折起来也就罢了,只有团扇真是摆来摆去都是一面扇子,冬天看起来哪有不碍眼的呢!
再想到,扇子本是多么Personal的东西,成了艺术品之后,竟变成大家的了。仔细想想,其间还不无哲思呢。
无字的书
通常,我们说看书,多半是说看那文字组成的书。可是,有些书真不是文字能写出来的,譬如美术专集、画册、摄影选粹之类,却少有人谈及。
最近我偶尔翻到一本黑白摄影集,书名是《论读》(OnReading),书里面是各种各类的人,在各种各类的地方,读着各种各类的书的各种各类的样子。所有的色彩只有两种:黑、白,却把一个“读”的世界,“读”到了不能意想的地步。这本书,真是比彩色的更其多彩,比许多有字的书更其多姿。
图书馆、校园、街上、树下,等人、候车的时候,这些平凡人循规蹈矩地“读”,在这里统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美丽,要叫人忍不住对“读”生羡。
欧洲人的读,日本女尼的读,教皇在圣堂里的读,平民在屋顶阳台上的读。
老太太老公公读信,帽檐低低地,信纸皱皱的,不知道读了几次,不知道落了泪没有?
贫民区的孩子,一边舔着冰淇淋,一边胡乱往撒满了报纸垃圾的门阶上一坐,随便就近在身旁乱七八糟的旧报纸堆中捡了张漫画来读,一读就出了神,冰淇淋都化了。
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瑟瑟缩缩坐在一堵破墙下,聚精会神共读着一本书,书摊在中间那个没鞋穿的孩子的膝头上,左膝下的裤管破了好大一个洞。——连一个字都没有,可是那天气的冷,那由书中取暖的动人,简直比一首诗有着更多更厚的韵味,还比一则小品更压缩更精巧,甚至仿佛是一篇无字的小小说。(文字到此竟成无用的东西。)
无字书通常易流于“收集好照片”的毛病。好照片只能带给人片断的美,倘使书无内容,一本摄影集就只能止于消遣娱乐的价值了,这是很可惜的。《论读》这本书,正好指出了一条比较可爱可行的出版道路。因为内容超越了形式,虽然全书并无一字一句,却也同样使人翻阅再三,爱不忍释,并且像读了许多,得到了许多的感觉。
一本不用文字全由图片组成的书,真像我们生活里的“沉默的片刻”。有时候,沉默更有胜于千言万语的魅力,这一类无字的书,岂不也是应当提倡并鼓励出版的吗?
熊
一山不容两虎,可是旧金山这附近,却是两虎并存:一个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个斯坦福大学。它们常使我想到从前的北大和燕京:一个平民,一个贵族。两校相隔不远,因为明争暗斗的缘故,心理的距离更近了。赛起球来,俨然死敌一般。
前几年加州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只大熊标本不见了,学生们一致认为是斯坦福偷去的,因为失熊的时候刚赛完足球,而且是加州大学得胜。这推论实在合情合理——加州大学向来输球,气量都磨炼大了,只有那少爷学校赢惯了,一次也输不起。
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原来“熊”是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代表。
“那么,斯坦福的校徽是什么呢?”
女儿告诉我:“是一棵柏树。”
熊和树,不同类,如何相比?熊会爬树,比较自由?不见得。树能入地上天,寿命可长着呢。既分不出高下,这两虎就这么相安着。
我是看惯了学校里的“金熊”才开始感觉到熊的“可爱”。不然,说实话,对那大块头笨重粗蛮的动物,称景仰还可以,绝轮不到说“爱”的。所有动物里,熊是少数独来独往的动物,它孤独惯了,所以不爱“人”,也不要“人”爱。甚至公熊母熊,也只在交配时互爱一下而已,它们是没有家庭观念的。好玩的是小熊往往是双生,一岁以前跟着母熊,一岁以后就“自立门户”,“爱”在它们的天性之中也许总没有机会萌芽就夭折了。可是玩具熊却被人抱来抱去地抚爱,不可思议。
从前曾一知半解地读过福克纳“很难看”的小说《熊》。其中猎熊的头几章,写的是一个往后把森林当成情人和妻子的小孩,他在旷野中对抗孤独与成长的历程。那原始旷野的代表就是一只被陷阱残废了一足的老熊。
福克纳写道:“如果……后院兔子和松鼠是他的幼儿园,那么这老熊跑过的旷野就是他的大学。老熊自己,这么长久以来不曾有过妻室儿女而变成自己的无性的祖先,便是他的母校……”
福克纳由熊身上所得到的灵感,或许给了设计柏克莱加州大学校旗的人启发,但不知与加州州旗上的熊有无关联?而加州州旗上的熊,跟马德里太阳广场上代表西班牙精神的铜熊,是否同出一源呢?
熊与树,树与斯坦福,斯坦福与柏克莱;而柏克莱却不是福克纳的母校,熊才是……我在书桌前,滚动着知识的雪球,遂想起在一切崩溃之前的白净底层:
“……在那个崩溃本身是射精膨胀怀孕和生产的沸腾动乱的地方,显得是无生命和陌生的,那时死亡还没有存在……”
读书读到无视死亡的存在,也许是大学的一种目的?走过半生,回首一望,原来灯火阑珊处,不是那人,是一只孤独的熊。
无言的剑
在艺术馆里,看到一具十五世纪的人像,真人大小,衣饰带缕丝毫不爽,神态宛然。这类作品本不少见,但我却为之驻足——因为它全身孔孔洞洞,好似十五世纪就有了“后现代”的手法——原来是木雕。
木头,比起陶瓷铜玉大理石,真不知“脆弱”多少,虫蛀、霉湿、火化等都可以“活埋”了它们。这一块神奇的木头,竟由十五世纪活到现在,并且还要站在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孩子面前,同样沉默地示范着时间的可怕与艺术的可敬。
人与艺术的克星就是时间,古董就是战胜了时间的艺术和艺术家的化身。那雕刻木头的手,早已腐朽,白蚁们在那木身上也开过了许多次的流水席,但那遥远的时代里,一位艺术家的意志与情趣,天涯咫尺,我却仿佛了解。
想到武侠小说中,时常有认剑不认人的荒诞事——谁接了师父的剑就可成为掌门人,武功人品似在其次——现在想来,其实也不算荒诞。因为人不能把时间的去向一一交代,一把剑却是可以的。
越古的剑,好像说得也越多。越古的剑,也好像越发地欲语还休呢。
看鹿
有一天下班回来,看见门口站着三头鹿,大喜过望。
时常在路上遇到“当心有鹿”的路标。刚搬来的时候,隔壁老华侨秦先生也说:“千万别种菜,会招引山上的鹿来,鹿吃菜不要紧,有时连花花草草也遭殃。”我便一心等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