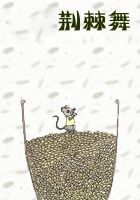舒穆禄着的,地老花脸沟,站在了半拉山崖下的水泡子边上。走了这大半天,他又累又乏,放下身上背着的桦皮篓,蹲在水泡子旁边捧水喝,正想站起来,眼红是上红的骨像羽毛似的叶子闪闪发亮。他喜出望外,忙背上背篓,攀着岩石往上爬。别看舒穆禄人髙马大的,爬起山来一点也不含糊,蹭、蹭、蹭,他手脚并用,不一会就爬上岩顶,前前后后也就是打个迷糊的功夫,他已经是喜滋滋地回到山崖下。看看阳光穿过树梢落在地上的影子,已经是正午时光,他赶忙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可是,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半拉山崖下,这可把他吓坏了!天啊!怎么不见来时的路?眼看阳光已西斜,舒穆禄的心里是越想越怕,再走不出去,就在这老林子里等着喂狼了!自己这条命交待了是小事,盼望着他回去的兽奴们舒穆禄“扑”地跪在了山崖下,虔诚地求告着:“乐库里妈妈(指路女神),我麻大山了,您显显身给我指条路,把我领出林子吧,可就要灾难临头了!
我求求您了!”
就在他不断求告的时候,林子深处传来一阵“嚓拉嚓拉”的脚步声舒穆禄愣住了,莫非是乐库里妈妈真的显灵了?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侧耳听听,是真的,而且,正朝他这边靠近。一阵神秘而又恐惧的感觉降临,他赶快擦干脸上的汗,偷偷地伸了伸腰,跪得更加直溜,生怕一有响动,乐库里妈妈就会不高兴地甩手走开。
声音越来越近,人影也越来越真亮,舒穆禄惊奇地看到,往他这走来的是一个背着个桦皮篓的格格!
舒穆禄高兴得一跃而起,直冲冲地奔到那格格面前,掸袖跪地就给格格打了个全跪千,嘴里叫着:“舒穆禄给乐库里妈妈请安。”站在舒穆禄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秋祭之夜从人群里消失的。
在林的来是个,又喜,惊奇的是他竟把她当成乐库里妈妈,惊喜的是自己单身进山竟巧遇这么个浓眉锐目、浑身英气,却居然还对她又跪又拜的阿哥!舒穆禄大声地求告着:“乐库里妈妈,我叫舒穆禄,是东海窝集部的兽奴,上这来,是为了给我大伯的腿来采药的。现在,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如果我回不去,窝集部的兽奴们就要遭殃,乐库里妈妈您帮帮我,帮我找到回去的路。下一世,我指定投胎做牛做马报答你!”
听舒穆禄一连串地说了这么多话,芍丹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林子里已看不见阳光,天不早了,再耽误下去,就要出人命的!她麻溜地一把扶起舒穆禄,转身就朝林子外走去。
舒穆禄紧跟着芍丹,走过茂密的森林,走过林间的溪,走出林子,跨上红鬃马,奔驶在来的路上。
红鬃马腾起四蹄飞奔,一片片林子被甩在身后,骑在马上的舒穆禄暗自庆幸终于能够按时回到东海窝集斗兽场了。
在那里,一轮冰清玉洁的圆月在宁静的夜空缓缓移动,温柔的月光照着那排沽满鳞状血迹的木栅栏,晚风吹拂下的斗兽场宁静得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是,舒穆禄并不知道,这一美好景象只是他眼前的一片云,是飘过他面前的一阵雾。
此时此刻,一场狂烈的暴风已经在东海窝集斗兽场刮起,等待着众兽奴和他的将是一场惨烈的命运!
女罕的马队风驰电掣地冲进斗兽场,女罕飞身下马。德都勒急忙从后面赶上来,诚惶诚恐地跟在女罕的身后走进撮罗子。
曹尔佳急匆匆走进,掸袖跪地:“给女罕请安!”
“德都勒,带人把富察给我绑来!”落座在大木墩上的女罕声音。
“口庶!”德都勒答应欲去。
“报女罕,富察的腿摔断了……不,不能走。”曹尔佳挺害怕,战女后,着眼都一眼。
是咋回事,前几天问德都勒,不是还说好好的吗?
女罕面色一沉,从座椅上站起来,走到德都勒的面前,冷冷地盯着他,声音一下提髙了许多;“你前两天是怎么说的?”
这,这都女的眼,着曹尔佳,“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什么时候摔的,早上不还是好好的“今天早上,您带着猎户走了以后,我让他们整理场子里的木栅栏啥的,不知道怎回事,他就摔得躺在地上起不来了。”曹尔佳小心翼翼地回答着。
“你他妈的真是烂泥捏不成团!就让你管一天的事,你……”德都勒火冒三丈他朝曹尔佳呸了一口,“这个熊样干什么吃的!”
“好了!别说了!断腿?只要有口气就给我把他整过来!”女罕的眼里射出令人生畏的寒光厉声命令着。
“唬!”德都勒答应着转过头他狠狠地盯了曹尔佳一眼,“还愣着干什么,带上人跟我麻溜地走啊!”
“慢着……”女罕的话停顿了一下,拿起那块卜骨用的兽骨在手里把玩着,“给我把所有的兽奴都带过来,我要让他也尝尝心里难受的滋味!”
德都勒带着阿哈们直奔兽奴住的大撮罗子而去。
老兽奴端着一碗酒走到土坑前,递给躺在土坑上的富察,“喝两口吧,活活血也解解痛。”
“玛法,”一个年轻的兽奴走到老兽奴面前问,“眼看天就黑了,舒穆禄还没回来,万一要是德都勒回来怎么办?”
“他带着猎户进山了,怎么着也得明天太阳二杆子的时候到这没事。再说了,怎么办?虎出山林鱼到河汊到哪山就唱哪山的歌唢人是我让去的我担着。你们……”
“砰”地一声重响,老兽奴的话还没有说完,虚掩着的桦树门被踢开德都勒带着一帮阿哈冲进木屋。
兽奴们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富察的木榻前。
看到这架势德都勒气得心火直窜他腾腾地走上前一把把富察从炕上拎起来恶狠恨地骂:“早不摔晚不摔,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这一手,你是咋回事?你他妈的存心给我找难看咋的队在炕上下蛋啊!?”
“头领,富察是摔了一跤把腿摔折了。”老兽奴说。
德都勒扔下富察朝老兽奴踢了一脚:“你他妈的逞什么能耐,谁让你回话来着?来人,把他给我整出去!”
几个兽奴上来欲抬起富察。
德都勒骂骂咧咧地上前扒拉开兽奴,吼叫着:“滚开!什么王八犊子,还用人抬?舒穆禄,来,把他给我整出去!”
兽奴们面面相觑,躲避着德都勒咄咄逼人的眼神。
“舒穆禄呢?啊!说,舒穆禄上哪去了?”德都勒火冒三丈。“头领,今天早上,富察的腿摔坏了,我让他……”老兽奴站出来,恭敬地说着。
“不,”富察打断老兽奴的话,拖着一条伤腿滚下了地,因为痛,他一脸苦色,手支撑着半跪在地,“是我,是我让他上山给我采药去了。”“什么!你让他上山?这跟出逃有什么两样?自从我当上东海窝集部的兽奴头领,就没出现过兽奴私自上山的事!”德都勒气得眼睛发直,眉毛支楞成两把刀,现在这一出事,我这兽奴头领的位置还传给谁?自己的命能保得住就是天大的运气了!他跺脚甩手,喋喋不休地骂着,“你他妈的还腆脸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呸!敢让他上山?你找死!没报请我就私自上山,他犯死罪,你也活不了!”
“德都勒头领!是我让他去的。”老兽奴跪在富察身边,抢着说,“人是我让去的,要杀就杀我一个人吧。”
“杀你?杀你当个屁用!你让我怎么向瑷珲女罕交代?啊!”德都勒一脚踢倒老兽奴,气冲冲地叫喊着,“来人啊!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富察给我拴在马后,拖死他!其他的人都给我押到斗兽场去!”天黑下来了……
月亮从长白林海跃然而升,今夜的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亮。肃慎人说太阳和月亮是一对亲姐妹,太阳是姐姐,她的名字叫“逊格格”;月亮是妹妹,叫“毕娅格格”。为了给人间照亮,姐妹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浩瀚的天宫当值,总也不能见上一面。当姐姐想妹妹忍不住而痛哭时,人们就会看到太阳的边上有一圈环儿般的泪痕(日环食);当妹妹想姐姐忍不住而痛哭时,人们就会看到月亮的边上有一片乌云般黑色的眼泪(月偏食)。每当这时,人们就会打起神鼓唱起乌春(满族民歌),表达人类对这对姐妹的感谢:
太阳把金光撒下来,月亮把银光撒下来,金光银光孚育万物,肃慎人代代舟格格。
今天晚上也许是姐妹俩开天旷古的第一次团圆。
日月相融一轮圆月火红她轻轻地、轻轻地在长白夜空缓缓移动。
月光从高天倾泻,撒在苍郁葱茏的林海从俏丽多姿的美人松身上滑下,在斗兽场边灌木林里投下朦胧的阴影。
林风哼着夜歌鸟儿轻啼蝉儿轻鸣,远处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虽然苍老却透露着森林婚礼证婚人发出的那份得意。有一阵阵淅沥沙拉的声音,那一定是虫儿送嫁的队伍,骑着快马唱着乌春走的地多么浪漫缠绵的情爱之夜多么温柔娴静的长白月夜!
一阵纷乱的马蹄声打破夜的宁静。
一路燃烧的火把划破老林子的黑暗。
一队人飞马而至。
斗兽场内顿时一阵忙乱。
五团火苗从东南西北中窜起,八个柴堆在木栅栏前燃烧。
“打!给我狠狠地打!”德都勒指挥着阿哈们,“往死里打!送他们下地狱!”
一队阿哈手持牛皮鞭,走马灯似地轮番抽打着被绑在木栅栏上的兽奴。
火苗呼呼,浓烟翻卷火堆里劈啪的响声夜风翻飞的呜声兽奴们被鞭打、被火燎烤的凄痛喊声在夜空中交织而响,斗兽场上一片惨景。
有人宣号“女罕到!”
一群卫士护卫着女罕出现在斗兽场。
女罕身着一袭黑貂长袍,满头的黑发上没有一点装饰。她铁青着脸,双眼冷峻,紧闭的嘴角溢出一股傲然之气。
“女罕吉祥!”德都勒和众阿哈半跪在地。
“起来吧!”女罕双眉一挑,冷冷地扔下一句话。
熊熊燃烧的火光驱散黑暗,女罕在卫士的簇拥下走向木栅栏。夜风吹散浅灰色的夜云,一轮皓月当空,银光满地,北国荒野上的秋草连绵起伏,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
女罕走到着的和兽。
一股股着火的火,着上,着在上的兽奴们,有人在低声地呻吟,有人在痛苦地叫喊,有人已经昏厥。
被绑在木栅栏上的富察破衣烂衫,鹿皮衫的破碎处伤痕累累。他低垂着头,披散的头发在夜风中翻飞。
跟在女王身后的德都勒拿起一根火堆里燃烧的木头,将烧得通红的一端猛地一下按在富察的脸上。
“吱”地一股青烟冒起,发出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啊!’昏迷的富察被烫醒,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
老兽奴已经奄奄一息,他古铜色的脸膛被火烤得又黑又亮。他努力地抬起了头,看到德都勒肥大的手掌在火光的闪烁里一摇一晃,就像熊掌,他怒瞪着两眼,恨不得一猎刀过去,割它个掌断血流。他愤怒地叫骂着)“德都勒,猎人不打蹲天仓的熊,怀崽的野牲口,
“哈!哈哈……”女罕发出一串冷笑,“好,说得好!你是男人,我倒要听听是谁吃了豹子胆,是谁敢让舒穆禄去上山,又是谁居然敢让舒穆禄骑我的马!”
你他妈的折腾绑着的人,还算是个男人?”
“尊贵的女罕,是我,一切都是我做的。是我让舒穆禄去上山的。”老兽奴目视女罕带着死又何妨的神情坚定地说。
“不,不……是他,是我……女罕……是我……让舒穆禄去……上山去的!”苏醒过来的富察竭力把话说得清楚。
“好啊!不管是你,还是你,你们不知道兽奴是不准私自离开斗兽场的吗?啊!”女罕勃然变色,“既然你们嘴都挺硬,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嘴硬的下场!富思库!”
卫队头领掸箭袖半跪在地:“富思库在,听候女罕命令!”
“给我处死所有兽奴!”瑷珲女罕杀气腾腾。
“嗾!”富思库朗声答应。
“来人!”富思库一声令下,列队在女罕身后的卫士们奔跑过来,杀气腾腾地站在被绑着的兽奴身边,手中的青石刀寒光闪闪。
“女罕,你不能这样做,处死无罪的人,要招神灵……”老兽奴地着。
一道寒光落在老兽奴的脖子上,“噌”地一声,喊声戛然而止。
女罕收回宝石刀,冷然地说:“我倒是要看看,谁还敢叫唤!”
“女罕,这一切都是我富察造成的,与他们无关,要杀就杀我一个人吧!如果您不解恨,就把我千刀万剐还不行吗?”眼看着老兽奴杀,看着兽奴就,富,他不地声地着。
“哼!富察,就你一个兽奴的命,千刀万剐就能抵破了我东海窝集祖宗规矩的罪孽?”女罕不屑一顾,“你算个什么东西!”
德都勒带着人往大火堆上加木柴,夜风吹过,火焰熊熊燃烧,火苗飞舞,映得女罕脸上一阵红一阵黑一阵白,阴阴阳阳,十分浄狞。
“女罕……您先杀了我吧,让我死在他们面前,我对不起他们啊……”富察号啕着哭喊。
“富察,你还知道对不起?”女罕走到富察面前,指着众兽奴说,“你看着,你睁开眼睛,明明白白地看着,他们都是为你而死的!”
女罕怒然下令卫士们,开刀!”
卫士们一拥而上,把兽奴们从木栅栏上解下,摁倒跪在地上,“嘿!嘿”地一阵嚣叫,手里的青石刀“嗖、嗖”地从空中劈下,“咔嚓、咔嚓”令人恐怖的的刀劈声,绝命的惨叫声四起!
“砰、砰”地一颗颗人头落地轰响,腔子里的血喷涌而出,飞溅在草地。浓烈的血腥味立刻在斗兽场上空弥漫。
“女罕……你杀了我,杀了我吧!让我和弟兄们死在一起!”富绝地。
“想死?那还不容易!富察,人来到世上,就两种选择,要么活着,要么死去。死,是世间最容易的事情,死可以忘记所有的痛苦,可以抛弃所有的烦恼,可以不要所有的爱,可以永远没有内疚,可以把所有的悲痛和遗憾都留给活着的人!我不会马上就让你死的,我要让你带着所有为你而死的人留下的恩恩怨怨慢慢地去死——去死!”瑷珲女罕恶狠狠地指着满地的尸首,“你看,他们是我下令杀的吗?不是,不是!他们是为你死的!”
夜风呜咽,火焰旋升,映着女罕的身影。
夜风吹动着女罕的貂皮袍,在火光里翻飞。
一匹快马奔驰而出,引来野狼拉长声音的尖利号叫。
舒穆禄手持松明子火把在荒野上纵马疾驰。
马蹄得得飞过森林,飞过山坡,终于来到了小河边,斗兽场就要!
忽然,奔跑着的红鬃马止住前蹄,一甩脖子嘶鸣起来,那畜牲惊恐不安地髙抬起前腿,后退了几步后尥着蹄子不肯再往前行。
一心赶路的舒穆禄被掀翻在地,他一骨碌爬起来,摸摸身后的桦皮篓,好好的,他心定了许多,赶快一闪身奔到马旁边,一边撸着马脖子上的鬃毛,一边警惕地打量四周,奇怪了,没有什么动静啊!他刚想翻身上马,一阵风刮过,阵阵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再抬头看斗兽场的上空火烟飞舞!
不好!舒穆禄撒腿就往斗兽场方向跑去。
舒穆禄跑到了斗兽场边上天啊!舒穆禄惊愕地看到:
地上横七竖八地满是尸体烧焦的腥臭味扑鼻而来!
所有的尸体都没有了头,被砍下的头颅有的滚落在火堆前依稀能看见圆睁的眼睛和大张着的嘴,有的滚落在火堆里,已经烧得只剩白骨有的还在冒出火苗!
都怪我都怪我回来得晚了!
要是我不迷路要是我再快一点回来……他们,他们就不会死了!
舒穆禄高举的手重重地砸在地上无声地哭了!老玛法死了,大伯死了,众兽奴都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狠毒的女罕、头领我跟你们了舒穆禄出的斗兽里去“富思库让卫士们退下。”瑷珲女罕简短阴沉地命令着。
“嗾!”富思库指挥着卫士们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