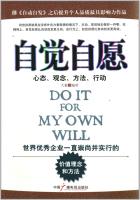身边好像有马蹄声,哥哥,是你来了吗?
我手臂都酸了,再也抱不住马儿,马蹄一个飞跃,我从马背上甩飞了下来,失重的一瞬间,脑子异常清醒。
我要死了吗?以前想过多种死法,从来都没想过从马背上摔死啊!我是那么害怕骑马。
要是头先着地,那我死的岂不是很难看!
出乎意料的,落入一个宽厚的环抱,一阵天旋地转,那人抱着我从草坡上往下滚了下来,一圈圈的滚动,让我头晕眼花。
我吓的紧紧抱着眼前的人,失声大哭道:“哥哥,哥哥!我差点就死了……”
他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阿欢,不用害怕。”
我瞬间止住了哭声,从他怀里抬头,原来是于单救了我。他咧嘴对我笑,脸上有些发白,头发乱蓬蓬,很明显他也被吓到了。
我惊魂未定,眼泪止不住往下落,我还活着。这时云珠儿和华英也已经策马赶至,两人脸色都是非常担忧,看到我和于单都没事,大呼了一口气。
我们费力从草地上站起来。
华英从马上翻下,急急跑到我身边,连忙拉着我的手上下看,愧疚道:“阿欢,你有没有事?都是我不好,差点害了你。”
我勉强一笑,脸色却还是惨白:“别担心,我没事的。”
于单怒瞪她道:“华英,你也太不知轻重了,阿欢她本就不会骑马,要是出事了怎么办!你总是这样莽莽撞撞,迟早出事!”
华英脸上一红,面上有些挂不住,怒道:“我、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他两眼看这就要吵起来,我拉着华英安慰道:“华英……”
她猛地甩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看着我们两个人,气呼呼哼了一声扭头就跑了。云珠儿站在一边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好像明白了什么。随后她跟着华英,策马离去。
于单护着我从草坡山滚下,发髻散乱,身上的衣服也被荆棘石块划开,两人甚为狼狈。我窝在他怀里,马儿慢悠悠往回走,回想起刚才一幕,心里十分后怕,只要他再慢一点,我很有可能摔断腿脚,甚至是死亡。
“阿欢,你刚才为什么喊我哥哥?”于单的声音从脑后传来,我陡然回神。
远处草原山坡,西边斜阳日暮,不规则的流云时而变换形状,山坡青草被夕阳染黄。放羊人悠长的呼斥声,像歌谣一样悠悠传入耳畔。我喃喃道:“莫道老牛归去饱,牧人炉下正生香。草原,真美啊!”
答非所问,他亦没再问,只是和我这般,看着天外夕阳,渐渐变幻的草场和流云。看着牧羊放牛的人,挥斥着长杆,赶着成群的牛羊归栏。看着时光渐渐流逝,看着美好一寸一寸落下,又升起不同的夜晚景象。
“你若是喜欢这里,不如永远留在草原,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他在我耳边留下这样一句话。
这里做我的家……
有成群的牛羊,广阔的草场,美味的食物,甘冽的酒水,火热的歌舞,豪放的民风,远处的夕阳。这一切,我都能拥有吗?
回到营地时,阿伊丽被我们的样子着实下了一大跳。听完我们讲的之后,更是脸色煞白,拉着我差点没哭出来。
第二日,我睡到中午都难以起身,头昏脑涨,我方晓得自己是病了。
我从来很少生病,就算病了也都是自己尽力扛一扛,可这次病的来势汹汹,我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喝了一大碗姜汤之后,没有丝毫用处。
于单听闻后便来看我,叮嘱了几声便走了。
我在榻上紧紧裹着自己,云珠儿来看过我,对我暧昧一笑:“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伊稚斜,原来,你喜欢的人是太子?”
她眼睛里带着询问和不确定。
我笑了笑,脸上因为感冒生出大片红晕,她大概以为我是害羞,所以脸红。
我没有反驳她,就算是默认她的说法。不管她怎么理解都好,只要不再误会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而后的几天,阿伊丽试了草原民族的各种治感冒的偏方,我仍旧毫无起色,病反而愈发重了起来。
草原上的人,都是身体壮阔,他们常年迁徙游牧,在马背山生活,体质相对汉人较好。
他们若是生病了,大概打场架,发发汗也就好了。因此他们在医理中药材方面的文化知识,远远没有汉文化来得丰富。医药之累书籍,他们也更是没有。他们的生活更多放在如何在恶劣的草原沙漠之中存活。
勉强支撑了四天,到第五日时,我已经倒在床上说胡话了。阿伊丽眼泪汪汪的拉着我的手,营帐中吵吵闹闹。我模模糊糊睁眼,看见许多人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头上身上都装饰着各色羽毛,脸上带着狰狞的面具。围着火盆中间不断的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铃铛法器伴着呼唤,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这里难道就是罗刹鬼狱,幽冥之地?
我这一生,活的这样短,也从未做过坏事,为什么我要下地狱?眼睛肿胀无力,再也睁不开。耳边的声音渐渐模糊,只听到有人在我身边喊:阿欢,不要死,活过来。
陷入无边无际的混沌梦中,那些疲惫苟活的生命一个个若走马观花一一闪过。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一个白衣男子的身影,面若秋月,眉似远山,眸似秋水寒星,嘴角微扬,好听的声音像泉水叮叮咚咚。
我醒来时,看到头顶的花纹天顶,原来我还活着。费力地坐起来,发现自己头痛好了许多,身上除了疲累之外,好像没什么大毛病。
阿伊丽掀开帷幔,见我醒来,又惊又喜,眼泪汪汪的放下药碗抱住我,带着哭腔说道:“阿欢,你终于醒过来了。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还以为你……”她埋在我脖子里哭了起来。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声音沙哑地安慰道:“好了,好了,我没事了……”
她从我怀里钻出来,眼睛红的跟个兔子一样,明显哭了好几次呢。
我伸出双手给她抹眼泪,笑道:“只是生个病,你怎么就哭成这样?”
她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红眼嗔怪道:“你差点死了你知不知道!你昏睡了整整三天,太子请了许多萨满巫医来给你看病,结果一点用都没有,气的太子殿下将他们一个个轰了出去,我们都以为你不行了……”
她声音一点点变低,眼看着又要哭了,我连忙问道:“然后呢?”
她松了口气:“还好左谷蠡王及时赶回来,带回来一个穿着白衣的中原人,他拿着小针在你身上扎了几针,又留下一些草药。他说你今天一定会醒过来,我原本还不相信,现在看来那人还有些本事。”
原来我模模糊糊看到的不是做梦。伊稚斜又一次救了我,若不是他,我这次很可能去见阎王了。
阿伊丽转着咕噜咕噜的大眼睛看着我,疑惑问道:“阿欢,在你们汉地,给人治病,都要用针扎人吗?看起来怎么这么奇怪?”
我哧笑了一声,揉着她的脑袋道:“傻丫头,那不是扎人,那是中原治病的一种方法,用针灸刺激人体的穴位,打通经脉,十分精妙。”
阿伊丽歪头想了想:“那不还是扎人吗?”
我低低一笑,北方游牧民族大概无法体会中原的医术有多么玄妙,也无法理解我对‘扎人’和‘针灸’不同的理解其实是从心底的尊崇。他们有时攻城略地无比勇猛,在知识文化方面真是与汉地不可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