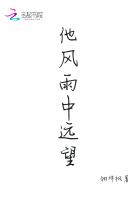我紧张地瞅了瞅那个可能飘来监视我的目光的角落,又望向大厅内来来往往的军官文官和小姐们。
莫斯文克皱了皱眉头,满怀疑惑地问我:“怎么,有问题吗?”
“你好像一直在四处张望,”莫斯文克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在找克里姆林宫里的熟人吗?
我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在莫斯文克的小腹上轻来一拳,讽刺道:“报告指挥官!我只是突然发现,大厅里别人的反应很奇怪而已。”
“哦?是吗?”莫斯文克懵懂地问了一句,“有什么奇怪的?”
对此我拒绝解释。如果不是我对莫斯文克有所了解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这个打仗的时候生龙活虎的家伙,到了社交场合里,是故意装出对环境“一无所知”的样子。
我们迈进了舞池。莫斯文克照着之前斯拉维克的样子,一只手放在我的臀上。我紧抓他另一只手。
“这个姿势……好古怪,”莫斯文克皱了皱眉头,“就像是……在蒙古人节日里的摔跤比赛一样。”
我再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回答:“放心,指挥官同志。我又不会把你给吃掉。只是我有点好奇,难道您以前从不参加舞会的吗?”
莫斯文克半天都没有吱声。很好,我想,我大概是猜到理由了。
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们部门里倒是经常性举办舞会。问题在于,既然有我这种目光焦点,自然也有那些几乎不参加的人。也许正因如此,舞会才经常在体育馆里举办。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室内的边缘角落里的篮球场地,让一部分人不显得无所事事。
我可以确定,在此之前,莫斯文克绝对是边缘篮球场里的常客。
就这样,我带着这个笨手笨脚的学徒,跳了很长时间。为了解决对方一直紧张得冒汗的问题,我只能建议莫斯文克,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琐细的事情上,比如长方桌子啦,盛放红酒的高脚杯啦——
总之——嗯,其实我也挺紧张的——只要不去想洛马诺夫昨天的叮嘱,我的手心不停出汗,还一直被莫斯文克踩到脚等烦心事就好。
“话说,你先前在说什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疑惑地看着莫斯文克,然后又被踩了一脚。
“你好像认识埃格尔元帅?”莫斯文克冲着洛马诺夫的方向努努嘴。刚才埃格尔元帅和其他几个外国人一直围着洛马诺夫,刚刚才做鸟兽散,只剩下后者满面红光地抱着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女跳舞。
埃格尔……听到这个名字我轻轻地把嘴一撅,没好气地回答道:“当然。我们家一直都认识他。”
就算看我的表情,莫斯文克也应该,我在和埃格尔元帅,乃至家庭的关系都比较僵硬也不愿再提,但莫斯文克似乎不太懂察言观色。
“切。我还以为,你和埃格尔元帅是老熟人,老朋友了,”莫斯文克吐了一口气,疑惑地问,“你应该……不是平民家庭出身吧?”
换做其他人,如果敢跟我提起这段历史,我一定拂袖而去。可我不能,我只能继续诅咒洛马诺夫。
我幽幽地回答道:“知不知道斐迪南一世?他是我的曾祖父。”
我感觉到,自己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是在谈论刀山火海,最底层的地狱似的。好吧,本就如此。
莫斯文克似乎并不诧异。他只是略一吃惊,目光有些古怪地问:“你是保加利亚皇族吗?真奇怪,那你是怎么进入克里姆林宫的?”
我奇怪地看了莫斯文克一眼,突然想起,这是很正常的问题。一如盟军国家的领导人,很少有平民家庭出身的一样,在联军国家里,家族履历上的“前剥削阶级”这个词,就是升迁之途最大的阻碍。
我尽可能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按理说,我这个样子应该挺妩媚的。可是莫斯文克的反应,却像是在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尽可能不要笑):“的确如此。但在保加利亚,有一支家族是个例外。”
“例外?”莫斯文克明显没听懂。他挠挠脑袋,“什么例外?”
这家伙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然而我眼珠一转,假装出一副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的表情。
“得了吧……”我假装无意地踩了莫斯文克一脚。抬起头,与笑逐颜开的洛马诺夫四目相对,后者丢给我一个“干得漂亮”的眼神,我对此报以白眼,若无其事地将下巴搭在莫斯文克的右肩上,右手从下往上扶住,“再革命之后,没被清洗的保加利亚贵族,只有一家。”
“那好吧,”说是明白了,但莫斯文克的脸上,依然写着“一头雾水”这个词组。但他勇敢地选择了打肿脸充胖子,假装出并不孤陋寡闻的样子问我,“可是……你好像,很讨厌埃格尔元帅的样子?你们家族和埃格尔元帅有过节吗?”
“比那个严重多了,真的。论矛盾,大多数人想都想不到……”
突然间,莫斯文克没由来地浑身一颤,把我搂在了怀里,在我耳边轻声说:“有人在监视我们。”
“你说什么?”我诧异不已。第一个念头,就是洛马诺夫安排监视我的特工,可能已经被察觉了。
当我转了一个圈,转到莫斯文克的视角方向,顺着莫斯文克的目光,朝大厅远处的楼梯口望去的时候,一副场面应证了我的猜测。
紧挨着楼梯口的那扇门早就被人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的呢绒的身影,像是从舞厅里凭空出现,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口一样。注意到我可能在看着他那个位置,他略略偏过一点点脑袋,冲着我们的方向。冷冷地点了点头,推门而出。
我总觉得,他应该是隐形人。不然的话,怎么会没人注意到他?
而且……当他看向我的时候,我感觉到,在他那双清澈的蓝色的眼睛里,一直闪烁着紫色的光芒。
刚才那一瞬间,我可以确定,我以前绝对见过他,只是我想不起来了而已。他应该不是洛马诺夫的探子,只是对我们有点好奇,于是暗中观察,看我们会做出什么事。
看来……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
回到久违的公寓,我突然感觉到,从美国回来之后,最想念的,还是这个我曾十分讨厌的小房间。
洗漱完毕,睡觉时间到了。之前在宴会上,埃格尔元帅可是告诉过我们,很快我们还要投入新战场的。我最好抓紧一切和平的时间。
电视上还在宣扬着联军一次次的胜利。华盛顿解放后,美国本就脆弱的本土防线,现在更是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大批本来要南下的加拿大人被堵在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就连杜根本人都已经不知所踪;而留在南方,准备抵抗联军钢铁洪流的美国人,现在不得不放弃大片卡维利曾断言“绝不放弃”的国土,收缩战线。目前为止,情况不错。
如果说……维拉迪摩大元帅对纽约的突袭,没有因为损失了四艘无畏战舰而打成持久战,配上自由女神像的废墟,纽约就更完美了。
关掉了电视机,我推开床上乱丢的内衣和其他衣服,一屁股躺了上去。刚放松下来,舒服地躺在床进被窝里的时候,我就犯迷糊了。
可是没过多久,刺耳的电话铃“叮铃铃——”地催促了起来。我不耐烦地伸手,接起电话的时候,里面传来了马卡洛夫慌张的声音。
“政委同志,麻烦你赶快来一趟军营,我们这里……出事了!”
“什么事这么急啊……又不是盟军鬼子又打到莫斯科了……”
“不是!指挥官同志他……和维拉迪摩同志已经大吵大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