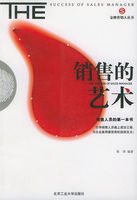在日升日落中数着日子,长赢已经吃完了身上携带的极少的干粮,但比起肚饿的难受,巨大的困意才是最大的难关。
当夜交手时,单花间提到流火三人。长赢也很担心他们的状况,那单花间说他们已经死了,长赢是肯定不信的。虽然单花间武功路数刁钻狠辣,但李靖流火逐日三人也绝非吃素的。只是不知道现在他们有没有回客栈,未看到自己和公子笙他们又会怎么做,回天机阁?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由于洞内寒气逼人,几天来倒是没有什么凶禽靠近。长赢只是担心单花间,不知道她疗伤需要多久,伤好之后会不会再寻他们。若是公子笙迟迟没有转醒,届时也只能靠自己全力应付了。
长赢站在洞口看夕阳下山中青叶迎风飘摆,微风吹拂。不过尽管山野景色如何优美,盯着看了七天也终归会腻,眼皮又开始耷拉下来,长赢忙甩头,逼自己快想事情赶走这如影随形的困倦。
想什么好?
想想边城罢。
长安以西再往西走,直到走到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便是大曌与西域的交界——边城。那里的房屋皆是土垛砌成,不见一片瓦砾。人们都是粗麻布衣,勤勤恳恳。边城的人们大多没有名字,印象里父亲也是没有的,穷困的家是在边城所谓的乡下,那里更加贫苦。父亲时常带她骑着骆驼,在戈壁上放肆高歌饮酒,长赢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快意豪迈的模样,还有那曲悠悠回肠的阙歌:
“烈风卷狂如刀
铁马金戈生死相交
樽中酒心头走
一泯恩仇金沙西流
。。。”
父亲将她抱在壮阔有力的怀中,十分深邃挺拔的五官笑得温柔,
“丫头,睡罢。等你醒了,就到家了。”
睡罢,醒了就到家了。双眼随着回忆中父亲的话语缓缓闭上。
蒙然间,一双淡色的眉眼出现脑海,接着是熟悉的苍白面容,一袭月白窄袖长衫。长赢立马醒神,抓着长剑的手越发用力。
“几天了?”
突然身后传来那清冽的嗓音,才发觉周遭的温度升起许多。
不知他何时醒的,长赢心中出现一丝喜意,兀自松了一大口气,回过身仰头皱着眉看他,他面色仍是病态的白,身上的冰霜化去,打湿了他的衣和发。
“我怕我做得不好。”
公子笙看她脸上都是憔悴,听见她回过身来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怕自己做得不好,继而又见她眉宇舒展,喃喃道:
“还好你醒了。”
然后就眼一闭倒在他湿透的身子上。
他踉跄几步站稳扶好了长赢,保持着站立拥抱她的姿势,等待着身体恢复。
夜半时分,衣发被他运功弄干。摸了摸长赢的脑袋,手使一个巧劲便将她横抱起来,离开了山洞。
租了辆马车,慢慢悠悠地去了江南。
长赢就靠着他的腿躺在马车中,睡了两天两夜都没有醒来的意思。
李靖的情况也不清楚,他只能先带长赢去往离苏州不远的地方,忽然想起她来自江南,便决定前去嘉兴。把发生的事情传书若凡,让他立即派几名身手绝佳的暗卫来江南接应自己。
他低头看着长赢。倔强坚韧的小脸此刻恬静柔和,自己为何会为了救她中断驱毒使出寒掌,他不甚清楚。只是在察觉到她危机的时分,眼前晃过的是那个斗笠落下后呈现的孤冷红妆,女子执剑攻向他时红襟翻飞的模样。紧接着身子便不受控地起身救她。
他的影卫,是他的璞玉,是他的宝贝。
毒发后醒来,第一时间就在搜寻她的身影。看到她平安无事守着自己,他觉得有些高兴。过去不是没有过毒发的情况。若凡同百里渊轮班交替着照看他,除了他们,自己从未相信过任何人。
他想告诉她,她做得很好。因为她真的就把自己当作他的影子,毫不张扬安静地在黑暗角落守着他。不过她也是傻得很,当真七日不曾阖眼。
长赢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宽敞舒适的床榻上,眼睛四处打量,想知道是身在何处。
“足足睡了三日,醒了?”
声音从对面传来,长赢转头就看到了对面小榻上闭目养神的公子笙。看他脸色已恢复如常,长赢又仔细观察起他,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不适之处。
他又开口问:
“饿了吗?”
接着睁开墨色的眼瞳,随意看了眼床上的她,然后起身轻拂长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步出房门,留下一句“梳洗一下出来吃饭。”
长赢见他步态平稳轻盈,应该是没有别的什么不适才稍有放心。后想起他叫自己梳洗,才注意到十天未曾打理的身子衣物泛着臭味。长赢觉得自己倒是还能忍,只是苦了公子笙,三日来都被这熏人的气味包裹。当下立刻下床到屏风后沐浴一番。
换上应是他叫人准备的墨青色绸缎长衫,长赢散着滴水的青丝就出了房间。才发现她这是身处一间客栈第三楼的客房。
推门走进客栈二楼的雅间,坐到正在用膳的公子笙对面。
刚刚吃了两口,却听他神情自若问道:
“猜猜我们这是在哪儿?”
“嗯?”
料想公子笙也定不会就这样放弃追查鸿门之事回长安,所以两人应是在苏州附近。长赢朝窗外看去。眼前的一片一瓦,和记忆中的嘉兴慢慢重叠。
转过脸来望着兀自用菜的他,似等他说出为何带自己到这儿的答案。
“毕竟暂时不能冒险留于苏州。想起小乞丐说过,她是从江南来的,索性我就带着你来了这儿。怎么,把自己故乡都忘了?”
他眼角流有暖意,竟只是为此,便待她来了这离苏州并不算很近的嘉兴。
长赢还保持着左手端碗,右手拿筷的动作,微不可见地轻叹了口气,平静看着他的眼睛,道:“我故乡不在江南。”
接着又继续刨这碗中饭菜。
他愣在长赢这句话后。同时对心中忽然升起的不明就里的失落情绪很是费解。
原来长赢并非来自江南。他觉得连自己的影卫来自何处这么多年都弄错了,非常不对。眨了眨长眼,问:
“那,你家乡在哪儿?”
长赢饿了多日,刨起饭菜便停不下来,边吃边回答他:
“边城。”
“边城?”他执筷夹着盘中美味,放入口中咀嚼着思索,又问:“边城何其遥远,远至大曌以西之边界。你又是怎么来的江南?”
只见长赢狼吞虎咽的模样没有任何停顿改变,神情如常,告诉他:
“边城贩卖人口猖獗,我是被卖到江南的。”
公子笙举筷的手再一次停在半空。
过了一会儿,缓缓把竹筷落下搁在桌上,对长赢展开一个浅浅的微笑,才说:
“这江南嘉兴,不该来的。怪我,不知道长赢小时候在这儿有那样不开心的回忆。慢点吃,吃完,我们就离开。”
他很少笑,也并非第一次对长赢笑。
可长赢却看着他这一笑,喉咙变得干涩,心中也涌起酸楚。自己只是他的影子罢了,他何必挂心一个影子的喜怒哀乐呢?
况且,其实这江南她不开心的回忆并不多。反而,得到过很多快乐。
“公子不用。”她也回以他一笑,“被卖到这里,我挺高兴的。”
他也才意识到,知道是到了这儿之后,他的小乞丐其实话变多了。公子笙鬼使神差地问起长赢在江南发生的种种,看着她向来淡漠的眸子覆上少许光华,告诉他,被卖到青楼她打了好几个月的杂,后又使计逃走沦为乞儿,还有一帮乞丐头子欺负她,她又用阴招欺负回去。。。
他浅笑着听她娓娓道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她讲的最后一件事中凝结了微笑。
他的小乞丐,本没有名字。
“长赢”二字,有夏天的意思,一个叫宫谦的贵族少年,说她性子过冷,就给她起了这名儿。
心里不知何故生了一丝怒意,他不喜欢他的影卫,用别人起的名字。
见他笑容消失,长赢也适时闭口,微低头自责道:
“公子,我话太多了。”
他提起桌上茶壶给自己倒了盏茶,薄唇刚碰到杯沿,公子笙脑中忽然捕捉到什么。将茶杯一放,溅起几点茶水,神情莫测地又问她:
“我记得当日在长安初见你时,你身边还有一女孩儿。你方才说她是那宫谦的表妹,你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
“缪戈。”
他蹙眉思忖许久,后起身负手站着背对长赢。
长赢只听见他细微的自语声,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