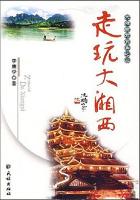十年过去现在却听到他轻声地这样吟唱。——命运的使然,我这漂泊的游子,每次思念远方的你们,我会向故乡顶礼。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在开启时,这世界变得温暖……漂泊最终让他明白了家的意义。而我们也在这歌声的陪伴中,在各自奔赴的旅途中,变得越来越坚强,自省,柔软,清晰。
从来不相信那些没有见过大海的人明白什么叫宽阔,没有见过沙漠的人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荒凉。所以也从来不相信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会明白什么叫家的温暖,了解什么叫父母的伟大。去经历过,才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那个世界,而不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那束光,一直都照亮在你行走的路上,不曾熄灭。
离开家,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东,昆仑山之西。它的西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部又与巴基斯坦相连。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一片千峰万壑相隔的洁净之地。
翻阅喀什的资料时,我开始被吸引的不是塔什库尔干这块净土,而是通往它的那条公路,和发生在路上的一些传奇故事。
中巴公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建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1968年6月,中国的筑路大军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开始施工,直到十一年后的1979年11月筑路的工作才全部结束。
在高原上筑路,就是一场与天地的抗争。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有168个人因为修建这条公路而永远地留在了巴基斯坦的北部群山中,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
曾经跟随筑路大军一同工作的巴基斯坦老人阿里·马达德,多年来一直都守着那些没有归乡的人。他每天都是天一亮就去墓地,月亮爬上来才回家。在寒冷的冬季,那里不会有一点积雪。在缤纷的秋天,那里不会有一片落叶。阿里说,这里是孩子们的家,我要把他们的家打扫干净。
内心的声音。
一种无形的力量引领着我,引领着我走向注定的命运……看完这段资料,我就决定先不从喀什直接赶往英吉沙了,我要去走一趟中巴公路。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想去看看那条公路,去看看它所达到的那些地方。
中巴公路全长1224公里,中国境内有415公里,我决定看完这不长不短的415公里。这条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公路最终没有让我失望。虽然起伏的海拔让人窒息,时而雪山那边刺骨地寒风阵阵刮过。可是我的脑子却像一部复印机,一张一张飞把这条壮阔的观景大道极致的美景都留在了心里。
我和司机王姐聊起关于这条路的故事,她却惊讶地说,我跑了好多年的中巴公路,可是你说的故事,我却是第一次听说。
塔什库尔干是离红其拉甫口岸最近的一个小城,它的街道非常地宁静,没有喧嚣和吵嚷声,有的只是风吹动街道两旁杨树树叶的声音。泥土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之中,这里如同一个与世隔绝的田园小镇。它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也许曾经喧嚣繁荣、车水马龙,此刻却只有这宁静的风轻轻地拂过。
我们的车在绕进县城的时候,路过了一片绝美的地方。它在石头城的背面,是一片绿色的草原,稀稀拉拉的几个白色的敖包点缀在草原上,中间一条小河穿过,不知道从哪里流来又要流向哪里。天上的云很低,和远处的雪山融在了一起。有夕阳照在那里,羊群变得雪白,河水变得清澈,仿佛身在画中。我想,天堂再美也不过如此。
从来没有一座小城给我如此的感觉,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息环绕着我,似乎前世曾经来过这里。也许前世我就是那牵着骆驼的蒙面过客,在这幽静的杨树林中喝水休息过。也许曾扎着漂亮的碎花头巾端着羊奶穿越过那碧绿的草原。也许还遇见过玄奘和马可·波罗。一切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在这里都不觉为过。住进一家便宜的私人旅馆,主人是当地一个漂亮的塔吉克女孩,一进门她便始料不及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轻吻我的脸颊。我吓了一跳,杵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司机王姐站在旁边偷着乐,她说,这是塔吉克族人的见面礼节,其实一般是亲吻嘴唇的。我咽了咽口水,背着包就赶忙去找自己的房间了。
塔吉克人是善良淳朴的民族,他们的善良从那一双双透彻的蓝色眼睛里就能看得见。在塔什库尔干,白天他们会把钥匙挂在大门上然后大摇大摆地出门溜达,晚上睡觉也不关门。夜不闭户,对于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到处看到的只是粗粗的防盗栏和厚厚的防盗门,把我们死死地锁在了那个封闭的钢筋水泥空间里。小时候在四合院里长大,还能体会到邻里之间的交集,现在搬到高耸的楼房里,关上自己的门,就隔离了整个世界。人和人之间已经变得那么的遥远和陌生。
塔吉克人把马粪和牛粪晒干后加上干草做火种用于烤肉,这种原始的做法并未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让羊肉更加的美味。塔吉克老太太看见我狼吞虎咽的吃相乐得合不拢嘴,我不好意思地冲她点头,冷不丁地就冒出一句,这粪可真香。汗汗汗!
王姐说,这是一片难得的净土。在新疆开车跑了十多年,这里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她说,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心里会特别的放松。
我无法告诉她,对于这一切,我真的似曾相识。可能那就是心里对生活最纯粹的一种设想。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减法,越简单越快乐。而我们都市的人却一直不停地做着加法,还乐此不疲。
塔什库尔干海拔三千米,所以温差也很大,晚上非常的冷。白天穿着短袖,晚上就得裹着大衣。夜里口干舌燥睡不着,起床去找水喝,发现走廊上有个人披着冲锋衣盘腿坐在那里玩电脑。她听见开门声抬头对我笑,你好。我说,这么晚你还不睡啊?她笑着耸了耸肩,我还在工作,怕影响同屋的人所以出来这里。听她的口音是台湾人,我说你从台湾来的吧?她点头,是啊,我已经出来快两年了。我说,是出来工作吧?她摇头,是出来旅行快两年了,我已经环游世界一圈了,中国新疆是最后一站,我就快要回到台湾了。
我这才仔细地打量起她。这个女子看上去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瘦瘦小小的体格,戴着金丝边的近视眼镜,显得有几分文气。若是日常生活中碰到,根本不可能把她和背包客联系在一起。看上去虽然柔柔弱弱的模样,却已经花了两年时间环游世界,心中不免对她多了几分崇敬之心。
我好奇地问,走了这么一大圈儿,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呢?
她想了想笑了,说不上来,好像自己正在消化掉一个地方就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现在非得要让我说,我可能会说新疆吧,因为非洲,大洋洲,欧洲,南美,东南亚,已经都快要被遗忘了,还好我一路都在记着笔记。她说,我太喜欢三毛了,所以很多脚步都是跟随她而前行的,比如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撒哈拉……
后来,我自然而然地也一起和她背靠着墙壁坐在走廊上聊天。在路上遇到有趣的人,总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她突然说,旅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她说,本来出走前我非常地坚定,可是后来却有些迷惑了。看到的景致越多,遇到的人越多,内心的感知就会重重叠加,所以开始会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虚幻。一个美丽的风景在你的脑海里能够停留多长的时间?然而它又能改变你的什么呢?走过亚马逊河时我被一只不知名字的虫子叮咬,整个小腿肿得完全没有知觉。我以为自己会死了,那个时候心里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我为什么不选择坐在优雅的咖啡厅里听着古典的音乐读一本浪漫的小说呢?一路上这些问题曾经不停地困扰着我,我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可是奇怪的是,我居然坚持到了现在。而且面对就要结束的旅途,我竟然变得有些惶惶不安了,刚才我坐在这里时就在想,其实我这样地不舍这旅途。我不断心有所感地点着头,其实有时我也会惶恐,不知道这样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只是心中不断有声音在催促,不晓得那是什么,信念?自由?也可能是逃避现实的懦弱。只是这样的声音一直在,便会一直走。
如果不是为了专业性的探索,也许行走对我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原因和目的可言,只是为了内心小小的安稳。为了等到年老时回忆这一生,没有因为它的惨淡平庸而留下过遗憾。可是谁又能说得清,即使走得再多,走得再远,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能获得更实用的感知和收获呢?因为毕竟我们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现实的境地之中。
她笑,也许正如你所说吧,实现人生价值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只是我们选择了这一种。至少我认为这一种方式它很勇敢,它能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它的美好远远比残酷要多,对吧?
我也笑,当然。
路遇知音,我们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彻底是睡不着了。脑子像放电影一样的倒转,想起了曾经在路上碰到过的那些坚韧的女子,她们背包独自行走,带着倔强和微笑一路行走在最艰苦的地方。雪山,沙漠,原始丛林,有的人挨饿受冻经历过狼袭,有的甚至遭遇打劫失去了一根小指。她们的理想也许并不大,也许根本没纠结过什么才是最终的意义,只是一直在遵循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去活着。
我在努力做这样的女子。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开,我就出门了。
石头城里特别地安静,只有我一个人。为我开门的塔吉克大爷打着哈欠说,没有这么早会来到这里的人。我看了看表,八点整,相当于北京时间六点。
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古城,它曾经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蒲犁国的王城。城的基部全部由石块建立起来,上部由土块砌成。如今这座城已经塌陷了很多,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建筑体,但是有的城墙依然还在。它们在雾气之中显得沉默,对于过去一言不发,只是保持坚挺的姿态迎着风伫立在那里。
沿着碎石的小道走上了城墙,正前方是翠绿的草坪和民居里飘出的袅袅炊烟,远处是一条延绵雪山群构成的雪线。伸开双手站立,仰头望天,觉得有眼泪想要掉下来。
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它并不是计算我们到底走了有多远,而是在停留下来的那一刻能感觉到我们离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又近了一步。
我想,那个台湾女子会同意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