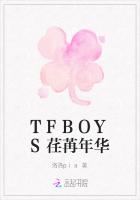牧洲跟我做同桌的时候吹破了牛皮。
他口口声声说过的天堂,其实就是地狱。
虽然我自费飞到了拉萨,但是从拉萨赶往他所在的小村落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我们坐了颠簸不堪的汽车,坐了三轮车,甚至还坐了牦牛车,可是,抵达他描述中那个美丽的山间小学校依旧遥遥无期。
在乱石密布、夜间温度骤减的山涧间穿行时,我甚至都想写一封遗书让陈牧洲捎回去了。
我们头顶是白雪皑皑的雪山,脚下是滚滚的江水,我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我承认,这里的风景的确是美的,甚至比陈牧洲照片里拍的还要美,但再美的风景也要有命看完不是吗?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陈牧洲一路上都很照顾我,他甚至用一条绳子将我和他拴在了一起,以免我不小心滑落。我的脚底板磨出了血泡,再三推脱后,他突然毫无绅士风度地将我背起,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宿营地,他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抱歉的表情,在将一杯自己调配的热腾腾的酥油茶递到我手中后,轻声对我说:“害苦你了,乔小安。”
我闭上眼睛,尽量将自己放空,我怕我一个忍不住就泼他一脸。
好在,在我吞下第七杯难喝的酥油茶之后,我们真的远远地看见了那座横跨在小小山涧间的石桥。
据说,每到夏季,山巅的积雪就会融化,河水暴涨,而且异常寒冷,涉水前来上课的孩子每次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忍受巨大的痛苦。
同行数天,站在桥上的我,第一次对陈牧洲露出了微笑。
我真怕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骨子里的乔小安是那样义无反顾地相信着他。
河水哗啦啦作响的桥头,陈牧洲将立在桥头的青石碑亲手指给我看,那上面刻满了捐建者的名字,而第一个名字就是身为班长的我。我找到了高二三班所有人的名字,却唯独没有找到陈牧洲。
在被我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笑得像个调皮的孩子。
他说:“我是骗子啊!骗子怎么能上光荣榜呢。”
那一次,热情的孩子们升起了篝火,他们唱着歌儿将洁白的哈达戴到我的脖子上。
火光映亮了一双双闪亮的眸子,我终于相信,在那遥远的地方,真的会有陈牧洲所说的天堂。
我用没有信号的手机拍了好多好多照片,繁华都市里早已消失不见的白云与眼神、因为汛期来临而变得异常泥泞的小道、孩子们破烂的课桌以及那座崭新的小桥。
第一次,站在陈牧洲身边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骄傲。我觉得,是他,让我们变得仿佛比以前更有意义,更理解幸福的含义。
我甚至都想好回到学校后怎么来一场声情并茂的演讲了,我是班长,我有这个号召力。
可是,大骗子陈牧洲却再也没有给我这个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
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在去到他所支教的那个小学的第三天,我就病倒了。从来都只会连累我的陈牧洲发神经一般,为了帮我补身体,居然天未亮就跑到牧民的牦牛圈里挤牛奶。他走时,还调皮地眨着眼睛对我说:“知道吗乔小安,这里的牦牛都认识我哦,看见我肯定多多下奶!”
结果,也许是手法不够娴熟,他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护犊认生的牦牛。发疯的牦牛追着他四处乱跑,终于在快到小学时追上了他,一脑袋顶在了他的屁股上。
然后,陈牧洲就从新建成的石桥上落进了水流湍急的河水里。
当大家在桥面上发现打翻的饭盒时,水面上早已没有了他的身影。
河水落差极大,在几里以外汇入涛涛的雅鲁藏布江。
那一次,所有孩子都没有哭,他们虔诚地相信陈牧洲不久以后就会回来,而哭声会让他迷失了方向。
那一次,村民们选代表将我送出了山,因为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而那里得不到该有的治疗。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要对陈牧洲说的,看样子,我的身体等不到他回来了。
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因为一个叫“那日”的小朋友告诉我,阿妈告诉他微笑能给迷失在远方的人指引方向。
我的耳边不停地回响着同桌陈牧洲骗我的那些话。
他说,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每个人都笑得很真,很傻,那里有可爱的牦牛,清澈见底的河水,让人不敢直视的阳光。
我想,他自始至终都是个骗子。
2013年10月,我第一次放声大哭,是在高二三班那场关于陈牧洲的演讲会上。
我将从手机里拷下来的照片,用幻灯机一张张放给同学们看,台下鸦雀无声。
那一次,校长撤销了“关于陈牧洲同学的处分”,并且还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宣传栏里的光荣榜。
校领导带头,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号召同学们捐款,募集了很大一笔资金。
据说,那笔资金不但可以帮藏区的那些孩子盖一间像样的图书馆,还能帮他们购置很多崭新的课桌椅和文具。
而对于校长让我和其他几位老师代表学校一起去当地捐助的请求,我却笑着拒绝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是为什么。
我害怕的是,当我千山万水、不辞辛苦地去到了那里,站在桥上迎接我的人群中没有他。
我想,平凡如我,还是比较喜欢隐藏在嘈杂的都市里,那样才有安全感。
我会在某个放学的午后,偷偷隐藏在流浪狗那日的狗窝附近,小心翼翼地守候着,大气都不敢喘。
然后,猛地一个箭步,捉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