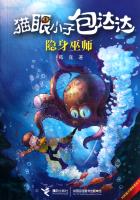“娘娘,太子殿下来了。”婢女的声音从屋外细细传来,话音刚落,便听见木门“咯吱”一声被人打了开来,一人踏进了屋内。
高挑秀雅的身材,橘红色上好绸缎上绣着十分精细的蟒,披领为紫貂,袖端用熏貂。腰间系着的嫩粉荷包却显得格格不入。太子继承了其母妃敏氏的较好容颜,肤色白皙如女子,一双桃花眼眼底含情,嘴角微微上翘,经过指出皆留有清香;看遍天下,比此人更美之人,怕是屈指可数吧。
楚长瑜原是靠在榻上小憩,被脚步声惊醒,悠悠睁眼,才刚睁开眼来,太子便走到了她的面前,似笑非笑的看着她,笑却不及眼底,更似有一丝愤怒。
他也不管她是否请安了,坐在她的身侧,端起她放在桌上早已凉透的茶,看着榻上卧着的美人,语气不明的道:“本殿下听说,贞毅将军今早曾来拜访过太子妃?”
她抿抿唇,温和回道:“兄长远去北荒征战已有数月,今日回程,有了空闲时间才来看的臣妾,其实是奉家父家母所托,转送给臣妾一封家书罢了。”
他藏在袖子里的手紧握成拳,眼中嘲讽和愤怒一览无余,他咬牙道:“空闲?亲爱的太子妃,贞毅将军可是连赶数日,人人皆道将军归心似箭,本殿下本来还好奇呢,到底是什么人或事能让将军如此归心似箭,现在本王知道了,终于知道了。”
他起身,大步上前,将楚长瑜的下巴死死捏紧,嘲讽的道:“原来是我的好太子妃啊!奔波数日,连军营都不回,皇上也不见,下了马就赶来太子府了,你们的兄妹之情,真是让本王感动啊。”
她脸色苍白,眼底闪过一丝凄凉:“兄长是受父母之托……”
“你以为我会信那些话吗!长瑜,你别把我当傻瓜!”他终是受不住,青筋暴露,愤怒的嘶吼着,像一只暴怒的狮子,捏着她下巴的手更紧了,她感觉自己的下巴就要被捏碎了,咬牙喊出了一声“疼……”。
他看着她,还是放了手,转过身去,不再看她,突然的寂静显得十分诡异,她心如乱麻,眼底泪水终是忍不住,迸涌而出。
听到身后微微抽泣的声音,他身躯一震,拳头捏的死紧,过了不知多久,他平淡无波的缓缓说道:“太子妃的心里既然没有本太子之位,那我不进便是。”
说完,已不见男人身影,只有他身上传来的徐徐清香还顿留在屋内。
她苦笑,果然两人还是……终走到了这一步啊。
*************
酷暑难熬,天早早便亮了起来,树上蝉鸣从院内传来。婢女们拭了拭额上的微薄细汗,继续扇着扇子。
楚长瑜最讨厌的季节便是夏季,每当酷暑来临,她便要搬到朝北的屋子里居住,整日不出门,让婢女们扇风,冰窖伺候。
不知不觉入住这清宁宫已有五年有余,自先帝驾崩太子顺位登基之后,她便在此住到如今。
也被锁到如今,像只金丝雀一样,只不过这主人对这鸟从来不闻不问罢了。
自五年前那晚起,她便在没跟太子说过一句话,人前夫唱妇随,别人只会以为她是故作矜持,哪知道,这皇上皇后,早在皇上容旻还是太子时,便已经貌合神离了。
而他……她眼底滑过一丝苦楚,楚长斐自容旻登基后,容旻便下旨册封他为安毅大将军,命他看守北荒。臣子们都道是皇上不惜人才,她倒觉得,皇上恐怕也想惜,只可惜,自己偏偏和此人扯上了关系……
她自是知道楚长斐为何人,他去北荒之后,非但没有荒废,反而在北荒树立起了极好的名声,安毅大将军的拥簇者日益剧增,家父又是尚书令,家母还是众命妇之首,再有她这个皇后,楚家势力已不能以大来形容了,恐怕皇家之下,便是楚家最大。
她也清楚,皇上又怎么可能让楚家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呢,他怎么会不怕,怕楚家再这么下去,哪天便会吃掉容氏江山?他恐怕正在策划着,将楚家连根拔起,一人不留吧。
若是真到了那一天……父母,自己,还有他,恐怕都……。
她不甘心,她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楚家栽进容旻陷阱里,她要做点什么,起码争取一下。
想到这里,她猛地睁开眼,喊道:“来人,拿纸笔,本宫要写封家书给……”
“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一鹅黄衣宫女匆忙从外跑来,气喘吁吁的噗通跪地,道,“皇上在楚尚书令府里找到了楚尚书与总管太监,明国军师私通的书信,上面写着‘九月九日,便是容氏江山易主之时’皇上震怒,当场便斩了总管太监与……与楚尚书的人头,当场抄家,恐怕安毅大将军也凶多吉少……而……而娘娘您……皇上正命人往清宁宫赶来呢。娘……娘娘,我们怎么办呀?”
楚长瑜再无力气,手里端着的凉羹洒满一地,心里这环绕着‘当场斩楚尚书项上人头’和‘安毅大将军凶多吉少’这两句话,满腔苦楚,更是讽刺,原来她再算,也永远不会比英敏神武的皇上快,他等这一天,恐怕等了很久了吧。
一阵脚步声传来,一个太监端着一酒壶和一酒杯,随着走在前面,身着明皇色衣之人进屋。
她并不想回头,只能听到众人惶恐跪地,并齐齐呼喊着“参见皇上”的声音,呼一口气,笑着转过身子,迎上了他深沉的目光。
登基多年,他的城府比当太子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完美无瑕的掩盖自己,更学会了,如何无声无息的除掉碍眼的绊脚石了。
目光投向桌上的酒壶,她笑意更浓,他没料到她是如此反应,微微皱眉。
“皇上是念及多年结发夫妻,来送臣妾一程的吗?”她笑着看他
他紧攒了攒拳头,并未回答。
“楚家风头太盛,有意谋反,诛九族都不为过,不禁是家父,还有臣妾,还有楚家上上下下数百人的性命,更有安毅大将军,对吗?”
他拳头握的更紧了,却还是一言不发。
她坐在凳上,仰头微笑的看着他,仿佛就像多日未见的情人,用葱葱玉指拿起酒壶,倒了满满一杯酒,端起放在鼻前闻了闻,仿佛十分陶醉地感叹了声:“是臣妾最喜欢的秋露白,没想到十年前的一句话,皇上至今还记着,人生尽头时能饮一杯秋露白,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他薄唇紧抿,眼底有几分不舍,在她即将饮下之时道:“你若是想,又如何会走到如今。”
她手一颤,凄凉的笑了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眼底蕴藏了太多的东西:“这也是皇上您的选择不是么?”
他身躯一震,薄怒地看着她。
不愿意再做无谓纠缠,一口饮尽,秋露白十分呛口,仿佛在体内燃烧,似乎要将这段孽缘,烧成灰烬,不留一丝痕迹,她笑得更艳了,胃里绞痛难忍,强忍着笑道:“但求下辈子,无容旻,无斐郎,无牵挂,无忧愁。”
他看着倒在地上,口流着鲜血的她,闭上了眼:“都给朕出去。”
众人不敢怠慢,待众人离开,他单膝跪地,颤抖着用手指覆上了她紧闭的双眼,一滴泪水滴在她白皙的脸颊上,缓缓流着。
天启五年七月初三,楚尚书意图勾结明国谋反,楚氏九族皆诛,皇后楚氏薨于清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