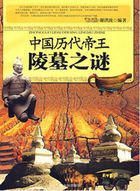“陛下,恕奴才直言,鲁骞乃世之神匠,您有所不知,他在民间,黔首们都称颂他为‘鬼斧神匠’,足见此人非同一般啊!虽说皇陵已然建成,留他又有何用,在陛下看来,留他非但无用,反而有患,可依奴才愚见却不然,皇陵虽然建成,可难保它没有半点瑕疵纰漏,建皇陵一事由鲁骞一手操办,万一皇陵有何瑕疵纰漏,到那时鲁骞已死,如之奈何?此乃一患也!再者,鲁骞虽幽禁于陛下手掌之中,无甚大碍,可鲁骞妻小尚在民间逃窜,若是陛下盛威之下斩了鲁骞,让在外逃窜妻小得知,难保鲁骞妻小不为其报仇啊,更让奴才担心的是,若是其妻小有皇陵图谱,那就……”
赵高说至此,只见秦始皇甚是不悦,怒斥道:“够了,狗奴才!”吓得赵高连连后退数步,跪下求饶道:“陛下息怒,陛下息怒,是奴才一时失言!陛下英明神武,何事能难住陛下呢?都怪奴才多嘴!”他说着便在自己嘴巴上抽了三下,始皇才道:“知道便好,起来吧!”赵高跟随始皇多年,知道始皇为人性情素来孤傲自恃,目中无人,即便哪位大臣谏言正合他意!但如若措辞稍有不甚,就会勃然大怒,瞋目而视,作吃人状!自始皇吞并诸侯,兼并天下以后,最怕人提及“死”字,凡是有人提及“死”字或是有关“死”的东西,他便会怒不可遏,可赵高适才一再提及‘皇陵’二字,话语中,又有个“死”字!试问始皇岂能不勃然大怒呢?故而赵高自称道:“失言”之语!
此时始皇才面无怒色,坐在龙榻之上,手指着奴颜婢膝的赵高:“赵高,真人若不念在你平日伺候真人有功的份上,就凭你方才那些话,非处死你不可!日后再敢在真人跟前提些污言秽语,小心你的狗头!”此时吓得赵高两腿发软,跪倒在地面无血色道:“谢陛下不杀之恩,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一面说一面叩头谢恩,样子十分可怜!龙榻一端坐一美人,秦皇也不避讳,便在那些太监面前调戏那女子。始皇大统天下后,自称为“朕”,后因求仙人不死之药,改称为“真人”!
“别老跪在那儿了,去,把左丞相李斯给真人召来!”秦始皇向赵高命令道。赵高唯唯诺诺地站起来道声:“诺!”遂向秦皇龙榻外疾步行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丞相李斯才至宫殿,赵高道:“左丞相,您先在此候着,陛下马上就来!”赵高口中的‘在此候着’指的是秦皇的御书房,此间乃是专供秦皇召见朝中大臣之所!须臾秦皇龙袍加身,衣冠楚楚地从后宫来至御书房,俨然没了方才的衣冠不整,行为放荡之态,霍然成了一位驰骋疆场、君临天下,傲视群雄之气的皇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斯见到秦皇赶紧行三拜九叩之礼,口赞吉祥之语!
“丞相,平身!”秦皇坐在龙椅上脱口说道。“谢陛下!”李斯遂谢道,谢完遂起,起完又道:“不知陛下召唤臣来有何要事?”秦皇遂退下左右,才道:“真人欲斩了鲁骞,不知丞相有何高见?”
“恕臣直言,万万不可啊!”
“说说看,为何不可?真人愿闻其详?”
“那臣就斗胆说了,不可有三也!一、陛下地下宫殿初建成,定有不美之处,留着鲁骞正好将地下宫殿进一步完善,此乃一不可也;其二、鲁骞妻儿已逃窜民间,若是他们真的有地下宫殿图谱,只要鲁骞还活着,他们便不会轻举妄动!此乃二不可也;其三、只要鲁骞活着,陛下可以随时命他改变宫殿的机关和开启之法,若能如此,便是有人得到了地下宫殿的图谱,又能奈何?此不可三也!臣乃愚见,还望陛下定夺!”李斯作礼谦让道。
“好,好啊,如不是丞相,真人差点铸成大错矣!”秦皇拍案叫好道,李斯谦卑道:“陛下乃圣明之君,臣只是略陈陋见,何足道哉?”秦皇听了,喜不自禁,仰天大笑起来,一阵大笑过后,秦皇又道:“那真人便把鲁骞之事全全交付与丞相处理!”
“臣定不负陛下之命!”李斯包拳鞠躬道。
“还有此事,乃机密,除了赵高与丞相知外,绝不能外泄!违令者,族矣!”秦皇语气甚是严厉!
“臣不敢!”李斯怯懦道。
“下去吧!”秦皇边喝茶边说道。“谢陛下,臣告退!”李斯遂拜道辞,退出宫殿……此事暂说于此,后话再叙!
且说那日白衣女子从醉仙居骑马归来说起……桓楚早已体力不支,饥饿难耐!白衣女子遂不忍心。让他骑马归来,连吃三个大饼,连喝三碗热汤,方止!
次日,桓楚没让白衣女子唤他,他便早早地起床了!他起床虽早,不过还是没白衣女子起得早,当他起来的时候,白衣女子已经在院内开始练功了。“早,白狐姐姐……”桓楚刚行至门外便向白衣女子问好道,“我不是说过,不许你唤我姐姐的吗?”白衣女子听见桓楚又叫她姐姐,故而一边练功一边说道。桓楚默然了片刻,低下头想:“她可真怪!她比我年长,我叫姐姐是应该的,她是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了?”此时白衣女子已经停止了练功,走到了桓楚面前。“你为何老不让我叫你姐姐呢?我明明没你大的!”桓楚仰起头看着白衣女子的眼睛天真地问道。“这……”白衣女子看着他的眼睛,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遂把头掉了过去,背对着他说:“我只是不习惯生人叫我‘姐姐,姑姑’什么的……”
“可我也不习惯唤比我年长人的名子啊,尤其是对我好的人!”桓楚脱口而出。
“那我对好吗?”白衣女子明知故问地柔声问道。“姐姐不是对我好,而是对我很好很好的,您那夜从那么多坏人的手里将我救了出来,还要教我习书练武,这是我长这么大,除了家里人以外,您是对我最好的一个!”桓楚本是个聪明的孩子,又和白衣女子说了近日来朝夕相处,故而说起话来,没有了怯意,既无怯意,说起话来自然有水平。白衣女子听到桓楚说到此,不觉有几分感动,遂转过身来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嘴巴还蛮厉害的,算了,那你往后爱怎么叫便怎么叫?随便你!”桓楚听到这儿,兴高采烈地唤道:“是,姐姐!”从此以后,桓楚便唤她‘姐姐’了!
白衣女子从小就是个孤儿,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自从她被义父收养后,义父每日都硬逼着她学武认字,若是把当日教过的武功或是书没记住,义父不但不让她吃饭,还要用鞭子抽她;就算她全学会了义父教她的东西;她还是吃不饱,不是吃得多,也不是义父给她吃的少,而是她吃的都被师哥师弟抢去吃了,剩下得只是残羹剩粥,她几乎每日都吃这些东西度日长大的,故而从来没人那样夸过她。“好了,你洗脸了没有?”白衣女子关切的语问桓楚道,“适才洗过了!”桓楚干脆地回答道。桓楚刚一说洗过脸,就见白狐姐姐什么也没说,便进了木屋,桓楚一时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正纳闷时,白衣女子又从屋里走了出来,只见她手拿一卷书简,桓儿便猜出一二了,定是要教他诵书的,“姐姐,您手上的拿的是何书啊?”桓楚好奇地问道白衣女子只简单地道了一句:“!”
“您要教我?”桓楚显得很是吃惊地追问道。“没错?”白衣女子一面打开书简一面对他说道。“我在家时,爹爹已是教过我的……”桓楚说话的样子不知为何一副很小心的样子道。
“什么?你习过?真的?”白衣女子女子显得很是吃惊,“是啊,爹爹说过想当一个出色的木匠,就得先从学起,故而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诵读的,只是眼下有些记不全了……”桓楚又一边说一边抠着自己的手。“你爹爹是作木匠的?”白衣女子试探的语气语问道。桓楚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白衣女子见她问到此,又勾起了桓楚伤心的往事,遂岔开了话题道:“既然你会诵读,想必书简里的字你都认得?”
“也有不认得……”桓楚照实回答道。“那好,你先诵读,若是里面有不认识的字,你便问我,好不好?”说着白衣女子便把书简递互他手里,桓楚吃惊地问道:“姐姐是不是又要丢下我,出门去?”
“没有,我给咱们去做饭,要不然早上吃什么?”说完白衣女子转身便进了小木屋……
当白衣女子踏进木屋做饭,桓楚才发现,白衣姐姐脸上的面具换了,换了金色的金属面具!
“饭做好了,桓,吃饭……”白衣女子一柱香的功夫饭便做得了,于是急忙唤正在看书的桓楚!桓楚遂应声道:“好,我把这句话读完,就吃,姐姐!”白衣女子唤过他后,便又进得屋来,去端菜盛饭,刚一切弄好,白衣女子见桓楚就进来了,便说:“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
“噢!”说着桓楚便打了盆水洗了脸,走到饭桌前,看着丰盛的饭菜,不由得咽了几下口水,遂道:“姐姐,你做饭做得可真快啊!而且还很香!”白衣女子回答说:“俩人的饭,做起来自然快,我看你肚子饿了,你赶快吃吧?”白衣女子刚说完,桓楚便端起碗来要吃饭,可不料他刚托起碗,不知怎么的,碗就摔在地上,于是碗碎了,一碗白白的米饭便撒了一地,还没等白衣女子开口问他是怎么了,他便解释说:“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的,不知为何,早上起来我的胳膊很重,拿什么都是软绵绵的没力……”
说着他蹲下身子捡地上的碎碗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