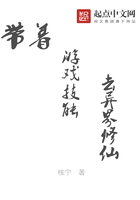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艾姬,想让她也来分担我的快乐,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想正式上班之后告诉她,以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天我骑车慢悠悠地在科大学校里转,相信谁也不会怀疑我不是学校的一员。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学校里。本来开学的时候想来学校看艾姬的,但由于有她父母的陪伴,我便不能来。我在学校的几个交叉路口偷偷徘徊,企图看看她的父母是何许人;但等了大半天连艾姬本人的影子也没见着。
艾姬所在的班级已经让她落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若是其他人这样中途插班恐怕不行。为把落下的课程补上,她得加紧追赶才行。她没和我长时间在一起,我不应该有任何的理由去埋怨她。
人就是一个奇怪的生物。遇到顺心的事时,黑暗的也会是光明的;相反,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光明的也会变成黑暗的。
在未上班之前,趁着这浓浓春意,我独自来到浣花溪公园。说实在的,一直在成都生活这么多年,至今也舍不得花那几十元钱去看一下杜甫草堂。每每只能在那大门外轻轻观望。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哀思仿佛仍在我的心中流淌。
年初“人日”这天,众多的人去拜祭这位伟大的诗人,而我却躲在家里噙着泪吟诵着他的诗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我用这种奇特的方式表达着我这久远的情感,并非像有些人那样附庸风雅地去打扰诗人灵魂的安宁。
清代学者、书法家何绍基诗云: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人日即每年正月初七,纪念诗人由此而来。
浣花溪公园是我最喜欢的公园了。这里有许多公园无法相比的宁静;这里有胜似田园生活的美景;这里有历代许多大诗人飘浮的身影。它是都市生活里一片难得的净土。
我走在用石板铺就的羊肠小道上,听着那流传千古的古琴曲《流水》,仿佛整个身心已化成碎片在随着那潺潺溪水流淌;路旁的美女拨弄着我的心弦,仿佛曾经的西施和范蠡在梦中荡舟戏游。
走累了可以坐在木椅上歇息,头上有遮阳伞;想方便了可以到不收费的挂着画的公共卫生间,艺术熏陶无所不至。周末这里有精彩无比、逗人好笑的极具川味的文艺活动,比花几十甚至上百元在那些所谓的俱乐部看一场表演划算得多。
每当我要离开时,我都不知不觉地默念着我过去画作上的一首诗:蝴蝶翩飞闹花香,鱼儿戏水翻白浪;本是春来一幅画,落款题名浣花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