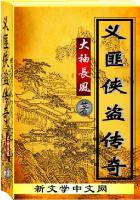夕阳余晖,映得西苑金碧辉煌。入茶树围绕的春熙门,穿过长竹藤架,登上挂满用茶叶填充的香囊的回廊,伴随着淡淡的茶香行过穿堂,见院中的茶花树已与正殿的黄琉璃歇山顶比肩。
推开半掩的黻(fú)亚纹隔扇门,烨帝御笔的“怡然自得”匾渐渐从昏暗里露出光彩,走过花梨木透雕松鹤长春落地罩,只见鑫贵妃一身金红色锦帐芙蓉的氅衣,优雅的倚在西次间盘长纹和合窗前的软榻上闭目养神,室内的掐丝珐琅香炉云雾缭绕,袅袅缠绵,嗅起来倒是格外清新。
“母妃还是这样喜欢焚这样重的香料,仔细身子。”
鑫贵妃缓缓睁开眼,“我儿回来了。”
景昱依礼跪拜,“请母妃千岁金安。”
“你甚少对我行此大礼的,看样子,儿子不是很乐意为娘的安排。”
“儿臣不敢。”
“你不敢?普天之下,恐怕没有你不敢的事情吧,左侍郎大人。”一听这话,景昱缓缓抬起头,看鑫贵妃拉着长长的脸,瞪眼看他,“我知道你还是怨我,否则你也不会一直待在太微宫不肯回来,可即便我不拦着,你就能跟她在一起吗?你想想清楚,有他在一日,便不会是你。”
“儿臣不敢埋怨母妃,儿臣知道,母妃一切都是为了儿臣好。”
“你是一个懂事要强的孩子,少时得蒙陛下眷顾,如今又是如此的出息,娘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但只这一点上,为娘断断不能顺了你的意思。男人一旦儿女情长起来,就忘乎所以,你该效仿你的父皇,权衡轻重,舍得放手。道理,你是明白的,所以既娶了她,就收敛你的脾性,好好把戏给我演足了。至于其他的,你无需插手也不必管,我自会为你处理。你且放心大胆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没有了嘉氏和阮氏的支持,奇氏亦是你的后盾。”
“儿臣定不负母亲厚望。”话间,景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锁定窗外的铭婼,却故意恶狠狠斥道:“是谁?滚出来!”
进了屋,铭婼朝景昱冷笑道:“多年不见,昱哥哥功成名就,气度非凡,脾气更是渐长啊!怎的,有好事情,不许我听听吗?”
景昱望着朝自己款款而来的可人儿,这在他心尖上的人,她的心竟跟他的隔了那样远。
从前是,现在是,未来更是。
此刻的自己对着她的十分爱里竟生出了两分恨,三分畏。
恨她利用自己,畏她迷失了自己。
日下西沉,幽蓝色的天际浸染整个空翠楼散发着郁郁之气。
“送你的新婚大礼,可还喜欢?”
并不习惯铭婼这般阴阳怪气的说话,景昱没有抬头看她,反问道:“为什么要回来?”
“这话,刚刚你怎么不问姑母呢?难不成,你没胆吗?”
看着那不曾见过的妖媚眼神,别过眼,郁郁道:“我想听你亲口回答我。”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
铭婼一针见血,直插景昱心底,“好,当我没问。”
铭婼不以为意,转念改变话题,“我并不觉得她跟我像,一丁点儿都不像,她,永远都替代不了我。”
景昱苦笑,对这波澜不兴的玩味话语回复道:“没错,她的确跟你一丝一毫都不像,她不是代替你,她就是她。”
不想铭婼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就这样,你甘心吗?”
景昱长叹一口气,“一切都晚了,太迟了。”
“那是你,不是我,你要的是天下,而我,只要他。”
寥寥字句,狠戳入心,景昱肺腑恸切,无以复加,神色恍惚道:“没有你,我要这天下也是枉然。”
“别以我为借口,多冠冕堂皇。”
“你始终是不信我,连个机会都不肯给我。”
凝视景昱难掩的失落,铭婼不为动容,“即便我信你,但你可能不争吗,别傻了,就算你真的无心,也会有人为你而夺,你会唾手可得的。”
景昱终还是忍不下心,不由自主的拉住铭婼的手,“你真以为听之任之就能得到吗?”
“不,我只靠我自己。”
那双手,似那极北寒地的冰霜,冷得令人发憷,良久都捂不化。景昱失神一笑,“是你命人偷了家谱,故意陷害给太子的吧。”
闻言,铭婼即刻将两手从景昱那滚烫的掌心抽离,不屑一顾道:“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是一直都在找机会报当年之辱,但那鲜为人知的真相,连姑母和你都不知道,我又从何得知?”
景昱压抑住内心的凄楚,用力攥紧拳头,试图让自己理智一些,“他没告诉你吗?”看铭婼摇了摇头,景昱试探道:“那宸妃的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宸妃曾因荣正皇太子之死遗弃景明,而她在失宠之后被烨帝赐死。此事不如前事藏得深,紫微宫里难道不是人尽皆知吗?”
景昱狐疑的看向铭婼,惶惶道:“难道......你是想以此要挟他?”
“弑母之仇,他会不为所动吗?”
景昱不禁苦笑,“你太小看他们的感情了。”
“那也比不过我和他的青梅竹马之情,不要忘了,是谁陪他度过了那些阴暗的日子。”
铭婼此话一出口,便让景昱彻底清醒了,“我奉劝你别太把‘青梅竹马’当回事,你我如是。”
“我欠你的,拿这天下来还,而你欠我的,你拿什么还?”
“你要的太多,今生我还不起,若有来生,我再还吧。”
“也罢,那就拭目以待,走着瞧吧!”
看着秋菊端着丝毫未动的饭菜出来,景明缓缓闭上眼,低下头不语。
秋菊叹了口气,劝道:“殿下,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劝劝主子啊,都一整天不吃不喝了,这样下去,主子的身子可是熬不住的。”
半响,景明终于抬起头,欲言又止,只摆手示意秋菊退下,自己默默的转身迈步。望着景明失落离去的背影,秋菊不禁心酸。
自壬午年景明入“励精图治”上书房起,秋菊便开始服侍他。看他在宸妃病逝时受惊生病,在塔娜郡主逃婚后喜怒无常,在算计娶亲时暗暗窃喜。她甚是熟悉他的脾性,她在想,究竟是怎样的女子值得他那般用尽心思,耗费精力去谋划?直到去年重阳,崇政宫宴上,一清丽高挑的娇娥,宛若她衣上的朵朵蓬莲,亭亭玉立于大殿正中,集聚众人玩味之目光。她无法称之为倾城倾国、国色天香,她不如塔娜郡主可人尤怜,不似恪纯公主高贵清冷,不会于万千之中引人回眸侧目,但看景明嘴角刻意掩饰的笑意,秋菊笃定,这就是他想要的。
云桥之上,她刁横野蛮,毫无大家闺秀的端庄,却又不如旁人一般对自己的骄纵刻意加以掩饰,她是那么自然而大方,行云流水的套招,让景明毫无招架之力,轻而易举的套牢了他的心。起初,秋菊是担心景明会落空的,因为凌芸乃皇后嫡亲侄女,阮家身为烨帝岳家,加之镇国将军夫人母家是代表华夏一族的羲氏,仅仅给一个侧妃之名分,实在是委屈而不光彩的事,传出去,必会满城风雨。另外,侧妃是没有大婚仪式的。却不想凌芸不以为意,就那么简简单单的乘坐一顶轿子嫁进明居。
二人这一路的经历,前途漫漫,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荆棘,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得以跨越?
迷雾中,不知是谁笑得那么畅快,又不知是谁笑得那般得意,断断续续的娇笑声,缠绕在耳边久久不肯散去,死死地揪着凌芸的心,一丝不肯放松。“谁?是谁在笑?”凌芸在雾中胡乱的拨弄,试图寻找到方向逃离。忽然,一抹湖水蓝在眼前浮现,凌芸急切的上前想去揪住她,“都是你,在景明的心里,我永远比不上你!”
哪知手还未触及那湖水蓝,便瞧着一边又多了一抹红色。那身着大红色喜服的人缓缓的回过头,却丝毫不放松搭在那湖水蓝肩上的手。可待凌芸看清那人的脸,她彻底崩溃了,她疯狂朝那湖水蓝扑去,两肩却被一股力量拉扯得生疼,电光火石间,眼前一片漆黑。
猛然睁开眼,看着帷帐上挂着的香熏在晃,惊魂未定的凌芸意识到方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噩梦,而自己却依旧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渐渐清醒,发觉自己被一个人紧抱着坐在床上,她下意识的挣扎,“你谁啊?”话音未落,一股熟悉的体味飘来,凌芸急切的推开身前的人,借着微弱的烛光,她看清了她梦中看到的那张脸,“混蛋,连做梦你都要来气我,跟她合起伙来气我一个人!”任凭凌芸拍打撕扯,眼前的人始终无动于衷。
是什么滴在了手上,好凉。
凌芸恍惚停下手,不自觉的朝那低着的头伸出手,尚未触及就被一手拦下,而他的另一只手紧捂住脸,不敢直视凌芸。
“你哭了?”凌芸诧异,“你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凌芸不顾他的挣扎,硬是抱住他的脸,仔细端详,看他眼中闪烁着泪光,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忧郁、无助与失落,如此情形下,她已再说不出任何恶语气话。她不禁主动吻了一下他的唇,安慰道:“对不起,我不该这么使性子的。”他不出声,只摇了摇头。
靠在他的肩头,凌芸默默的说:“你是在乎我的,对不对?你若不在乎我,你才不会那么生气,可是,我现在真的好怕,好怕你一气之下就不要我了,刚刚在梦里,你就不要我了,你跟她重归于好了,你们在那里笑,很开心的对着我笑。”凌芸突然起身,语无伦次的哭诉道:“景明,她回来了,你就要奉旨娶她了是不是?可是,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没办法看着你娶别的女人,当然,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你是皇子,是郡王,你此生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想乞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至少,至少等我们有了孩子的,我有孩子陪着的时候,我......”话到此处,凌芸彻底崩溃,嚎啕痛哭起来,“我真的做不到......我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昏沉中,唇上一丝温热,却又有一丝冰凉,很深很沉,仿佛自己要窒息了一般。
难得喘息,眼前一亮,欲要起身,一时视线模糊,头昏脑涨,待眼前清楚,只觉得浑身困乏无力,转头观望,房内灯火通明,凌芸方知,不过一梦中之梦,痴缠魇住了。隐隐嗅到药味愈加浓烈,只瞧秋菊疾步上前,忙放下手里的托盘,扶她坐起,又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长出一口气叹道:“主子可算是醒了,我这就去偏殿请阮妃过来。”
“等一下,”凌芸一手拉住秋菊,诧异道:“我这是怎么了,何以阮妃会在?”
“自从殿下走后,主子连日高烧不退,皇后娘娘和嘉贵妃娘娘亦不在,公主有孕又不好去惊动,奴婢没辙,便去东宫请了阮妃过来主事。”
“怎么都不在?”
“殿下事先未与主子提及此事吗?”秋菊一愣,见凌芸目光呆滞,便缓缓道:“因裕世和熙皇太后忌辰,各宫皆随圣驾于十五日去了东都,现下唯有您和阮妃在宫里了。”
“那今日?”
“今天是十七,”瞧凌芸欲言又止,秋菊会意,说道:“殿下临行前来过,见您睡着,便没有让我唤醒您,只是悄悄的,”说着,秋菊面色含羞,不禁抿了一下嘴唇,弱弱道:“亲了您。”
凌芸心头一颤,却听凊葳一声嗔笑,“瞧你这醋吃的,人家也没怎么着呢,你倒是好,先自乱起阵脚,把自己酸晕了头。”看凌芸一张苦瓜脸呆坐在床上,凊葳在床边停住脚,白了凌芸一眼,“真是难得让我逮着机会好好笑话笑话你。”说着坐在床边,示意秋菊递上药碗,舀满一勺汤药送到凌芸嘴边。
凌芸连眨了几下眼,故意气道:“不劳阮妃娘娘大驾,还是......”
“少矫情,赶紧张嘴,本宫这手举着很酸的。”
凌芸任由凊葳喂了药,顺势倒下,复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秋菊掩好门,方一转身,却见凊葳仍立在廊下,谨慎上前,躬身问道:“娘娘有何吩咐?”
凊葳浅笑,“你倒是机灵,”转瞬变了颜色,冷冷道:“我来了两日,独你一人上前伺候,却不见莲心,她人呢?”
“回娘娘,阮淑仪也病了。”
“真是主仆情深,同病相怜啊!”
凌芸再醒来之时,已是深夜,口渴难耐,奋力爬起身,只看秋菊坐在床下,趴在床边睡得极沉。知她照顾自己劳累,凌芸不忍叫醒她,便仔细掀了被子,悄声下床,踮脚走到桌前,连倒了两杯水喝,才解了渴,顺手拿了搁在桌上的斗篷,走到秋菊跟前,正欲给她披上,却听屋外传来一声惊叫,唬得凌芸险些叫出声来,之后被月光笼罩的明居刹那又恢复寂静。
缓缓打开房门,凌芸忐忑着迈出一只脚跨出门槛,乍见脚下一个白影窜过,惊得凌芸屏气闭眼,再睁眼定神往外一望,却是一只白猫奔向了牡丹堂的西山墙。不过虚惊一场,凌芸长出一口气,正要合上门,心里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会有猫?
“花晨月夕”原是没有猫能跑进来的,因为莲心怕猫,自己便嘱咐了福祐让他安排两个小宫人专门看着,不许猫进来。心里惦记着莲心,怕猫扑了门窗乱叫,凌芸不加思索,疾步出门。
尾随朝前院匆匆而去的凌芸,远远瞧着涵韫楼东间有烛光闪烁,一双影子正映在窗上,而此刻的凌芸正紧贴在窗下的琉璃壁上。
伴着那难掩的嬉笑声,渐渐地,她的心跟这夜一样,沉了下去。
“吱嘎”,那是明间的门被推开的声音。良久才看东间的落地纱晃悠悠的被掀开,见凌芸步履蹒跚进来,秋菊从床边的软垫上坐起身,含着酸楚,故作不解地问道:“主子这是去哪了?”说着利索地站起来,正想要上前去扶凌芸,却不想她竟伴着一声怪异的笑直挺挺的向下倒去。
秋菊毫不迟疑地大步扑上去,奋力用自己的身躯接住凌芸,顾不上被泪水迷住了双眼,声嘶力竭地尖叫:“来人啊!宣太医!快来人——冬梅夏荷叫太医!快叫太医啊!太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