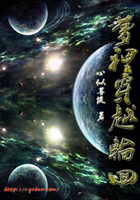在叶冬他们走后不久,老刘就从楼上看到监视的人尾随而去。他为叶冬叫苦,却束手无策。幸亏还有烈山在,这个人办事牢靠,而且还身手了得,把叶冬托付给他,应该会万无一失。老刘一边寻思,一边睥睨若兮。只见这位梁小姐安之若素、气定神闲,对打进来的电话只轻声吩咐一两句便挂断,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如挂帅出征的穆桂英。老刘心里觉得好笑,同时感叹时光过得太快,不觉间,那些春天才刚刚发芽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古木。
中午时分,若兮叫了餐。老刘胃口大开,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而若兮只用了一点粥,吃了两块南瓜饼,遍漱口净面,坐在一旁。
到下午两点,包刕返回,拿来了两套制服。那款式看着蹩脚,面料也很粗糙,若是穿在身上,只有画虎类犬的效果。若兮似乎并不在意,返身回屋换装。等她再出来时,已变了一个人似的。老刘上下打量,就见若兮早把淡妆洗掉,又在头上扎一条马尾辫,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无框眼镜,那样子显得娇弱文雅,像是一位大学在校女生外出实习。老刘不由得暗暗喝彩,看来只要人的底板好,穿什么都好看!
相比较而言,老刘的样子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他这套西装有点小,只好把西装上衣的扣子全部解开,前襟被他的大肚子顶起,像屁帘儿一样忽闪着。这副派头十足是个好色的带班队长,让人没有丝毫怀疑。若兮和老刘相视而笑,包刕鼓掌,又把易拉得领带递到老刘的手中。二人换装完毕,也不乘电梯下楼,顺着楼梯一圈一圈地盘下来,又从酒店的后门闪出,才钻进包刕的车中。
包刕一边开车,一边介绍说:“梁小姐,George带着郑冰在营地负责统筹安排,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您这边的消息。周贾去了牛首山林场那边,已经和对方联系上了,对方的态度很重视,希望得到市里的相关批件。幸亏咱们早有准备,周贾推托说今天是周末,来不及去取,只能等到下周一,再补齐手续,这算是稳住了一方。吴毅现在就在祖堂村,已经和村主任打了招呼,村里好说话,一听说是中央直属的科学院,全开了绿灯,而且热情地款待,现在吴毅他们还在喝酒。我们一会去打个招呼,就算合理合法了。总之,县官不如现管,只要他们不和林场那边通气联络,咱们就应该不会有大麻烦。另外,我们租用了两辆依维柯,一部分人由汪婷带领守在宁丹路许家凹一带待命,只要三点一到,这批人就会从祖堂村直接进入目标区域,建立隔离区。还有,您刚才吩咐要买的东西,我已经置办齐了,都放在后备箱里。购买汽油太显眼,我买了两桶花生油,五升装的。”
若兮满意地点了点头,闭目养神。
老刘嘿嘿地笑着说:“真不会过日子,买大豆油就行,又不是给你们炒菜吃,是放火用的。梁小姐,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这票人马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吧?轻车熟路呀!我提醒您,咱们盗墓就盗墓,千万别再干别的了,你们这属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是被严打的对象。等这件事一了,咱们赶快一拍两散!”
若兮没有搭理他,依旧看着窗外。
包刕回答说:“刘先生,请你不要误会了,我们是外企,不是社团。这也不是盗墓,而是实地考察!”
“哈哈,那我还真说错了,我道歉。可你们这些洋买办更可恨,你们搞国中之国,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大行资本主义之道,腐蚀我们的年轻人,吃人不吐骨头,更当灭之而后快。”
包刕气得无话可说,知道再纠缠下去也是鸡同鸭讲,索性也一言不发。老刘哼着小曲,洋洋自得。
汽车很快就驶进了祖堂村,这里因为靠近旅游区,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民宿、餐馆,是个富裕的村子。包刕电话联系吴毅,果然他们还在喝酒,汽车直接开到饭馆门口。包刕递给老刘一张胸卡,胸卡上写着——“华东二分队队长刘力”,老刘心领神会,夹在西装的领口上。心里暗想,这帮人心思缜密,做起事来轻车熟路,自己还真得对他们另眼相看,而且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别让他们给卖了。
普桑熄了火,停靠在一边。若兮和老刘跳下车,径直走进饭馆。吴毅早迎了出来。这个吴毅年纪不大,顶多四十岁,可是天生的少白头,一大半的头发全白了,花白的头发,配上四方国字脸,浓眉毛,单眼皮,厚厚的嘴唇,一副憨厚的相貌,让人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吴毅拉着老刘走在前面,还未登堂入室,客套话便已出口:“来,来,主任,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队长,华东二分队的老刘!”
话音未落,老刘已经迈步进屋,坐在包厢里,早就喝得面红耳赤的村主任连忙起身,大呼幸会。他的旁边也站起了一排,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估计都是村里的翘楚,定是会计、头面人。
老刘拿出派头,指了指胸口的卡片,说话也文明了许多,在影视圈里,这叫入戏。“敝姓刘,单名力,力量的力。各位请坐。”
在老刘的劝让下,一桌子人才慢慢坐下。若兮眼皮低垂,似乎很不习惯这样的场面,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那里,安静地坐在老刘的身旁。酒桌上的几个人早看到她的容貌,都惊为天人,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不放。
还是村主任比较识大体,并无官场、酒场、牌场中的匪气,一边狠瞪身边众人,一边堆起一脸憨厚的笑容,问:“嗨嗨,这位小同志还没有介绍呢?”
老刘大手一挥,朗声说:“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小梁,可是我们研究所里的所花,刚毕业,算是实习。”
主任马上带笑戏言:“年轻有为啊,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进入这么大的国家科学院,将来也必是大科学家嘛。来,小梁同志,我敬你一杯!”
桌上的人都纷纷咂嘴赞叹小梁的好学问,起哄端起酒杯,笑语相敬。
若兮只得端着杯子轻抿了一下,就放了下来,轻声地说了句,“谢谢!”这一声谢谢如百灵鸟出谷,早把众人酥倒了半边。
老刘过了半晌,才说明来意:“主任,我们来是想和您商量商量,关于幽栖寺遗址的发掘工作。”
主任眼睛盯着若兮,直到吴毅给他敬酒,才把注意力转了过来,“噢——这件事情,我和你们这位吴同志说过,‘国家无小事’,我们一定会尽全力配合,可以动员全村老少齐上阵,比如这个这个挖土方啊,守夜什么的,你们尽管放心。”
老刘连声道谢,又说:“我们这次要发掘的幽栖寺,始建于南朝刘宋大明三年,也就是公元459年,古诗里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指你们这里呀,距今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幽栖寺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中,早期著名的庙宇。所以这个挖掘考古工作很重要,我们希望马上就能开始。可是今天正好是周末,我们有市里的批件,下周一才能送到林场备案,但是我们又不想影响进度,您看有没有什么么变通的手段?”
主任的心思肯定不在这件事上,作为一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肯定在思考别的大事,老刘的小难题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村主任喝了口酒,痛快地提议:“刘队长,你说的这个情况刚才吴同志已经介绍过了。你们毕竟是中央直属部门,发掘考古工作又是利民利国的好事,我们不能太教条主义了。你们喜欢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喜欢怎么挖,就怎么挖。你们怎么干都可以,我为你们保驾护航。我还会在村里给你们征用几所好房子,作为你们临时办公和住宿的地点,以便你们的工作人员能够专心投入工作。这个钱就由我们村委会来出,都是国家的事嘛,请不要这么客气。”
老刘激动地都快哭了出来,早知道如此,还和林场那边打什么招呼。主任看着老刘激动地表情,又补充了几句,才算作罢。
老刘激动地握住主任的手,久久地没有松开。直等到情绪平复下来,才接着说:“既然是这样,我们马上就通知考古队的同事,设立隔离区,开始初步的勘测。我先带着小梁回去,把市里的东西收拾一下,明天中午之前就搬过来。主任,您不会变卦吧!”
主任一听,眉开眼笑,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房子我马上就给你们安排。”说着,微笑环顾众人。
老刘见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若再坐下去,既怕横生事端,又怕若兮更不自在,便起身告辞。大家都要出来送客,老刘执意推辞不肯,最后村主任一声令下,由自己全权代表。可他早已喝得半醉,风摆杨柳一般,任由吴毅架住。
直到把老刘他们送上了普桑,主任还在替二人愤愤不平,“哎呦我的个乖乖,这是什么车呀!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车子,很不舒服的,不如用我的车送你们回去~~~刘队长、小梁,明天见哟!”
老刘婉拒了村主任的好意,摇下车窗、挥手告别,他深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村主任心里的算盘他明白——为官一任,要是能在自己的治下搞出一些成绩,这又何乐不为!果然,直到车子消失在街角,主任还站在那里招手。
玄武湖畔,细柳低垂,菡萏暗熏芳草,湖面尽染香风,江山全在笑颜中。叶冬和烈山徜徉其中,行一步停三停,真如游兴正酣的文人墨客,被景色撩拨地欲罢不能。叶冬早爱南京,却几番失之交臂,两次南下都行色匆匆,今日才算领略到南京之美、玄武湖之美。湖,他见过不少,北京的昆明湖,济南的大明湖,武汉的东湖,杭州的西湖,若是和眼前的这片广阔的水域相比,都显得逊色几分,同样是长堤春柳,此处另有一种风情。
明代的台城傲立在湖畔,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影后,那布满弹痕的墙体似乎还在诉说着这座古城的锥心之痛。不远处有号称南京制高点的紫峰大厦,脱颖于一众湖光山色之中,为这个时代注脚。山峦叠翠的九华山和古朴的鸡鸣寺悄然峭立,那里的樱花早已开败,留一地香消玉损的叹息,延伸到紫气氤氲中的浮屠塔深处。太阳已经开始西斜,玄武湖被披上一件金色霞帔,那静如止水的湖面似乎被扰动春心,刚才还如镜如画,蓦地便波光粼粼起来,更衬托出湖中的仙岛气象不凡,玉树琅玕、仙气缭绕。
叶冬醉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么多挫折,他一定会为之雀跃。可是眼下,他只是走走停停、安步当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鉴别身后的尾随者。
烈山带笑挖苦道:“你这个人好奇怪,放着眼前的景色不欣赏,一路上鹰视狼顾,自己倒显得心怀鬼胎。”
叶冬苦笑不止,拉烈山席地而坐,见左右无人才说:“烈山兄,你别笑我!我的心慌得厉害,早魂不守舍了。只是不知道是因为被人跟踪,还是~~~~~~”
烈山抬手截断他下面的话,又把手一摊,淡淡地笑着说:“请把你的心拿来?我来替你安心!”
叶冬一愣,随即会意一笑,也颇带禅机地答道:“我的人虽然在这里,但是心已经到了祖堂山,我担心甩不开尾巴,更担心今晚的事。我刚才和你说过,尽管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但覆水难收的道理你我都懂。只怕过了这一晚,你我便再不得安宁,很可能要亡命天涯!”
烈山眉头渐锁,正色道:“‘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
叶冬似懂非懂,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烈山的话。
烈山接着说:“这段话是禅宗四祖道信讲给法融禅师的,其含义直指佛之真义。法融禅师自此之后顿悟成圣,开创牛头宗,成为南宗第一祖师。他当年隐修的地方就在南京祖堂山的幽栖寺,也就是我们今夜要去的地方,‘祖堂’之名也由此而来。我想说的是,命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我内心深处的虚妄之念。你若起贪便是贪,你若怀愁便是愁,‘荡荡无碍,方可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其实‘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便知。’叶冬,这些话是我师傅让我转告你的。”
叶冬愕然,茫然道:“我该遵循什么原则去行事呢?”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一日,释尊示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时五方天王互说异色。世尊复藏珠入袖,却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无珠,何处有色?’世尊叹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将世珠示之,便各强说有青、黄、赤、白色;吾将真珠示之,便总不知。’叶冬,世尊所言之摩尼珠,便是你我眼前所生的迷踪乱象,若不勘破,便入虚妄。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不为所动、随波逐流。”
叶冬依旧茫然不解,挠头道:“不为所动、随波逐流?这不是矛盾的吗?”
烈山颌首道:“既矛盾,又不矛盾。你听我讲,那日世尊因乾闼婆王献乐,其时山河大地尽作琴声。迦叶起作舞。王问:‘迦叶岂不是阿罗汉,诸漏已尽,何更有余习?’世尊曰:‘实无余习,莫谤法也。’王又抚琴三遍,迦叶亦三度作舞。王曰:‘迦叶作舞,岂不是!’世尊曰:‘实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语?’世尊曰:‘不妄语。汝抚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叶亦复如是。所以实不曾作舞。’这就是我所谓的‘不为所动、随波逐流’的手段!”
叶冬听罢,疑惑备至,又顾虑重重地问:“若是按照你的方法,你我岂不是要助纣为虐!”
烈山神色凛然,凝视半空良久,才喃喃道:“也许是吧,其中缘故我说不得,也说不清。我可以再给你讲一段故事,以解你心头之惑。藏苯大师充忠珠辣在象雄地区修持密法的时候,曾经路遇三位迷路的猎人,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奄奄待毙。大师对三人说:‘你们不要担心,说不定马上就能找到野牛的尸体,就可以度过饥寒。’大师说罢,便和三人分手。不久,他们就找到了一头刚刚被咬死的野牛的尸体。当此时,充忠珠辣大师也来分食。其中一名猎人发现,在大师的牙齿缝隙间竟有牛毛,随即怀疑刚才咬死野牛的恶狼就是大师变化的。大师早心领神会,吩咐三人说:‘你们把牛肉剔掉,用野牛的皮包上骨头。”三人照办,充忠珠辣大师诵念经咒、以手抚之,那野牛随即重生而起。大师道:‘我若不把它放生,你们会对我产生邪见,并失掉信心。这野牛本来是可以解脱畜生的痛苦,达到菩提道的。’众人愕然。叶冬,我不知道你对这段故事作何感想。但是我觉得,这段故事正是在告诫你我,不要以世俗的成见看待我们要作的事情,一切行为均无善恶分别,均起自内心的虚妄。你要学会看淡,才能好自为之。”
叶冬听罢,寻思良久,既佩服烈山的学识,又感谢他的良苦用心,不由得点头称是,而他的心里却暗暗称奇,隋老为什么让烈山对自己讲这些?难道他早意识到了什么危机?看来,老爷子的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讲明,多半是怕自己年轻冲动,曲解其中含义,这才让烈山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叶冬打定主意,今晚过后,说什么也要再去拜望隋老一次。
烈山望着叶冬,见他的脸色由阴变晴,这才长出一口气。隋老的话他已然带到,但是隋老的用心他却没有猜到半分,叶冬的心结算是解开了,而他的心头却阴云密布。他搞不清楚师傅为什么要急急火火地把他从四川召回来,然后又让他按兵不动。而直到这个叶冬的出现,才又紧锣密鼓起来?这其中的缘故令他大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