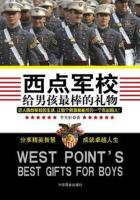吴姐把信送出后,还不到十天,清兵就来把虞夫人抓走了。
整个东厢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几封并没有被刻意珍藏的旧书信,成了凿凿证据。
在吴姐的提醒下,我将玉佩埋到了后花园里。果然,第二天上午,一群清兵就冲了进来,把我抓了过去。
我也没有注意到,抓我们的不是官差,而是从总兵府派出来的清兵。一辆囚车,直接把我拉到了较场北面的军营里。
这里设有一座不为人知的秘密监狱,里面羁押的都是些反清志士。小玉的哥哥应该就在里面吧?吴姐又是怎样把信送进去的呢?她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这些。
大院的门很笨重,上面没有让人识别横匾。进了侧门,绕过影壁,我就看到了竖在甬道两旁的木架。它呈门形,约有两丈宽六尺高,横梁上悬挂的铁链和绳索,在寒风中晃荡。
大堂台阶的下面对称地放着八个站笼。它的两侧,一边是男牢,另一边是女牢。
牢里很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了环境。这间单人牢房,只有六尺见方。新砌的青砖还带着窑灰,空空荡荡的地面上,只有墙角堆着发霉的干稻草。
稻草里面藏着一只破烂的粪桶,裂开木缝中爬着蛆。我靠着牢门坐了下来,望着又高又小的狱窗。窗台上,放着两只用稻草编成小老鼠,使我惊喜不已……
这应该是以前的狱友的作品。她把两只草鼠高高地放到那里,是想还它自由?
她为什么不把它们带出狱呢?也许她根本就没有能活着出狱。我相信这里会有很多手段,能把人活活折磨致死。
“嘭、嘭、嘭、嘭……”
从甬道的里头,传来了一阵用头撞击木门的声音。
“想发骚?还是想要找死?”一声呵斥,两个狱卒握着木棍冲了进去。
“吊起来,吊到老实为止!”我发现自己的狱室里,也高高地横着一根木梁,原来,这是用来吊人的装置。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吊人的花样很多,侧吊,倒吊,正手吊,反手吊,四马攒蹄……整人的方法也林林总总,层出不穷。
“啊……呀……呀……”一声尖叫,久久不去。
听声音,好象是虞夫人的。虞夫人也关在这里?
不知道狱卒对她用了什么手段,使她声嘶力竭,惨叫连连。
“哈哈……哈哈哈……”肆无忌惮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沿着封闭的甬道传了过来,荡起回声。
“是想爷爷了吧?要不要我们给你?啧,啧,连裤子都****了,早点说嘛!”
“求你们……求你们饶了我吧……”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好象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哀求和痛苦。
她是从故友那里听到了三公主的消息?还是从我的身上看出了什么破绽?明天,在公堂上,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对质……
“带犯女朱氏上堂!”
第二天,太阳光从狱窗外面投了进来。刚刚睁开眼,一个粗壮的声音,就在门外拖着嗓门唱了起来。
两个狱卒走过来,手指上摇着一大串紫铜钥匙。
投开锁,踢开门,他们一人抓起我的一条胳膊……我仰面朝天,倒退着被他们拖出了狱室。昨天晚上打上的铁镣,丁丁当归地滑过了甬道和石阶。
他们把我架到大堂,扔到了地上。
“冬、冬、冬……”一时间,所有的刑杖擂着用青石铺成的地面。
我抬起了头,看到一个军爷,高高地坐在木案的后面,满脸的络腮胡子威严无比。
“民女姓肖,而不是姓朱。因为在深夜出生,母亲总是叫我子夜……”
“啪!”我话还没完,军爷将惊堂木一拍,厉声呵叱道:“大胆!不知道王法的东西,给我掌嘴。”
有两个壮汉,从后面走上来,重新抓起我的手,死死地扭到身后。他们揪着我的头发,一使力拉起了我的头。
刚才,一定是我乱看惹的祸。我的分辨,应该无懈可击。
这时,我只敢低垂着眼,静静地等待着……小的时候,我看到过被掌嘴的宫女,一张脸两个腮帮又红又肿,就象一颗被擦破皮的鲜蜜桃。
站在我身前的打手,敞开的衣襟里生着一串又浓又密的胸毛。
他用左手拧了拧我的面颊,等着我将脸挣向左侧……他的右手戴着一只嵌着铜钉的皮掌,突然结结实实落在了我的脸颊上。生硬的铜钉,打得左侧的牙齿一阵乱响。
他的手,轮得并不高。狠狠地打在脸上,不仅目眩耳鸣,而且满口是血。
咸咸的,不敢吐出来,只好往肚子里咽……他一直死死地盯住我的眼睛,从他阴冷的笑容之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怯懦,就象雪片一样落进了我的心头……
“好了!剩下的数目,先给她记在那里。”军爷轻轻地一拍,三个行刑者几乎同时松开了自己的手。
突然失去支撑,我应声倒在了冷冰冰的地面上。
“给我跪起来!”
军爷一声暴吼,使我不得不艰难地挺直了身子。
军爷的威风完全达到了目的,终于把语调降了下来:“犯女姓什么?”
“民女姓肖……”
没等我把话说完,打我脸的汉子就把一副拶子,轻悠悠地扔到了我的面前。
我心里当然知道,他们就是要我承认自己姓朱,承认自己就是大明的怀玉公主。
“好,算你嘴硬,那就再来尝一尝拶指的滋味?听一听灵魂出窍的声音。”
扔在地上的拶子,其实就是五根手指粗的檀木。每根檀木上,钻了三个圆孔,三道皮绳从中间穿过,如果从两边拉紧皮绳,五根檀木就会紧紧地并排着靠在一起……
身后的两条壮汉,抬来一个半人高的圆形木墩,贴着背杵在了我的两腿之间。木墩上面横穿着一根木棒,就象两条平展展张开的手臂。木墩的背面还挂着三条黑油油的皮绳,它们晃动着就象三条又滑又冷的毒蛇。
皮绳收紧我的腰,死死地扣住我的脖子,然后又压住我的胸部,将我的双臂缠在了横木上……
“现在,你是不是还准备姓肖?”
高高在上的军爷得意地说着,津津有味地看着我徒劳无用的挣扎。
一副铁钩伸进了我的鼻孔,勾住我的鼻翼向后发力一拉。
我的头仰着翻过横梁,被压在了木墩的上面。这时,我只有张着嘴才能呼吸,就象一条放在案板上的鱼。
“我再问你一次,你姓朱还是姓肖?”
戴着皮掌的打手拣起拶子,将木棍一根根分开,套在了我左手的四指上。
军爷的问话远远传了过来,皮绳轻轻地收了收,五根檀木紧紧地压着我的手指,痛得钻心。我知道,这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痛苦将会成倍增加……可是,我早已经身不由己。
“收!”军爷一拍惊堂木,两个打手拉紧手中的皮绳,一时痛得我混身乱抖,冷汗和眼泪一起流了下来。
皮绳越绞越紧,使檀木发出了吱吱的怪叫。夹在里面的手指,一点一点地被压成扁形。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冷静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道,时紧时松地将手指搓弄得血肉模糊。
我感到自己的血,一滴滴打在地上,溅起一朵朵红色的花。
终于,两眼一黑……
当我悠悠醒来,已经被老爷接回了自己的府里。我看到小玉跪在床前,流着泪包扎着我的手指,心头一热,竟失声痛哭起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