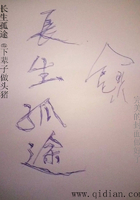打完点滴已是凌晨。
我轻轻抽开沈暮歌握着我手的那只手,他睡得很沉,刚才护士来取吊瓶都没有惊动到他。
下了床,我走出病房。
走廊里安静得很。
头顶的灯光打在地板上,明晃晃的,显得走廊里反而有些清冷。护士站里也只有个小护士趴着在睡觉,这时我才注意到护士站斜对面ICU病房外坐着的人。
他单手扶着额头,肩膀微微颤抖,寂寞的白色侧影有些单薄。
他好像听到了走廊上的声音,轻轻抬起头,看向我的方向,我张着嘴想要说些什么,奈何泪水澎湃,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在梦里,我怎么都看不清他的脸,我着急得直哭第二天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担架车。
白大褂。
记忆总是不会出差错的。
刚才的、曾经的,都与面前这张脸重合。
可我幻想中的重逢本不是这样的。梦中,他站在达尼丁那棵大树下,逆光而站,雪白的肌肤被温暖的阳光衬得越发干净。
这才是我记忆中的少年。
而此时,他只是定眼看着我,没有表情。
像是为了确认一样似的向前移了几步。
这时,他突然慌张地戴上手中的口罩起身,推开ICU病房的门走进去。
走廊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声音了。
所以我问自己:那不是顾念一吧?
。
。
第二天下午,因为沈妖孽睡懒觉我们很晚才去医院。
世事难料,巧遇高峰期。
医院里腾不出床位,人流的窒息感使人心情烦躁。
坐在拥挤的长椅上,我刻意板着脸不搭理沈妖孽。
他费力地举着吊瓶尴尬一笑:“连架子都没有了,那么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充当一下人工的了……”
我白了他一眼,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个钟头后,我听见沈妖孽的声音,于是我睁开眼,看见他将吊瓶递给一个个子矮矮的小护士,然后便急匆匆跑开了。
我眯了眯眼,又继续睡了过去。
中途,我又听见一个好听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带着久别的熟悉感,我努力地想要听清那个声音,末了,才拼凑出只言片语:“我来吧,小心血液倒流!”
连绵不断的睡意席卷而来,于是我又做了一个关于他的梦,梦里的他,还是十六岁的样子,而我则是二十四岁的我,在梦里,二十四岁的我却还追着他不停地喊:“念一哥哥,念一哥哥……”
我好像是缓缓的睁开了眼,面前那张轮廓分明的侧脸的出现仿佛是个错误,因为那只会是一个梦啊。
那张恍若隔了一个世纪的脸转了过来……梦里从来没有这样真实过!
他将吊瓶拿的老高,这时我才发觉这好像并非梦境。
没人能听见心碎的破裂声——除了我。
我仰起头,望着阳光反射过的吊瓶,它只是平静地泛着水光,怎么也激不起任何的波涛汹涌来。
阳光穿透瓶身,有些刺眼。
“怎么了”他问我,看向我的那双眸子全是那种可怕的陌生感。
或许从这一刻起,我的泪珠再也不会断线了,正如八年前——南岛下雪的那天。
望向他明亮的眼时,我的眼角仍挂着泪。我扯着嘴角笑笑,再多的情话都在阳光的恐吓下一步步退却了。
阳光也如此眷顾他,宠溺的温暖了他一身,额前的刘海紧贴,点点碎发嵌进充足的光辉里,就这样,他又再一次固执地变成了我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这时,我用一个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没什么,只是阳光太刺眼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