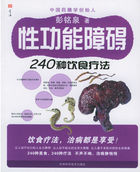“你省省力气,等着迎接马天云吧。”杜缨娘躺在床上翻了个身,自在地。
“哈哈哈!”屋子里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狂笑。
“千手观音就是千手观音!”目卩人又是两声狂笑,“古有常山赵子龙,千军之中取上将人头,今有诗城杜缨娘,千军之中梦周公。这般气度只怕也要成为千古美传卩阿!”
杜缨娘没出声,也没翻身,任他赞美。一声一声的话传来,就如一刀一刀地剜她的心。
“千手观音,不!我的师妹,你该起床了。”
这人竟是岳如飞,怪不得听着声音那么熟。武子峰惊得急火攻心,身子未动,扣在手里的暗器朝着岳如飞说话的方向疾射出去。
岳如飞早有防备,只管声音洪亮地说着他的话。眼看两颗铁藜子疾如流星,直取他的双目,他一抖手中的扇子,扇叶正好挡住飞来的铁藜子。
“武三架杆,你也好好坐着吧,听我把压寨夫人一直想不明白的事跟她说明白了,再比划不迟。”
“好!这话我爱听。”杜缨娘掀开被子,腾地翻身下床,两眼盯着岳如飞,等着他接着往下说。
岳如飞张望四周,突然大声说:“进来吧,听我讲千手观音的故事。”
马天云坐在总架杆的太师椅上,被几个兄弟抬了进来。
朱子刚吊着受伤的手臂,一拐一拐地走到岳如飞身边站定。
“师妹,不……压寨夫人,哦……应该叫千手观音!”岳如飞掌心里摆着三颗手枪子弹,抖抖索索地玩弄着。杜缨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酸溜溜地。
她盯着他,不言语。
“你想不明白又想弄明白的,是两件事吧?”岳如飞左手抓起三颗子弹又倒人右手掌心。“让我猜猜是哪两件事吧,猜对了,你答应我三个条件,了,我个。”
杜缨娘看他究竟如何表演,没有插话搭理他。
岳如飞伸出两根指头捡起一颗子弹:“说第一件事,应该是我们之间的。”
“岳团长慢着!”马天云急忙插话:“这娘们儿狡赖得很,不找个保人作证,岳团长就是猜对了,她也会耍赖不认的。”
“闭上你的烟锅嘴!”岳如飞板起面孔,打断马天云的话说:“我的师妹我清楚,在场的都号称男人,可跟我小师妹比起来,没有一个够爷们。”岳如飞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往下说:“师妹肯定一直在想,我为啥要在鬼子的地窖里扮鬼子,打伤你们……”岳如飞注视着杜缨娘,看她的表情。这事正是她坎上的大事。
“?”
果然是杜缨娘最想知道的事,否则,她不会急着追问。
“是为了国民革命的大事!”岳如飞挺了挺胸,转动眼珠斜视左右,说道:“我今天就向在场的各位宣布,在下岳如飞,生是党国的军人,死是党国的忠良!不是他娘的小日本的走狗!”
岳如飞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着实让在场的人惊讶,挎着伤臂站在一旁的朱子刚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腰上的枪。
岳如飞见状,指间的一颗手枪子弹“嗖”地飞了出去,不倚不偏击中朱子刚正要摸枪的右臂。朱子刚“哎哟!”一声跳将起来。
马天云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暗惊叹岳如飞的弹指功夫。
“我说话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插科打诨!”岳如飞看也没有看朱子刚一眼,加重了语气说:“在场各位可能不清楚,眼前这位名震江湖的千手观音,也就是时三眺总架杆的压寨夫人,就是我曾经的未婚妻,她的亲爹就是我的师叔。”
“我奉上司指令跟鬼子周旋,当上日伪的保安团长,背上汉奸走狗的恶名。我舍弃家业,把苦5经营的万贯家产拱手送给小鬼子;我抛弃爱情,将指腹为婚的情人打伤,赶出阳城;我背弃孝义,将爱我如子的师叔出卖,仙逝在鬼子的大牢里。这一切的一切,足以把我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重生……”
火把闪耀,发出嘛里啪啦的狂啸,岳如飞的眼眶里泛起一轮一轮的波光。“我相信,此刻你们都在心里骂我岳某人是欺师灭视背祖忘宗的小人,骂得好,不骂才不是人!可你们终究只是一介草莽,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不知道革命需要付出代价,要革命就要有杀身成仁的牺牲!”
岳如飞叉开双腿,双臂横在身后,表现出一副正规军军官特有的气质,犀利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
杜缨娘的脸上无风无雨。
马天云的脸上波诡云谲。
朱子刚的脸色在火光中飘摇。
武子峰一言不发,仰起那张不温不火的脸,像是在听一场演讲。
一张张表情迥异的脸,让岳如飞感觉到,接下来的局面有一种不可预见的担心。他又挺了挺胸,精神为之一振,更加慷慨激昂地说道:“为了党国之重任而卧薪尝胆,民族之存亡而舍身成仁,抗日之大计而忍辱负重,即使肝脑涂地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
“岳团长对党国的一片忠心,真是感天动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门外突然响起洪亮的声音。
岳如飞被门外的声音震住了,但很快镇定下来,大声地回应了一句:“在下不敢以英雄自居,忠于党国是在下的本分。阁下是何方英雄,请现身出来,让在下一睹阁下风采!”
“承蒙岳团长看得起!在下本是无名之辈,此来就是拜会岳团长。”一名新四军应声而出,边说话边向岳如飞走去。
“你?”杜缨娘认得,他就是崔松崔连长。
岳如飞仍然没有转身。他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来人不是他最担心出现的人。但可以肯定,此人也非等闲之辈。
崔松身后跟着几名新四军士兵,押着一名五花大绑的新四军进来。
武子峰和马天云都识得此人,他就是新四军的一名排长,崔松手下一名得力干将。但对他如此狼狈的样子,脸上都掠过一丝惊异。
杜缨娘也认出了他,正是昨天缠着自己和穆秀兰的人。要不是他缠着,四方寨的弟兄兴许就不会惨遭杀戮。
她正要发作,崔松冲她投来请求的目光,说:“杜二当家的稍安毋躁,等在下拜会了岳团长,再向你禀明一切!”
崔松说这话的时候,人已走到岳如飞面前。四目相对,彼此紧盯对方不。
崔松先收起咄咄逼人的眼神,转过身来面对众人,说:“岳团长刚才这一番表白真是感人肺腑,但在下认为,你只开了个好头,没收一个好尾,何不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地摆出来,让在场的弟兄真正领会阁下的良苦?”
岳如飞一如先前那样威武,站在崔松的身后岿然不动。他没有理会崔松的质疑,而是心平气和地反问道:“阁下是新四军的什么人?”
“我是新四军什么人对岳团长说明事件真相有影响吗?”崔松转过身来反问。
“我只想提醒阁下,你应该懂得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大局,希望表明身份,否则我会向战区司令长官禀报!”
“岳团长吓唬谁呢?你直接向蒋委员长告我好了!”崔松有一些激动,说话又是咄咄逼人,“你告我不该揭穿你,一边扯着党国的大旗,一边披着鬼子的虎皮,左右逢源,赚足了银元。”
“看阁下的样子,是存心来这里跟国军搞摩擦,破坏抗日的吧?”岳如飞恼怒之色溢于言表。
“岳团长既有国军当爹,又有鬼子作娘,此时的四方寨,里有国军的人,外有鬼子的枪,整得就跟个铁桶似的,我哪敢惹是生非!”崔松边说边围着铁笼的栅栏向杜缨娘靠近。
“一派胡言!”岳如飞终于按捺不住,大吼一声,捏在中指与拇指之间的子弹应声弹了出去。
岳如飞的弹指暗器真是了得,一般人根本看不见他手上有异动。子弹悄无声息地飞向崔松。
啪!岳如飞弹出去的子弹在半路上被一声枪响击落。刘旺财神情自若地收起了枪。
岳如飞身后的士兵“呼啦啦”地操起了枪,齐刷刷地对准了王排长身的。
崔松继续沿着铁栅栏向杜缨娘靠近,他似乎对刚才的险情一无所知,现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岳如飞用如此手段下黑手。但这一切被杜缨娘看得清清楚楚,对王排长身边挥枪击落岳如飞暗器的快枪手十分惊异。
“你也算武林高手,用如此下三烂的手段暗算人,配做岳家后人吗?”杜缨娘终于开口谴责岳如飞的卑劣行径。
崔松展开绷紧的脸,向杜缨娘投去感激的目光。语气骤然急转,平和地说道:“杜二当家最想弄明白的两件事,岳团长只说出了一件,后面一件事就由在下替岳团长代劳吧。”
岳如飞嗤之以鼻,表面上看去若无其事,其实心里已是波澜澎湃。一个新四军的战士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落了他从未失手的弹指暗器,并且用的是快枪。看来,围着铁栅栏转的人更是来者不善。
杜缨娘刚才的话更让岳如飞恼羞成怒,深深地戳伤了他的心,分明是拿他的家私隐秘作要挟。从他的曾祖父开始,江湖中已经没有人追究他们的。
岳如飞迅速转动眼睛看看左右的反应,看样子在场的人对杜缨娘的最后那句话没有上心。赶紧岔开了话说:“废话少说,就听你说说再一件事!”
“第二件事当然与时总架杆遭害有关!”崔松开门见山,一语道中最敏感的话题。在场的人都捏紧了手中的家伙。
“我是要说这件事。”岳如飞坦然应答。
“可岳团长打算如何说呢?敢说时总架杆遇害与你无关吗?”崔松两眼死死地盯着他。
杜缨娘看着岳如飞,她想从他脸上的反应找出破绽。
岳如飞确实很惊讶,忙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时三眺是我暗算的?”
“的确不是岳团长亲手杀害了时总架杆。”崔松边说边弯下腰去在地上搜索,捡了一把石子木块草根拿在手里。众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啥子药,都耐着性子等他说话。
崔松亮出一颗石子,放在地上,说:“这颗石子走漏了时总架杆的行踪,致使他受到追杀。”
他又亮出一块木块,也放在地上,“木板从石子那里得到时总架杆的行踪,马上带人袭击时总架杆并将他打伤,受到杜二当家的顽强反击,迅速撤离。”
崔松取出一根草举起来亮一亮,又取出一颗钉子,一并放在地上,“木块行动的同时将时总架杆的行踪透露给正在组织围追堵截的草,但草对木块的忠诚产生了怀疑,没有妄动。恰在这时冒出了另有所图的钉子,他跟草达成了交易,得知时总架杆的行踪,立即派人前去围堵时总架杆,但晚了一步。草跟着使出一计,派人打人时总架杆身边,伺机从他身上取走草的东西。草的人终于得手。木块知道后很气愤,终于找到机会杀了草的人,抢走草的东西,故意放了时总架杆。”
“大家注意,木块放时总架杆的目的是有其他意图,至于是什么意图,还不得而知。”崔松站起来从身上拔下一颗扣子,准确地丢在钉子旁边,说:“扣子跟钉子早就有一笔交易,于是,扣子带着他的心腹跟在送时总架杆去阳城的路上,伺机杀害了时总架杆。”
众人被他一会石子一会扣子弄得如坠五里云雾。
“到底是谁杀了时三眺?你就直说!”岳如飞忍不住催崔松。
“岳团长不用着急,你本来就是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又是带兵打仗的,不会看不懂沙盘上演兵布阵吧?”崔松仰起头来看了岳如飞一眼,继续摆弄着草跟木块。“木块没想到草的人抢到东西就迅速掉包,把真的送到了草的手上。草也没有想到,他得到的东西也被时总架杆掉了包。草与木块都得知他们抢到的东西是假的,几乎是同时判定,真的已经被时总架杆交给了杜二当家的。于是,草与木块都设法来到四方寨,企图联合钉子从杜二当家的手里抢走真的。”
崔松说到这里站起来,看着地上的石子、木块发呆。
“完了?”马天云忍不住问。
崔松抬头看了一眼马天云,说:“钉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游离于木块、扣子和草之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三方之手除掉杜二当家的。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木块本来与草是一丘之貉,为什么要说服钉子在今晚设计截杀草。而草本来已经对那件东西没有兴趣了,又为什么还要跟木块联手将杜二当家的困在这里。”
崔松看着岳如飞,问:“岳团长能告诉我吗?”
岳如飞迎着崔松的目光,眼里颇为不屑,说:“你先把草啊扣的说明是了,我就诉。”
“好!一言为定。”崔松长舒一口气,提高了声音说:“木块是你岳团长,草就是日军机关长西大条胖中佐。钉子现在如愿以偿,坐上了四方寨新任总架杆的宝座……”
“还有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谁呢?”岳如飞两眼如炬,追问崔松。
崔松脸色沉重起来。弯腰下去从地上捡起扣子,捏在手里沉吟良久,终于还是说了:“我带兵失察,对时总架杆遇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杀害时总架杆的扣子,就是马天云打人我新四军的内奸,今天已给杜二当家的带来了,任凭你怎么处置。”
众人哗然,一起把目光投向五花大绑的王排长。
“二当家的,别听他血口喷人,时总架杆就是新四军暗算的!”马天云激动得想从椅子上跳起来。
杜缨娘愤怒的眼神,从王排长的身上又移到了马天云的脸上。
崔松又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钉子,慢慢地走近铁栅栏里的杜缨娘,欲言又止,把钉子和扣子递给杜缨娘。
“岳团长,在下代你讲的没有错吧?”崔松转过身来问。
岳如飞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屋顶,半晌不出声。
崔松转过身来面对杜缨娘说:“杜二当家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的,岳团长没有异议,你怎么处置我都没有话说了。”
杜缨娘看着手里的钉子和扣子,眼中的泪水如潮水般涌了出来。“三眺,你都听到了吧?你总说对别人要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可人家不这样待你!”
王排长脸上的汗珠如豆滚落,突然摆脱看管他的刘旺财和傅大江,冲向马天云,大叫:“马大当家的,救救我!救一”
杜缨娘突然一扬手,钉子和扣子都飞了出去。
王排长发出一声惨叫,扣子没人他的眉心,砰然倒地。
几乎就在王排长惨叫的同时,那枚钉子也插进了马天云的眉心。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
杜缨娘突然问道。“崔连长,你能告诉我石子是谁吗?”
崔松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告诉我,这个石子是谁?”杜缨娘追问。
崔松心事重重,不知从何说起,看着杜缨娘急切想知道的样子,几次欲言又止。他站在原地,欲左不行,欲右作罢,脚下挪来挪去地耗着,连岳如飞的眼睛也被他的举动牵着,左右晃动。
自打几路人进了这间屋子,还没有静过,现在静得让人担心。崔松突然攥紧了右拳,使劲砸向自己的左掌,说:“杜二当家的听我说,他不是故意走漏时总架杆的行踪,更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现在连肠子都‘随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暗算三眺的意思?难道这人……”杜缨娘死盯着崔松,分明是问:“这人就是你?”
“精彩!大大的精彩!”门外响起喝彩声,夹杂的掌声让在场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不约而同地把眼睛投向那扇大门。
岳如的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