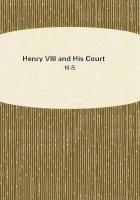仔细一瞧,不和昨日在街上相识。那眉目初醒还有些倦倦的,浅铜色的皮肤也有些红润。一只狼变得温顺的时候,就是现在。
“是你?”左逸霄一声叫住。二月天里,还穿一身较厚的长袍。本以为依旧不会搭理,只见他默默转过身来,向人投来一阵静谧的目光。
他打量了自己一番,尤其注意自己手里的一把剑,只是略有迷离。
左逸霄笑了笑,“昨天走的匆忙,还没请教阁下大名。”
他表情依然平淡,睫毛密密的,一垂眸印下斑斑影影。两耳不闻,嗓音深沉,反道:“昨夜那人,你不觉得死相很奇怪么。”
左逸霄有些惊诧,寻思过后,只是轻轻往前一靠,又笑道:“阁下识微善目,对此事不知有何见教。”
男子英眉一紧,似在揉开眼窝处的朦胧睡意,少顷,一双狼目又凛凛地盯在脸前。“杀人不凭一刀一剑,便是拳掌上更胜一筹;黑夜夺命无阻,必有洞察秋毫之思;至于天罗地网而不得其所,便是有鬼魅之躯、神速之行。三得其一,已是奇人;倘若全有,便是高手。”
左逸霄唇角微扬,不知怎么敞开心怀来,嘤嘤点了点头。
“的确如此。昨夜阁下也有兴致去湖塘吹风?”
“只是在东街巷子看到几个小厮,搬尸到府衙重检。”
左逸霄挑了挑眉,又道:“呵,老兄对这种事情倒是蛮感兴趣的。不过她这些本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尸体脖颈处的伤痕是所击要害。宽约七寸,伤痕黯淡,两目凹陷,明显是血脉缓冲受阻,内脏磨损所迫,这需要很强的内功才能做到;昨晚西街巷也闹事,等过去时,有两名受害者描述了一番。地上有些香粉,宽大一点的很明显是男人的脚印,而另外一些只是浅有接触,不曾留下大的印记,可见此人轻功也是极好。”
“看来昨晚的动静真不小。这等高手,阁下可曾见过?”
男子微微动容道:“一般来说,见过这类人的,要么和那个小厮一样,算痛快一些的。要么,就和你一样。”
左逸霄眼珠一转,玩笑道:“那我真是幸运。”
男子忽然轻笑一声:“我指的是,被这种人盯上,要么马上死,要么以后会死。”
左逸霄沉吟了一会儿,道:“啧啧,老兄,和你讲笑话一点都不有趣。”
“你的兴致还真不错。可是,我没时间跟你讲些废话。”
左逸霄眼中幽光悄然一闪,闲道:“哎,大限将至,难怪以前某人总说我是赶着去投胎的,啧。老兄可有什么好提议?”
“你以为你逃得了吗。”
“不,我是觉得,那种死法也太丑了。”
“......死人还不都一样。”男子轻咳两声,转眼看看一张戏谑的嘴脸,又道,“或许你得再等等。只要不必先急着自我了结就行。”
“老兄,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一回生二回熟,怎么说我跟你有两面之缘,要见阎王这么重要的事情,好歹也得潇洒一些。自杀?这么幼稚又小气的行为,岂非大丈夫做得?那臭女人不是要看扁我了。”
男子弯着嘴角道:“这种高手被派来用在你的身上,还真是......”
“三生有幸——”
“小题大做。”
左逸霄吃窘。男子淡淡抿蠢,依旧不是血红,有些滋玫的杏色。他的眼睛深邃,带点神秘的一张饶有异族风情的脸庞。
“一大早的,听二位聊‘死’的话题还能聊得如此投机,真是难得啊。”二人转身看长廊楼梯走上一人,稍显得有些尴尬。
左逸霄环胸倚在廊柱旁。“花生昨晚苦闷失眠,还能起这么早。”
“唉,习惯了,想改都难了。”裴书言白衣儒帽依然打理的干干净净,反观这二人却是随意太多。“昨日见公子武功了得,非同凡响,小生着实敬佩。不料巧缘公子也在客栈,不甚欣悦。”
男子一见如此文秀君子,不禁端正了容色。“......言重。”
“不知如何称呼公子?”
“在下姓卫,单名一个钰字。”
裴书言笑了笑,道:“汉时有良将卫仲卿礼贤下士,今有小生幸遇侠士卫钰公子,真是相见恨晚。”
“先生说笑了。”卫钰言语淡淡,却脸上晕润。左逸霄了无情趣地看在一边,这臭小子和笨花生倒能谈得一家去。
“先生不敢当。小生裴书言,这位左逸霄公子,与在下是朋友。哦,楼下备好了餐点,若蒙侠士不弃,请一同享用如何,也好相谈。”
裴书言再三相请,卫钰便只得随他下楼去了,左逸霄愣然一站,还有些不知所措。过一会儿,才刚坐下,掌柜竟亲自伺候,完全和昨日不是一个人,偏是对卫钰格外恭敬。擦了干净桌子,摆好碗筷,生怕得罪他姥姥似得。
裴书言道:“看卫侠士行装独异,不知来自何处?师承何门何派?”
卫钰道:“卫某故乡在漠北,家父是铁匠。几年前离家,给来往的南北商队做护押镖客,讨份生计,几日前刚到滁州卸货。”
“果真是塞外的豪士。”裴书言一笑。
左逸霄暗虑。卫钰问及昨夜详情,裴书言遂一五一十的告知与他。
卫钰眉目又凑到一起,道:“二位是庐州人?”
裴书言摇了摇头。左逸霄道:“初来庐州。也有些时日了。”
裴书言道:“依两位之见,那名女子武功之高,来历必定不凡。可是这等邪魔歪道,在武林中的确少见。”
卫钰道:“之前可结识过什么仇家?”
左逸霄猛然想道:“在千金座的时候,与崔焕在地下赌场交手,只是一些小事,惹得不太愉快罢了。”
“崔焕......他这人乖张跋扈,非得是碰到他的逆鳞,否则他不会轻易派出手下追杀。况且,他这几年无非是扩展了些声名,但以他的本事,绝不会有能力支配这么厉害的高手。”卫钰虑道。
左逸霄思来想去,跟老太婆在外头的那个时候,记忆算是模糊了,至于在兰山,能联系到的也就是不久前的那事了。
“左兄,可是想到什么?”裴书言瞧他神情有些不对劲。
卫钰注意到左逸霄容色,也盯在那剑上,缓缓道:“她杀人的惯用手法,可见是被精心调教过的,才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一旦瞄准目标,至死方休。不过,她既然至今留你性命,就不仅是杀人如此简单,而白白迁怒到一个旁人身上。她必定会与你交换条件,得到她想要的东西。而派她来的人,十分清楚你的底细。”
裴书言道:“那她想要什么?左兄可有这样的仇家?”
卫钰转过目光,只见左逸霄回过神来,吃了口包子,忽然笑道:“......她?要是为财,我全身就那两块红宝石值钱了。”
“你觉得这种东西能打动那样的杀手?”卫钰道。
“要是为色,我也就认了。哈......哈哈。”
卫钰默不作声。裴书言忙道:“左兄可不要大意,如果她是冲着你来,昨夜之事又不知何时会发生,性命攸关怎能当儿戏?”
“......说不定是巧了。我啊就偏和些怪人模棱不清,再说,你看她那模样,那武功,都邪门得很,说不定是练什么吸男人阳气之类的,或者杀人取乐,那种事情我也听人讲过。”
卫钰不语。他倒少动碗筷,只勤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吹来尝去。
“我看,今天和褚司狱商量的事情就先放放吧。现在全城秘捕还没动静,你最好不要露面。”裴书言温声道。
“欸,都答应了人,怎能随便推脱。慕昀舒还得去亭边找我,我也不好给她交代啊。”左逸霄怔道,“若是这次能遇到,我也好把事情搞清楚。”
裴书言劝他不住,转而道:“卫兄,裴某是个儒生,不懂武功;还有方才说到慕昀舒,也是姑娘家。小生见卫兄是个可靠之人,但请卫兄能协助他二人同去,也好照应。”
左逸霄肃道:“花生,你不必担心。这事情紧要,我会小心的。”
裴书言示意性的朝卫钰一探。只见他放下汤碗,看了一眼左逸霄。
“卫某称不上豪杰,只不过也是讨刀口生活的草民,要是涉及人命的大事,非百金不能效劳。”卫钰依旧淡漠。言罢,又低头喝着豆浆。
一百两黄金?二人闻言一惊。左逸霄有些气愤,本以为他还是个侠义之士,不想也是个重财的娘贼。一桌气氛顿时变了,来不及左右。
左逸霄随手丢了包子,声音一冷道:“阁下条件高越,我等一众草莽,望尘莫及。想必义士武功着实了得,倒不如等知府公文一到,悬赏杀人凶手的榜文上自有黄金万两,手到擒来,只怕再没比这来得更容易的事了吧!”左逸霄拍了一声响桌,双腿迈过长凳,向门口走去。
卫钰长目一抬,依旧端着汤碗,放在嘴边。
“左兄且慢——”裴书言一声叫住,有些无所适从。左逸霄执剑立在门口,只是不回头来。少顷,静下心神,面色温和道,“卫公子,这事原本就是小生相请,你既有所要求,我定当依从,不由推辞。只是百金之事要暂先一缓,你若帮得左兄,我必双手奉上。小生绝不是无信之人,倘若违背诺言,愿当听从卫兄处落。”
卫钰脸色略显温和,心中已有计较。
左逸霄心中一急,回身拉裴书言到一边,眉心一捆,道:“求他做什么?反正人抓不抓得到,没什么所谓,这种买卖人情我才懒得领!”
裴书言声音急迫,慰道:“左兄,那卫公子既能看出死者内情,显然不是一般人物。你和慕姑娘人力微薄,那妖女又深不可测,你若硬来,白白中了她的圈套,丢了性命。”
左逸霄道:“她要是冲着我来倒好,就不用拖累别人;只是这混蛋不认人命只认得钱财,岂不是比那些杀手还要可恶。”
裴书言劝了几句,左逸霄全然不应,转而看着卫钰一脸无所是非,又郑言道:“我觉得一个人武功如何,并不是靠金银称量出来的,我不是吝啬,也听过仗义疏财;不管你是故摆高态还是出于好意,我不会求你;我左逸霄的性命哪怕一文不值,也不用花钱雇人来当交易!”
四周一片静寂,却连风的声音也做哑。卫钰眼中暗影重叠,盯住左逸霄。左逸霄额前凌丝扫过睫帘,那凤目格外肃厉。半晌,他终是放下碗来,沁了沁鼻囊,嘴角微撇,半漠半笑道:“钱那东西,多多少少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在意的。只是受人之物,忠于之托,你不是我的雇主,我也没让你求我。我只是在履行对裴公子的承诺,得到我应有的报酬而已;这件事倒也可以免谈,不过要听裴公子怎么说。”
裴书言突然一笑,文眉一展,往前一立道:“百金之诺,计日可期。”
左逸霄欲言又止。卫钰淡淡呼了一口气,一把提起倚在桌角的皮鞘重刀,那兵器真不是是一般威严,刀柄宽厚的犹如三掌相叠,刀首锁着一个铁银环,当当地响,教人远远一见都是神色慌乱,绝不像慕昀舒使得细刀,可以说是杀人最上手的,宰牛宰羊怕都是业余的伙计。
他缓缓走到跟前来,桀骜不驯。到裴书言跟前停住,却瞥了左逸霄一眼,扔了一句话来。
“事成之后,必取百金;倘若有负,分文不取。”
遂饶有意味的扬了扬嘴角,走出客栈去了。
左逸霄怔道:“什么意思,谁让他帮忙了!你这呆子,净会给我找麻烦。”
裴书言笑了笑道:“我可是劝不了什么事,倒是你那般说他,他才要非帮你不可了。卫公子也颇有风趣啊。”
左逸霄一声气闷,说不上话来。裴书言应会,叫了住他。
钱项财在门外站了半个多时辰,却也不敢离开。丫鬟嘱咐说娘子正在梳洗,切记不要打扰。但曾听见娘子吩咐,才让说话。屋内,女子换了身缂丝红裳,盈胸半裹,头发依旧束在后勺,耳鬓垂下两缕卷卷的,颈上璎珞换成了白晶玉,选了一条淡粉披帛。
瞧了眼门窗外人影。束进头发去一根金簪,娇声道:“有事速讲。”
钱项财惊声道:“......大娘子,今儿早上司狱司的人来,说褚大人已请示知府,要在城中捉拿要犯,花朝节邀会的人安排在南、东两街门和清风亭附近,并派重兵把守,姑娘只怕得和裴公子另择佳地了。”
“声东击西......呵,真是无趣。”苏合停了住手,并无怒色,轻笑一声,“知道了。等裴公子来了,就与他说,去逍遥津处赏花吧。”
钱项财有些不解,这大娘子凡事顺着心意,怎么今天倒是爽快。
“大娘子,还有,京城传信来说,徐太师已拜帖九华山,派了几个内侍参会,不日即可出发。徐太师还吩咐您不要在庐州停留过久,后天便有人来安排您回京城。”
苏合一虑,扑了些胭脂,又道:“东厂的人怎么说?”
“单公公命小厮送了上好的黄山金毫,并转达太师,届时盛会诸座,东厂必不缺席。”
苏合皓齿一展,朱红的双唇更添几分妖艳。
钱项财传了话,便被吩咐下去。转身见慕昀舒纤细长影立在楼梯一侧,冰眸沉凝,长发被风抛在一边,容姿严丽,不敢逼视。
钱项财鞠了一礼,颤颤巍巍问候一句半道,遂绕行离远了。
慕昀舒看了看窗内一抹长影,略带忿忿地下了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