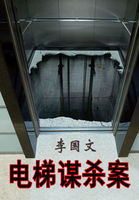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秀英妹,我这次来,是冒了四川兵备道徐典雄的公子,并伪造了他的亲笔信,是投寄给现今山东巡抚的,叫那龟婆看了,不由她不相信。况且有圣旨明文规定,谅她不敢反复。明日一早,我就找她,将你赎出。”
面对突然而至的喜讯,秀英简直不能相,几次她都怀疑自己是否在梦里。但眼前真切的情形,又不容她不信这是真的。四目对视良久,秀英才喃喃地说一句:“那……那苦日子真的到头了?”
方志翔尚未回答,人却蹭地一下后退几步,稳稳当当在桌旁坐下,端起茶盏凑到嘴边做出细斟慢酌的样子。就在此时,有人将门轻轻拍响:“这位公子,恕老身多句嘴,眼看着夜色已深了,铁小姐可还是……您看……”
二人心里都明白,老鸨见秀英终于有留人过夜的意思了,存了心思来大敲一把。秀英顿时满面通红,紧咬了嘴唇,恨恨地低骂一声:“这死不要脸的乌龟婆!”
方志翔却不在意,隔着门扇大声说:“老娘,我是谁你想必也知道了,本公子一见这位铁小姐,便爱不释手,铁小姐也义于本公子,我有心要赎她出去,得多少银两,你合计个价!”
“这……”老鸨没曾想他俩竟厮磨得这般决,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
“老娘,我是官宦人家子弟,这朝中的动向自然再清楚不过,皇上发过旨意,至于如何处置以前建文旧臣家眷的条款,想来你也清楚了?好,最近朝中透出风声,说山东巡抚即将调往北京,家父来补阙的希望最大,将来我可是老主顾哟,你想好了再说,明日一早我来听你回话!”
说着方志翔冲秀英使个眼色,秀英暗暗点点头。然后方志翔高声又说?“好’铁小姐,自古有情人终成眷属,本公子既然诚心,定然不会叫小姐失望。那就先!”
说着嗵嗵迈大步走出,老鸨连忙半搀住讨好地说?“公子,我这老婆子眼老昏花,额头上白顶了两个气泡,连公子这么大的来头都看不出。唉,恕罪,恕罪。公子明日尽管来就是,价钱么,好商量,好商量!”
方志翔也就大模大样地做出不理不睬的神情,胡乱应付几句带一帮人走出门去。
是夜秀英辗转难眠,惊喜交加。忽而想到明日便有望逃离这羞死人的苦海,欢喜得如小鹿在怀中乱撞忽而又想起方志翔说的要刺杀朱棣,不知能否像他说的那样顺利,倘若失败了,他们就会重新落人无底深渊中,那可就没多少出头的希望了。思来想去,忽然又想到方志翔潇洒翩翩,文武兼备,自己和他自小相识相知,多少回[乙仍历历在目,出去后还要和他扮成夫妻,说不定……心里甜丝丝地按捺不住。
终于忍不住,秀英悄悄下床,听听住在隔壁的秀莲屋里静无声息,恐怕早睡着了。这丫头倒美,有姐姐的庇护,虽然一天天地长大,却什么心思也不用费!秀英几分爱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也不点灯,摸索着走到廊外,轻轻拍拍史铁的房门?“大哥,睡下了?”
自从经历过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磨难后,史铁睡觉一向都很警醒,闻声他立刻一骨碌坐起,警觉地问?“秀英,怎么回事?”
秀英看看夜色浓重的四周,笙歌曼舞从前边楼内传出,飘渺若同虚无,黑暗中并没人注意这里,就大了胆子轻声说?“史铁哥,你出来一下,我有话想说。”
半夜敲门,史铁自然知道不是等闲事情,慌忙穿戴了衣服,拉开门,见秀英神情怪异地站在门口,诧异地问?“怎么啦,莫非……”
秀英不及说话,就势闪进史铁屋中,闭了门,喘息片刻,方将方志翔找到这里来的事情说了一遍。史铁听罢也是惊喜不已,但他到底经历多些,尚能稳住神仔细想想?“秀英,能不能刺杀朱棣,到时候再说,眼下这一步是先将你赎出去。只要能走出这个楼,有什么事情再从容商量。记住,凡事到了最后,往往愈容易做坏。千万小心,别跟别人提起,就是对秀莲,也先别说,她还小些。”
得了这些话,秀英底更力踏实,彼此嘱咐几句,匆忙回到房中。更鼓声声传来,如同幽暗海中起伏的涛声,不疾不徐地扰动人心底最深处泥沙尘封的往事。秀英睁大双眼,彻夜难目民。
同样难以人眠的除了秀英和史铁,老鸨也费了很大心思?合计。皇上颁布的诏旨她自然听说过,不过想想冷美人的名声曾招来多少银子,如今她终于懂得了风情,倘若能像其他姑娘一样彻夜接客,那银子不知还有多少。若以诏旨上说的,按原价给卖了,她真委实舍不得。
不过老鸨知道事情的缓急轻重,她想起那富贵公子说的,倘若万一他父亲真的来这里做父母官,自己此刻得罪了他,将来必定有自己小鞋穿的。弄不好,含荀楼就得关门。万不可因小失大呀!老鸨前思后想,终于在黑暗中一咬牙:“吃亏就是福,反正这个丧门星也给赚了不少银子了,索性就送个人情!”
第二天,方志翔果然如约而来,见了老鸨也不问价,挥手一摆,下人立刻奉上一个红托盘,揭开了上面盖的红绸,一封封成色十足的银锭白花花直耀人眼,粗略看看就有千两之多。老鸨本来只打算得个百八十两的本钱,此时眼睛都顾不上眨,满身肥肉抖动着不知该怎么好。
方志翔不屑地一笑:“我还有急事,立刻就得动身,快叫铁小姐下楼,带了她的家人,这就走!”
“那怎么成,那怎么成?”老鸨终于缓过神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慌忙说,“好歹我们母女一场,这说走就走了,还真难受呢!我去找两件像样的衣服,好歹也热闹一下。”
“不必了,车轿者在门外等着呢!”方志翔不管不问,连声催促,秀英也早有准备,自己带了秀莲,史铁扛一包行囊,已经走下楼来。老鸨乐得顺水推船,也就不再多说,拉住秀英的衣袖,还挤出几滴老泪。
一行人迤逦南下,路上倍力小心,不几日就进了熙熙攘攘的金陵南京。事先已经派人联络过,他们直奔师父在成贤街租赁下的寓所。
众人团聚相见,自然喜气洋洋。可是当方志翔着急地问起如何刺杀朱棣的事情时,他那白发苍苍的师父按剑长叹一声说:“唉,可惜我等在山西消息闭塞,错过了他刚开始戕害忠臣,天怒人怨的大好时机。现在他皇位早就坐稳,又采纳了许多怀柔宽恕的仁政。譬如对朱元璋曾杀害的功臣李善长,将他家属免罪,三代人封官。还对百姓恩威并用,人心基本稳固。并且此人生性多疑,更加上有迁都北京的意图,皇宫内外防备空前森严,我几次夜中到皇城和宫城中打探,都寻不到刺杀的机会。唉,报仇的机会恐怕不多了,或许这也是天运所归吧,非人力能抗拒呀!”
方志翔有些沉不住气地大声说:“那,那,杀父之仇就这样平白算了不成?”
“唉,朱棣与我亦不共戴天。”方志翔师父抖动苍白胡须摇头叹口气,“可惜昔比,昔日若刺杀燕贼’那是伸张正义于天下,而如今却是他成正统,我等倒成了逆天行事了。志翔呀,你既文武贯通,当然知道逆天行事,事必不成的道理,勉为其难呀!”
众人闻言个个垂下头,方志翔也自觉无话可驳,焦急着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也不必女此泄气,”师父见气氛沉闷,宽慰着语气说,“天理昭昭,是非恩怨总得有个了结的时候。古往今来,常常暗中算计别人者,其实算计的全是自家儿孙,平空生出事端者,积攒起来全是自身的罪孽。朱棣不惜大动干戈,罪孽已经造成,我听人说他的三个儿子都非良善之辈,以后有好戏瞧。眼下江湖中纷纷传闻建文皇帝并未宾天,他趁乱逃出皇宫,现今隐居在云南一带,我们不妨前去寻他,徐图后举。”
既然师父如此说,想来定有道理,方志翔默默地点了点头。
史铁站在一旁,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他一下子悟出了老者的意图。建文皇帝没死,他趁乱逃离了皇宫,这消息他也听人说起过,但史铁又想,天高地远,就算建文帝真的活着,又哪儿能寻得到?老人不过想借了这个由头,到边远的云南一带,远离了京彡,也远离了朱棣,眼不见心不烦地颐养天年罢了。
这其实正趁了史铁的心思,他再清楚不过,建文也罢,朱棣也罢,说到底还不就那么回事?唉,恩怨正像这头顶漂浮的云烟,扯也扯不断,捉又捉不住,只好听其自然啦。能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平淡地活他几年,也就知足了,经历百般劫难尚留余生的史铁,忽然觉得疲惫不堪。
见众人并无异议,师父绽开满是皱痕的沧桑的脸,打量秀英和方志翔一番,忽然笑道:“志翔呀,难得你把铁小姐救了出来,依老夫看,铁方两家本是世交,你两人自幼便熟识,可谓青梅竹马,又逢落难之际,不如就此结下良缘,日后流落异乡,也好有个贞应。”
这话正中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思,方志翔久经磨难,早已褪却了读书小生的扭捏气,微笑着看秀英一眼,大大方方地说:“恩师之命,安敢不遵?”
秀英却红了脸颊,嗔怒地瞪一眼方志翔,又抿嘴含笑看看史铁。史铁明白,此刻秀英和秀莲姐妹虽称自己大哥,但其实已当做长辈来依赖了。对于这门婚事,史铁前一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既然有人主动提了出来,他自然一块石头落地,长舒口气,在心底念叨一声:“铁夫人,她们姐妹终于有了着落,你也可以放心了。”
就这样,在方志翔师父和史铁的主持下,二人在自小长大,既留恋又痛恨的金陵南京,匆忙定下了一段良缘。新婚之后,他们不敢久留,一同奔赴云南。果然正如史铁所料想的,山川河岳,莽莽苍苍,万物皆如浮萍,哪里去找一个人的影?
无奈之下,众人只好暂时落户当地。幸好所带金银颇丰,足以维持日常开支,生活还算不错。紧接着又有消息自北边传来,朱棣采取了一系列仁政措施’不但在济南修建了铁公祠,以纪念铁铉,还为方孝孺全家平反昭雪,在南京建立祠堂,世代祭,并下旨恩荫方家和铁家的三代。
如此一来,方志翔和秀英对朱棣的仇恨在心底自然缓解不少,报仇的心思也日渐一日地削弱下去。不过他们始终不愿受朱棣的所谓恩荫,甘愿隐名埋姓地生活,专心供养师父。秀莲也在当地找到如意郎君,世代流传,遂成当地望族,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