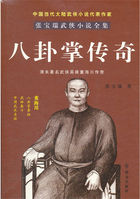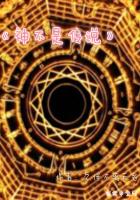一别之后,离开了吵吵闹闹的场面’葛诚突然觉得有些空空荡荡。和前些日子不同,路上没有了串亲访友的人流和车辆,他这辆马车碾在结实冷冻的路面上,隆隆的声音在旷野中回荡,旷野也因此更显得寂静。
或许一直往南走的缘故,天气随着车轮的转动越来越柔和,路面开始有尘土飞扬,周围田野中的麦苗似乎也显得葱茏一些。高高矮矮的房屋星罗棋布,散在田野与田野中间,走近了能听到犬吠鸟叫声,几个老头蹲在墙根眯起眼睛享受着阳光,农家汉子牵着牛慢悠悠走出篱门,肩上扛着各式犁耙,看样子春耕就要开始了。经过两天的奔波,已快到沐阳,而要到京师南京还有几天的路要走,那里恐怕已是莺歌燕舞了吧,秦淮河上的依依杨柳仿佛正在向他招手。天何其大,地何其博啊,他不能不暗暗感叹。
车夫孙老头五十开外,个子不高却很精悍。他已经在燕王府当了近十年的差,比葛诚资格还老。葛诚知道自己这次进京,燕王颇有些不放心,临行时再三叮嘱说,朝中事务错综复杂,皇上年轻少有经事,易于为大臣荧惑,卿但奏当奏之事,其他非所言者当自掂量。这分明是在告诫,那么这个孙老头莫非就是来监视自己的了?因此葛诚尽量少与他答话,要么专注地观看沿路景色,要么缩在车厢中假装打瞌睡。孙老头似乎也知趣,有问方答,从不多嘴。
昏昏欲睡间,突然听到一声马嘶,葛诚睁开眼睛探出头来。“葛大人,前边就是新沂河,咱们该坐船过去了。”孙老头稳住马,等葛诚决定如何坐船。
“咱们有马有车,自然要大一些的。”葛诚说着跳下车向河边走去。
因为是清闲时节,渡口处的人车并不多,倒是船家不少,一字儿开,在泛着冷光的河面上轻轻荡漾。见有客人,立刻围过来几个船主。“客官,要过河?您一位还是几位?有轿还是有马?”
人多话杂,七嘴舌,问得葛诚不知回答谁的才好。孙老头挤过来拽拽葛诚衣袖说:“葛大人,那边有条大船,马车能上去,已经有位骑马的客人在船上了,咱们去了就开船。价钱也不贵,你看……”
葛诚正头疼如何讨价还价,见孙老头已找好了,乐得省事,便跟着他挤开人堆,沿石砌台阶走过去。
船果然不算小,船体上新涂的桐油闪闪发光,高高的桅樯顶端一面小红旗正顺风急速摆动有两个人正铺板子让孙老头的马车上船见葛诚走过来忙施礼笑道:“客官里面请,我们这船你尽管放心,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搞这营生!要不是海禁查得厉害,我们早就出海去啦!这点小河算不了什么,片刻工夫就到对岸,保管你天黑在沐阳城里过夜”
看着手忙脚乱嘴也不闲着的船家,葛诚点头笑笑,踩着搭好的板子走到船上、
正如孙老头所说,船上已有了位客人,中央还拴了匹枣红色高头大马,马背上鞍镫锃亮,泛着铜光,马头上一圈紫色流苏,在风中跳跃不住,看样子马的主人有些来头。
葛诚绕过马,见马的主人正站在船舷旁临风眺望。本以为骑这种装饰考究的马的人应是位王孙公子,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个和自己年岁相仿的中年汉子,穿一身暗红色棉袍,外罩元宝罩褂,戴顶黑纱瓜皮帽,脚穿一双半高不高的黑皮靴,倒背双手正顺河望着出神。
听到脚步响动,中年汉子回头打量一眼葛诚,圆脸上浓浓的字胡向上翘一下算是笑笑,声音却异常洪亮,听得出中气十足:“这位客官也坐船?要到什么地方去?”
葛诚拱手回:“不才从北边来,到南京去办点事。”
中年汉子手拍船帮笑道:“好哇,京师可是个好地方。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乡嘛!你这一去,到长干里转转,去秦淮河逛逛,左手贩奇货,右手拥佳丽,享福不浅哪!”
葛诚听他说的有些意思,却一时琢磨不透,随口应付道:“哪里,哪里,不才只是办趟差事,事毕即回,先生说的福气,恐怕只能想想罢了。”
中年汉子点点头若有所思:“嗯,上命急如火,官差不自由。拿人俸禄,忠人之事,先生做的还算不错。”
葛诚见他话语溪2,心中老大不舒服,听船夫一声吆喝:“开船喽!”便转回舱内坐下,远远地看那人独立船头,衣袂的飘摇将他的思绪打得纷乱,觉得有什么地方似乎不对劲。
河面并不特别宽阔,加之风浪不大,不大工夫船抵对岸,船家和孙老头急忙起身收拾。看着岸板铺好,中年汉子牵过枣红大马,冲葛诚似笑非笑地说:“先生,其实咱们以前见过面的。”
葛诚一惊:“没有吧,我可没印象。”
中年汉子又是浓胡上翘:“当然,先生可能没在意,客悦来店中,我就坐在先生旁边,真是巧了!”
葛诚一脸茫然,不知他要说什么。
中年汉子翻身上马,扬着马鞭说道:“先生,在下送你十六个字,对先生自有益处。那就是,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说罢思动马鞭,一阵蹄声脆响,灰土扬起处绝尘而去。
葛诚呆立半日向,细细品味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很快感觉到,这次回京奏事,远比自己料想的复杂。看到孙老头已把马车驾好在岸上等自己,忽然想起,这回和中年汉子相逢,是偶遇还是人为的安吟看来孙老头这家伙还真是燕王特意派来的,以后得小心点,一边心不在焉地迈步走上车。
一路更加无话。渐往南行,春光渐浓,在和煦的阳光下摇摇晃晃昏昏欲睡中,马车很快驶过淮安,穿过盱眙,踏进高耸巍蛾的南京金川门。
时已黄昏,和风轻漾,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流和两侧似曾相识的各色店铺,葛诚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其实掐指算来,离开京师也不过三四年光景,可就是这三四年中,多少物是人肖科阿。皇上已不是过去的皇上,各级要员也纷纷改头换面。当今的圣上,葛诚倒是见过几面,只是印象已不甚清楚,仔细回想了半天,始终一片模糊,索性不去想他。
看看天色不早,今天是进不了宫了。便冲孙老头说:“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等明天一早面圣。”顿一顿又说,“不妨跑远点,到承恩寺那边,顺便逛逛。”
孙老头应了句:“但凭大人吩咐。”扬鞭吆喝一声,篷车汇人街巷的人流中。
葛诚端坐车中,看着马车渐渐驶近鼓楼。斜阳西下,金色余晖中鼓楼威严地审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和位于西侧的钟楼一起用晨钟暮鼓来宣告每日的开始结束,无形中给金陵城内每个人以天子脚下臣民的自豪感。葛诚知道,就在东北不远处,一望无垠的玄武湖正以它波澜不惊的湛湛碧水宣示着另外一种帝王之威,他甚至能感觉到此刻湖面上泛着的粼粼金光。
马车一径向南驶去。穿过北门桥,行人更加密集,路面似乎狭窄了许多,天色愈暗,有些店中已是灯影晃动。除了行色匆匆的过客外,沿街摆摊的买卖人渐渐多了起来,卖咸水鸭、炊饼等晚餐的,卖成衣、扯花布的,卖雨花石、佛珠等小玩意儿的,叫卖声婉转动听,此起彼伏,有几次马车不得不停下来躲让那些围着摊贩挑挑拣拣的行人。
眼前的情景,耳旁的话音,葛诚既熟悉又陌生,似乎还夹杂着些不可捉摸的感伤,不知不觉中,通过了内桥,往东一转弯,来到承恩寺和大中街交错处。
“葛大人,时候不早了,就在这里找个店歇息了吧?”孙老头拽拽缰绳,让马放缓步子,扭脸问道。
葛诚从遐思中省过神来,抬头正看见大街南侧有座三层客栈,气势还算宏伟,四个通明的大灯笼映照着匾额上的金色大字:“水鱼轩”。
名字倒挺有趣,以前在南京时可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家客店,葛诚抬手一指:“咱今住轩。”
早有伙计领着孙老头到后院去卸马停车,葛诚信步迈进大堂。有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迎上来’拱手笑道:“客官辛苦,快到里边请!”葛诚见他一身丝绸外套’头上还戴顶画满元宝图的瓜皮帽,料想不是一般伙计,便问:“贵店是最近新开的吧?”
“嗯,说是新店也不新了,”汉子笑态可掬,“洪武二十九年开张,有三年了。”
葛诚点点头:“那你这水鱼轩的名号是谁给起的?可有什么典故?”
“都是自己一帮老粗人胡乱起的,”汉子笑道,“哪有什么典故,不过是想着和气生财的道理,我们好比是鱼,客官您呢,就是那水,鱼得靠水养活着才成。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鱼帮水,水帮鱼,我们就给凑合着用上了。”
葛诚听着也笑起来,连声说好,见孙老头拎着行李过来,便由那人引着上了二楼。房间还算洁净,葛诚要了个一进两间的套间,孙老头在西侧隔壁的单间住下。
安顿已毕,葛诚坐下来嗫口热茶,这才感到有些疲惫,晕乎乎的似乎还在车上摇晃。想着明天就要面君,他忽然有些忐忑不安,奏事奏事,所奏何事呢?难道皇上召自己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就是要听那些在公文上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例行公事吗?葛诚明白,自己是先皇钦点派往燕王府中不多的几个朝臣之一,这几年来紧随燕王,对燕王府中的大小事情知道得不少,而目前朝廷和各藩王之间彼此心照不宣,都在暗中较劲。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新皇上才特别要自己?
要果真如此,那可就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了啊!葛诚想得有些心惊,接连几杯热茶下肚,竟出了一层细汗。
那么,要不要把燕王府的情况如实禀报呢?很显然,燕王对自己已有戒备之心了,他的人说不定就住在附近,自己如实禀报,万一走漏了风声怎么办?回到北平会有什么结局等着自己可推说什么都不知道,皇上他会相信吗?他想起在山东见到的那些锦衣卫们,皇上会不会让这些家伙们威逼自己说实话?另外,既然燕王不放心自己,为何又痛痛快快地放自己来南京呢?唉,剪不断,理还乱哪!
孙老头轻步进来问:“葛大人是到下边吃饭呢,还是点好了让人给送上来?”
葛诚沉思着放下茶杯说:“我倒还不觉得饿。你先下去吃吧,我待会儿再。”
见孙老头转身走出门去,葛诚暗想,这也是燕王的一颗眼珠子呀。苦笑一下低下头接着想明天如何奏对。
又有脚步声传来,吱呀一声有人开门。葛诚不耐烦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待会儿再去。”抬头看时,不禁愣住。
进来的不是孙老头,而是两个人,年岁相仿,都是四十有余,衣着也差不多,一律雨过天晴丝绸袍,只是一个颜色深些一个浅些,脚踏浅灰色软底靴,都没戴帽子,细带绾髻,看上去精神十足。二人不同之处只是一个略胖而高大,一个则消瘦矮小一些。
没等他们说话,葛诚立刻认出,胖而高的是当朝兵部尚书齐泰,痩矮一些的是翰林院学士黄子澄。当初葛诚在南京时,就与他们二人有过一些交往。那时候二人是朝中的大才子,一个是应天府乡试第一名,一个是会试中了第一名,读书广博,文章锦绣,深得先皇赏识,特意让他们侍读于皇太孙。葛诚还听说,这二人在皇太孙登极后,很快便加官晋爵,甚得重用。特别是他们力主削藩,极力撺摄建文帝将各地藩王的封地收回,去年周王被抄家就是他们一手策划。
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里呢?他们迫不及待地夜里来访有什么事呢?葛诚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见葛诚发呆,齐泰和黄子澄相视一笑,大踏步走上前,同时在他左右肩上一拍:“怎么?不认识了?当初咱们同游秦淮河,你还吃过我们的咸水鸭子呢!”葛诚慌忙施:“怎敢不认识尚书和学士大人呢只是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里,倒让葛诚吃惊不小。”
齐泰和黄子澄又是对视一笑,齐泰不无得意地说:“葛大人远来之客,风尘{卜仆,为朝廷之事劳顿纟此,我等怎敢不过来拜望呢?”
葛诚连说不敢当,请二人坐下,为他斟上茶说:“葛某区区一个燕府长史,论品级不人流,两位大人皆当朝国柱,能屈尊光临已让葛某受宠若惊,拜望二字如何承受得起,快不要如此说了。来,且饮一杯淡茶。”
齐泰和黄子澄倒不客气,端起杯来一饮而尽。看着葛诚又斟上了,黄子澄浓眉舒展,大眼睛中闪着笑眯眯的神情说:“葛大人,你虽久在北平燕王府中,但说到底还是朝廷命官,和王府家臣自是不同,这次进京,是不是有重归故乡之感哪?”
葛诚听他此说,已猜出几分来意,心说好家伙,正不知明天该如何奏对皇上呢,他们倒先把难题给提出来了。忙一脸正色地说:“那是,久处北地,天寒地冻,满目荒夷,每每站在北平城头眺望南方,但见白草茫茫,思国怀乡的辛酸别提多难受了。此次有幸回京,重见天朝繁华,真是有再生之感。这不,我特意从金川门大老远地跑到这承恩寺,一则明日面君时近些,再则也想故地重游。本想住到乌衣巷去,但天色已晚,没去成。”
齐泰点头若有所思:“难怪昨天圣上说葛诚心地耿直,虽远在边地,爱君之心终必不减,看来的确此,真是可敬。”看齐泰圆圆的脸上疏眉微皱,细目似闭似睁,一本正经的样子,葛诚连忙谦逊两句。
黄子澄手捧茶盏凑近些放低声音说:“葛大人,最近朝中纷纷议论藩王们因为皇太孙登极而他们作为皇子却没能轮上,心怀怨愤,尤其是燕王,仗着自己镇守北平重镇,手下有些兵将,更是磨刀霍霍,欲有不轨之图。可真有此事?”
葛诚心里咯噔一沉,知道难题终于提出来了。脸上却极力镇定,低头沉思着不知如何回答。沉吟片刻索性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讲出来:“齐大人,黄大人,恕葛诚直言,朝廷与藩王之事,我亦有耳闻,刚才两位大人来时,葛诚正思量着明曰圣上问起时如何奏对。葛某虽然在燕王府****差三年,但此事关乎社稷江山,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葛某虽有私下揣度臆测,却不敢轻易妄谈。”
齐泰和黄子澄见他说得真切,连连点头表示理解。一时无话,三人默坐饮茶,彼此心照不宣想着心事。
少顷黄子澄慢慢说:“葛大人刚才所言极是。但如今新皇登极,资望尚浅,藩王们雄镇四方,论辈分,他们是叔辈,论功勋,他们在先帝朝中都多少有功于国,只怕长期以往枝大树易折,尾大害于身哪!倘若一王发难,众王响应,顷刻之间,国家大半土地就会不属于朝廷,皇上政令就会不出京城。你想想,到那时必将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元末战乱之灾就会卷土重来呀!”
齐泰忙附和道:“正是,正是!故此圣上特以奏事为名,下旨要葛大人进京,以便洞察燕王动向,及早做好准备。既然注定要有这一痛,那就迟痛不如早痛,长痛不如短痛!”
话说到这份儿上,葛诚觉得已无处可躲。他只是忽然感到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把知道的情况说出来呢?除了怕说不准而引起朝野变动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往深处一想,他眼前闪过燕王髭须倒竖,横眉怒目的脸,闪过新沂河上遇到的那个中年汉子和他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
想到此他才恍然大悟,从心底里讲,原来还是在为自己的后路担忧啊!葛诚啊葛诚,想当初你和铁铉同在朝中时,那是有名的两根直棍子,忠于职守,宁折不弯,可如今怎么突然懦弱起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