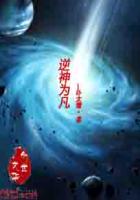四
这一天终于来临。
听说发了榜,白永和与王必高扔掉手中的书,拔腿就跑。四条腿频繁交替,两条辫子舞来摆去,全没了往日的潇洒。他们一口气跑到贡院,门前榜示的地方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两人顾不得斯文,喘着粗气、冒着热汗,毫不客气地拨开人群,一头挤了进去,瞪起两只核桃般大的眼睛,直勾勾地搜寻,恨不得一眼就把最想要的名字钩了出来。
白永和先从榜首看起,数了二十多名,还不见自己的名字,心就有点发虚,腿也软了,不敢挨个往下数,便从榜末往前看,数了约莫二十来名,还不见自己的名字,心中就打起了鼓,不敢往前数。不敢数也得数,硬着头皮往前,往前,再往前看。看一个不是,再看一个还不是,这心就悬得老高,目光游离不定,头脑也有些麻木,他预感到什么,又不愿往那里去想。心想,世上事不到最后,就不能轻言失败,就不能放弃。突然,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赫然入目——白永和!这是谁?他自问道。眼睛由不得定格在这里。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边看边念,当有人拉长声音念到“白永和”时,他这才意识到念的是自己,白永和就是我呀,我就是白永和。立时两行热泪长流,一脸喜色不禁,前后都不看了,两道犀利的目光如射出的两个箭头,死死地钉在“白永和”三个字上,连拔都拔不起来。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亮堂,多么争气的名字!他依次往后数着,数来数去,数不清他是多少名。不知数了多少回,才知道自己是第三十三名,不前不后,居中而列。榜上有名,喜形于色,白永和悬着的心终于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自言自语道:“啊,中了!中了!”黄榜朱字,十分抢眼,他脸红了,眼红了,连天也仿佛耀红了半边。
有人听见,问:“榜上有名?”
白永和几乎是带着哭腔,点头应了一声。
又有人问:“高中几名?”
他抖动着手,好不容易伸出三个指头。众人“啊”了一声。就听有人说道:“这位爷,你是第三名了?”
白永和又举出三个指头。有精明的人会意说你是第三十三名?有好事者一直数到三十三名高声念道:“这么说,您是白永和白老爷了?”
白永和谦逊而又自得地应道:“在下正是白永和。”
周围一片躁动。
人们说什么的也有。听来听去,不外乎是说年纪轻轻的就高中了举人,将来前程不可限量云云。
有的问:“您是哪里人氏?”
白永和回说:“隰州直隶州YH县。”
“什么?YH县?SX还有这么一个县?”人们又是一阵喧哗。
有个知情的人道:“YH县那可是SX省最小的、最偏僻的县,人称沙圪坦。沙圪坦能出位举人,如同深山出俊鸟!”
白永和只顾自己的事,忘了还有王必高王兄。谁知道王必高比他还要糊涂,他是第三十三名,王必高紧挨着他,就是三十四名了。可是,一个因太专注,只看自己的名字,不管别人的事情,滚瓜烂熟的名字变得熟视无睹。一个因为紧张,念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不知不觉,还是旁边有人高声念出“王必高”三个字,这才如从梦里醒来。心中想,意外事,双双现身眼前,二人禁不住击掌相庆,欢呼雀跃。从日头上山看榜一直看了约莫两个时辰,才一蹦一跳相携离去。
这一日,白永和把平生最好听的话都听了,最动情的风光都享受了。他只记得,自己是在不计其数的惊叹的、艳羡的目光的注视下离开贡院的。他只觉得,身后乌黑油亮的长辫子上拖着无尽的风光,他要把这道风光带回永和关,让黄河与他同享小登龙门的愉悦。当然,过了这道坎,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就指日可待。
五
不等白永和回到永和关,永和关已经嚷嚷成一片。
先是报子前来鸣锣报捷,张贴报条。白老太爷、白贾氏携白家大孙子白永平、二孙子白永忍和杨爱丹妯娌几个纷纷走出院门,接应报子,观看喜报。只见报条上写着:
捷报贵府少老爷白永和应本科SX乡试,高中第三十三名举人。
白家请报喜人用过饭,又赏了二百喜钱,打发走了。
刚打发走报喜人,闻讯前来道喜的永和关白姓族人潮水般地涌进九十眼窑院,把白老太爷和白贾氏忙得晕头转向,有点应付不过来。白贾氏吩咐白管家写了大红帖子,上面是“某月某日,因小孙秋闱侥幸,薄具小酌,敬请惠临”等字样,发给关里关外的近邻远亲H县里士绅。等白永和马不停蹄地回到永和关,大门口早有两根木做的旗杆竖在那里,门额上悬着“文魁”匾额,在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映衬下,气派里透着无尽的风光!
白永和一走进九十眼窑院,就被前来祝贺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看众人时,爷爷红光满面,乐得合不上那张没牙虎的老嘴;奶**上插花,身上衣锦,明晃晃的一对金耳环不停地摆动,人们难得一见的紫罗兰手镯也不时露出峥嵘,要多么优雅有多么优雅;大哥白永平一脸憨厚地紧贴着白永和站着,有些唯马首是瞻的样子;二哥白永忍只是淡淡地道了喜,就站在一旁看热闹去了。再看大嫂冯兰花,只顾呆呆地看着,别人高兴她高兴,别人激动她激动;二嫂祁娇娇手挽着爱丹的手,瞄一眼白永和,瞅一眼杨爱丹,丢眉弄眼,摆姿弄势,说不够的亲昵话,直想把人家的金往自家脸上贴。爱丹呢,不用说是心花怒放,百般妩媚,只是人多嘴杂,没她说话和撒娇的机会,时不时给夫婿一个饱含激情的飞眼。白永和看见了,不用说是多么受用。
县学教谕是屡试不第之人,凭资历熬了个附贡,花银钱捐了教谕做。知县老爷也不过是纳捐例贡出身,他们都不是出自正途,对科举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故而对正科出身的白老太爷贤孙不免高看一眼。教谕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不能亲来的知县大老爷,极有分量地说道:“三少爷学精虑远,后生可畏。既能秋闱折桂,金榜题名也为时不远,踏上仕途指日可待。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留着一绺山羊胡、行止颤颤巍巍的远房族叔白静斋,也忙附和说:“学官大人说得极是。我家贤侄,讷于言而敏于行,眉宇间英气逼人,说不准来年文魁的匾额会换成进士及第的匾额呢!”
教谕有些讨好地说:“他日做官为吏,可别忘了在下啊!”
白永和恭谦地说:“岂敢,岂敢,永和还要仰仗学官大人多多提携呢!”
众人点头称是,一片恭维之声。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吉言美语的白贾氏有些撑不住了,亲自拿起酒壶,给席上名士乡绅斟酒,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脸上越发红润起来,话也多了,嗓音格外的瓷实,平日少见的白贾氏的另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白永和想,这就是扬眉吐气了,奶奶的表现比他还要精彩,好像今日酒席宴不是为自己庆功而是为她庆功。自己能够高中,来自奶奶的痴心不改,奶奶的得意,来自自己的争强好胜。白永和有些飘飘然了。
白永和的岳父杨福来也来道喜。他端端地坐着,只是听众人说笑,偶尔也附和一两句,对这位举人女婿既不夸,也不贬,像个没嘴葫芦。看他脸色,快意中有几分失意,明亮中不免疑虑。白永和看见,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岳父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杨福来见女婿风光,心里自然十分得意。得意之余,便是怅惘和失落。“你是荣耀了,岳父我心却提起来了。三娃你一旦做了官,眼里还会有我们杨家,有我们爱丹,原先签过的以子过继的协议还认不认账?”这是此时深藏在杨福来心中的话。
白永和顾不得想、也不可能想到这些琐事,他正在兴头上,正在人生的光彩处。他依次给长者斟了酒,说了些恭谦谢忱的话,众人再次贺喜,气氛就达到了高潮。高潮淹没了杨福来的隐隐担忧,前所未有的喜庆气氛笼罩着新科举人家的各个角落。
入夜,白永和才有机会和爱丹相聚。小别胜新婚,更何况一去半年之久、适逢高中桂榜荣耀回乡的喜悦呢!两人喜上加喜,爱上加爱。白永和一个深吻,把爱丹击得浑身痉挛;爱丹竭力奉迎,又让白永和热血沸腾。一个恣意汪洋,一个瘫软如泥。此时,他们只觉得拆不开你,分不出我,只觉得这世界只有他二人存在,只有他二人在表演。全然不觉夜籁中秋虫此起彼伏的鸣唱,黄河流水哗啦啦的伴奏;不知窗外彩云追月的亲昵,明月衔水的妩媚。当然,更不知云翳蔽月的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