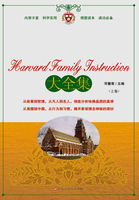推扶着撞车的十几个汉子,顿时合力将撞车往回倒推七八步,推翻在一边,举着旁牌遮护的兵士,早已经迫不及待朝城门涌去。进入门洞,七八名兵士拔出刀剑,与城内山匪战在一处,鲜血的甜腥气息混合这双方喊杀的竭力呼号顿时让战场气氛提到了最高!
一直躲在旁牌后面几十步的梵武,看着城门的僵持,马僵都攥出了汗水。好不容易等到城门被破,他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手中缰绳一松马腹夹紧,如同离弦的箭矢一般破风而去。
在他之后,五十名磨肩擦掌的铁甲,如同决堤洪水奔流向前。
梵武此刻将身子伏低,到城门的五十步转瞬即至,途中一两只箭簇打在他黝黑铁甲上,如同风中飘落的树叶。看着城门战在一起的两方人马,他大呼一声“让开”,就看见自家兵士纷纷两边向门外撤退。
一个箭步越过城门,手中马槊已然举起,梵武将手中马槊狠狠轮出一个半圆,三四名还呆愣着不知进退的山匪,咽喉胸口溅起的血花有一丈高,剩下七八个肝胆俱裂的山匪不是转身仓惶逃走,就是被随后赶到的铁骑踏碎在铁蹄下。
梵武看都没看星散的山匪,让略微有些减速的马匹提起速度,在他前方不到百步的地方,三四百人的山匪零散的聚在一起向他这边遥望。
痛快地大笑一声,云武手中马槊高高斜举,直指苍天,“给我冲散他们!”
五十个汉子齐声应和的雄壮音,五十俱铁甲沉默奔驰的肃杀意,一齐举起的马槊,将他们凛冽杀意全部宣泄而出。
发现城门不保的程一响,在第一时间将麾下弟兄集中在了此处,官军来势太快,攻势太猛,一切都让他这个没有经历大的场面的山贼措手不及。
在鸡公山横行了数十年,被多次官军围追堵截,却每次都能轻巧过关的他,第一次觑见整肃成营伍的铁马金戈之后,唯一的念头就是将手中的兄弟集中起来,拼死冲突出去。程一响已然没有信心,如同每一次那般,将手下兄弟全须全影地带回去,但他绝不能就这样折在这里!
听着如雷马蹄音,如同鼓点一般敲击在他的心脏,程一响“啊”地大喊一声,将心中积聚的恐惧,借着这一次大喊挤出体内。看着距离自己不过七八十步的铁骑,程一响转头怒吼一声,“都他娘的吓傻了吗?给老子放箭射死这些兔崽子!”
三百多人的山匪队伍中,除却前面三四排持刀的山匪之外,后面只要手中有弓箭的山匪纷纷搭弓,一时之间,稀稀疏疏的歪斜木矢箭雨,也犹如初春时节的毛毛细雨一般,纷纷而下。
梵武将左手小臂上绑住的骑盾撑起,熊罴一般粗壮的身体尽数蜷缩,随着战马的起伏上下波动,不过短短几十步,已经有五六只箭矢打在他身上,也只是溅起一阵火花然后无力垂落,而他咬着牙一言不发的刚硬脸上,却露出了带着轻蔑的嗜血冷笑,“如果只是这样的程度,那么一切就该结束了”。
他们这群贴身保护梵烨的亲卫,每人身上皆裹三层甲,内衬一身皮甲,外间再套一层锁子甲,再穿戴上专门保护胸腹肩膀等要害部分,由一块块沉重镔铁拼接而成的重甲,非带铁箭头的强弩七八十步不能穿透。
梵武一念及此却不多思,箭雨已然变得稀疏,抬起头几乎可以看见眼前的敌人脸上惊骇欲绝的清晰神情,不为所动地举起马槊,蓄足了气力的马槊在人群中一砸,一扫,便激起了漫天血花。
后面接踵而至的五十虎狼,循着云武破开的缺口,或如他一般大刀阔斧的地砸扫,杀伤一片,或者伸缩马槊如同吞吐不定的灵蛇,戳刺收割性命。
梵武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砸伤,扫飞了眼前多少的山匪,身处几百人近乎汪洋一般的人群,他不断拨开扎向他战马马腿马腹的刀剑,不断地使大力使得他的膀子都甩酸了。眼前的山匪阵列终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他兴奋地大呼一声,一个猛戳直取一个高大山匪的咽喉,一槊将他挑倒,眼前终于一片开阔。
回头张望,五十名骑军已然将三百余名的山匪队伍,切割地破碎散乱。不成阵型的山匪在血泊中惨叫哀嚎,已经吓破胆的败兵丢下武器四散而逃。
梵武调转马头,大声下令,“前队变后队,进城山匪,一个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