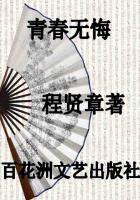进修校课程结束那天班上同学举办了一次联欢节目刘芳要我和她联合表演京剧《红灯记》的片段,她扮演铁梅,我扮演李玉和。我怯阵忙吐托辞,一代人扮演两代人,表演和化妆都费劲儿况且我的嗓音如挣脱绳索的毛驴吼叫,影响听众的心脏健康,打了退堂鼓。于是,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她独唱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为她拉琴伴奏,也算是我们联合表演的节目。
刘芳唱民歌本来极有天赋,等她登上舞台一唱,如潮掌声托起的“再来一个”的呼声在礼堂里回荡。她谢不了幕,只好再唱一支《远飞的大雁》,同学们依旧狂热地捧场。就在这一天,她在同学们的心中留下了‘百灵鸟”的雅号。而我的琴技本来很一般在同学们中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等大家走出校门各奔东西刘芳却叫住我,希望我陪她在县城内的西湖边走一走。
西湖中种植的荷花早过了极盛期粉红花朵凋落得已所剩无几倒是有许多即将成熟的青莲朵在花茎上招摇。习惯打游击战的垂钓者他们与管理人员兜圈子,不时选择一个荷叶稀疏的亮水窝子支起临时武装的简易鱼竿,焦灼等待贪食的鱼儿上钩。他们的鱼竿粗的是顺手牵来的晾衣杆细的是新削的水竹竿,还有刚从树枝上扳下的鲜桠,也有人把鱼线拴在石块上安懒钓。每当有一条不安分的鱼儿蹦出水面炫耀,钓客总要投去艳羡的目光。当某条笨鱼不幸中了算计钓客收竿时鱼儿哗啦啦在水面挣扎的场面,免不了吸引好奇的人群靠拢。在秩序被人们蔑视的年代,人们爱看热闹而不屑于管闲事似乎成了人人默认的游戏规则。
刘芳站在柳荫间问我:
“你工作的地点定了吧?”
因为县里的培训时间太紧凑文教局和望江区文教办公室要我先参加培训然后再补办报到手续,起薪时间则从我到县文教局报到那一天起算得上是特殊照顾。不过由于发配边远地区的结局巳定,充其量是补偿性的关照。这事我一直闷在心里现在刘芳一问,我只好无奈作答:
“大体上是到望江,究竟落脚哪里还不清楚。我想,大概是一层层地往下落吧。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有宽松工作给我,服从领导,顺从命运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何况我顶替妈妈的工作是出于不输一口胃气的冲动之举。”
“你在和谁斗气呢?”
“也许是和自己吧,鲁迅说过,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命定属于我的道路不管多难不管多出乎人的意料,都得自己去走,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呀。”
“你可以主动提出到望江小学,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我不准备提任何要求,顺其自然。说实话,我只有难以启齿的初中学历,本来该自己坐在课堂学习,这倒好,自己肚皮里都没有几滴墨水偏偏要去教书了。我觉得,即使到村小教小学一年级都是高抬我了。”
刘芳手指着闲靠在湖畔的一条小船说:
“你看,那儿有条船我们去划划,有人叫再划回来又不是偷船,好不好?”
我一点头随着刘芳溜下湖边的石坎解开缆绳,跳进了小船摇起桨来。同一条船我望着倒束着两条辫子的刘芳其实她长相还是相当出众双颊白里透红一对眼珠乌亮,给人留下健康的美感。最为难得的是自己和她在一起毫无心理压力,也真称得上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可是我的心里总是挂记着虚无缥渺的将来,不愿意让生活过早地定型那样’许多残梦,许多来不及追逐的将来都会伴找结。因此我对过早建立一个所谓的幸福家庭,甚至产生了几分杯弓蛇影的恐惧念头。兴许我是不懂生活、不解风情的那类乏味的男子,一双脚天天渴望迈上并不熟知乃至根本不存在的远方。这会儿,我与她相距近在咫尺,倒觉得不如远隔天涯才好。
“你在想什么?告诉我!”刘芳问我。
“什么都不想没有过去没有将来“那么只有现在只有我们?”刘芳再问。
“不,只有蓝天上的那一朵浮云’它太像我的命运’没有稳定,没有安宁,谁知在什么时候会刮来一阵狂风,把我和我的梦想吹得无踪无影。”我的话似呢喃,似自白。
“你太悲观了,其实在这样的时代只要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人都会有前途。我问你,我什么时候不是把你看成自己人,不是视你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好青年,而是对你另眼相看?”
“你没有’我真的很纤你真怕因为被你高看最终让你更加失望。”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你纤也不应该仅仅停留于面……”刘芳的脸颊绯红像映日荷花。
“我的能力太小,我所有向往的目标几乎无一实现对所有关心过、帮助过我的人我现在都欠着一大笔恩情我也渴望自己能够报答那时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说话认真,不带丝毫游戏成分。
“你个人的目标还没实现,就拒绝一切女性,拒绝伴随年龄增长出现的正常情感吗?”刘芳的眼里有埋怨有挑战。
“付出情感,应该与责任挂钩同样,接受情感需要自己有担当。不然那就是可耻的亵渎而世间上圣洁的情感是不容忍亵渎的。当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妄语情感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轻率那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种自爱。其实人生的长途需要一次次的面临量力而行的放弃,否则背不起太重的行囊。那样不单使自己很狼狈还拖累别人。”
刘芳闻言,眼圈红了她掉过头用手绢擦擦,过了一会儿平静地朝我说:
“我们上岸吧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赶路。”
上了岸刘芳拒绝我相送,转过身子匆匆离去。
我望着她的背影消失’是对是错,一时不能判断。不过,我知道自己不光失去了一个恋人,也可能失去了一个友人。人站在太阳的光芒里,胸间冒出一股无可名状的忧伤觉得堵心堵喉的难受。但是,我明白,当人生的拐点突然来临并且没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必须向对方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保留歧义无异于在歧路口了无休止地逗留误人误己误时误路。我决不能向她追过去一句不计后果的表白将为彼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埋下一个危险的伏笔。
我在家休息了两天便赶到望江区去报到只因新学期很决要到来了不敢延误时辰。区文教办公室余主任告诉我到望江区报到不一定就能留望江镇全区六个公社到处都差人如果我非要留望江不可他也可以考虑,因为我是下乡在望江公社的知青,能从母亲退休的城郊区改派望江区已经算有觉悟了。我当即回答服从安排。这样,他便告诉我平澜公社小学最近有个教师减员,教五年级的课程,派我去顶岗正好应急。我没有再啰唆说推口话,他便拉开抽屉拿出介绍信填上了我的姓名。我的工作地点便完成了由县到区再到公社的转变,这在公办学校里已经深人到了最基层人的脚步踏踏实实接了地气,算占得一个无人争抢的稳稳当当的位置。
等我回到插队下乡的雀山一队取自己的少得可怜的居家用品时,高队长用手挠着新剃的光头,嬉皮笑脸地说:
“我还说你小子,屁股一拍不再打回趟了呢!虽说不是老子推荐你走的人你到底是一件喜事呗未必不喝两杯烧酒就溜趟趟儿?至少算得上我没坑害过你嘛,再说你一走老子还有些舍不得话个别,该不该?”
“高队长你别把话说疏远了。在队里喝酒,在场镇喝酒,随便你定。要请哪些人头,也由你说了算。给你交个底,你不馋我这一顿,我也会请你相处四五年了,到底还是有情分的。”
高队长一拍大腿,痛快说:
“老子也告诉你其实我早已有安排,我们队上请你我家那只叫鸡六七斤重,冲着你,我要在它颈子上抹一刀。猪肉由队上去割你只要提着烧酒来和我这大老粗一醉方休,没亏你吧?”
我装出犯疑惑的样子说:
“是不是你又下了一个套套儿哄我去钻进?我是吃过你的亏的人,不放心啊。”
“你把心放回你肚子里去吧老子不算你,算去算来,算老子自己?现在,队里一个知青都没有,老子还搞不惯了。怪不,你在我还嫌你呢!”高队长一咧嘴,憨厚一笑。
第二天中午,我拎着盛满五斤烧酒的塑料壶,走进高队长家等待队上的客人陆续来到。大家刚端起酒杯准备敬酒,魏胖娃带着十余个知青出现在门前叫嚷着:
‘涨良,你咋个招呼都不打把兄弟们都忘了我们却没忘记你哟。你在这儿伸筷子拈闪闪我们转了几匹山找不到你的影子,还打主意稳坐起嗦?”
我忙立起身子迎上去低声对魏胖娃说:
“魏兄今天我有事生产队出了一片心,贫下中农请我吃顿饭,你都要来搅黄?你们走吧,我有空来找你们耍。”
魏胖娃脸上有些急:
“不行不行今天八月初六是大喜大庆的日子。公社胳书记娶儿媳妇,摆几十桌’你还不快把你那套毛选拿出来,带我们去走人户。”我一听更觉得要赶快送他们走,解释道:
“我那套《毛泽东选集》是区里发的奖品,扉页上写了我的名字,还盖了区里的公章送人不好。再说现在去,等人走到人家的筵席都散了。”
“不行不行,你要去。不然你真不记情人家骆书记去年推荐工农兵学员,是千方百计关照过你的哟,你不要记性好,忘性大。”魏胖娃说话不分场合’声音越来越高。
魏胖娃身后的一群知青也七嘴舌为他帮腔:
“张哥,你要去,不要寒了大家的心。”
“你不要现在有酒有肉,就不给兄弟伙的面子了?”
“走,张哥,这道门槛绊不到你的脚你快高抬贵步!”
我正犯难高队长从里屋抱出一套《毛泽东选集》来堆笑递给魏胖娃顾:
“你们几个知青要去赶礼’我这里有套毛选’还是我哥娶儿媳妇时,他队里的知青送的,你要就拿去,不要客气。”
魏胖娃接过四卷雄文’抱在胸前,脸面乐呵呵地说:
“你老哥够意思,理解我们革命知青。你干脆好事做到底,让张良跟我们走吧,他是饿老鸹,嘴大肚皮空,一个人要吃掉半桌席。他走了,你们多挟几筷子,更合算。”
高队长急于送走这些不好招惹的主向我使个眼色对魏胖娃说:‘好啊,我本想安排个人给张良送行李你们和他走顺路捎去还更省事,你说呢?”
赚娃高兴得把手上的《毛泽东选集滕身边的4知青抱着,掏出一支经济烟给高队长旋即划根火柴为他点上说道:
“帮张哥送行李不要说你老哥打了招呼我们自愿都要帮忙好说,好说。”
我忙叫魏胖娃一群人等着,转过身来举杯向桌上的队干部说道:“我张良到雀山四五年时间,受到在座诸位的教导和抬举,一生一世不敢忘怀,不敢负恩。有朝一日如果有机会,一定效犬马之劳,希望大家不要客气。我今天朋友突然赶来不能陪酒到底,实在抱歉。我这里自罚三杯,权当给大家的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