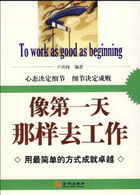流浪者本来是钟小北的酒吧,名字是我起的。
我说,每个人都在流浪,有的人发现得早,有的人发现的晚。
钟小北一双桃花眼忽闪忽闪含情带水,捏我的脸:“矫情。”
他手指骨节柔缓,修长白皙,冰冰凉,险些让我害上恋手癖。
酒吧现任老板任七是个特招人的小伙子。
哈尔滨夏日苦热,他常松松垮垮系一条低腰迷彩裤,露出漂亮的人鱼线和规规整整六块腹肌,两臂扛着一条过肩龙的纹身,下巴上胡茬发青,眼睛倒仿佛懒得睁,睫毛长长的垂着。每当两手慵懒地插在裤子口袋里,红绿交错音乐嘈杂的人群中呼喝穿行,身后往往跟着两个小弟,身影所至,浓妆艳抹各类姑娘为之侧目。
南岗酒吧本就不多,像样的一只手就数的过,我最喜欢流浪者。
任七问我为什么,我就笑着问他:“你说呢?”我穿着条黑色吊带连衣裙,头发刚做过离子,垂在胸前,一丝不乱,“猜到我就告诉你。”
这会儿清晨六点多钟,人散得差不多,颇有点杯盘狼藉的样子。红的、绿的、蓝的,各色的灯光闪得晃眼,我眯了眼睛,歪着头瞧任七的表情。
他手里是一杯蓝色的鸡尾酒,微微沾了嘴唇,笑:“知道我还问你?”
我一手捏过他的杯子,晃了晃,抿了一口,也笑:“为了你呗。”又凑近他耳边,“就喜欢看你的样子。”
任七触电似的往后退,被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腰带,瞪大了一双细长的眼:“白月,这可开不得玩笑。”
“谁和你开玩笑?”我心里暗笑,声音嗲得自己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七哥,我可在你这耗了一宿了,酒也喝了一缸,你怎么补偿我?”
任七紧张四顾:“你……你先松手。”
强子和小松正扯着脖子往这边瞧,任七一回头,吓成两只缩头龟。
“你怕什么?”我冷笑,“不松。”
“松手!”任七眉头已经皱起来。
“你这酒不错。”我一口尽了杯中酒,回头喊,“强子,续杯!”
强子两步窜过来把酒满上,目不斜视,又窜到别处去。
“你到底想怎么样?”
“训练有素啊,”我瞄一眼强子的背影,哈哈笑起来,又放柔了声音道,“七哥想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呗,都听你的。”
“白月,你知道,训练有素也是小北训的。你再这样,朋友而没得做了。”
“道貌岸然。”手指沿着腹肌向上滑,停在青色的胡茬上,眨眼睛,“没关系,做不了朋友做情人,做不得情人做****呗。”
“白月,我对你不薄啊。”他蹙眉,眯着眼,“你不能这么害我。”
“任七,你对我不薄,我对你薄吗?”我用尽所有温柔盯着他的眼睛,可惜险些笑场,所以只好低下头靠在他肩膀上,“你觉得我待你不好,想要什么补偿呢?”
皮肤的接触一瞬而逝,任七不知退了几步,慌里慌张的样子实在让我忍无可忍,捂着嘴大笑起来。他看妖怪似的看着我,大半天,回头扯过正往吧台取酒的强子:“拿件外套给他!”一溜烟地跑了。
“姐……”强子一脸苦笑:“你这是咋了?北哥怎么不陪你?”
我忽然心里酸酸的,摆摆手,“没事儿,我走了。”
转出了门,天已经放亮,却有些阴沉。强子追出来,拿了件外套给我,我一眼就认出那是钟小北的。早上的风有点凉,我忍不住发抖。
“谢了。你怎么不拿任七的外套给我?”
“啊……?”强子的嘴张了又张,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真像只吐泡泡的鱼。
我穿上外套,说:“你告诉任七,我今晚上还来。”
我回到寝室时,房里空无一人。周汀甲在床上留了字条:“回家,勿念。”
我大二,修美术,周汀甲是我室友。这姑娘哈市人,相貌奇特,与王宝强神似,深得我爱。她是学中文的,却基本上不通文墨,写个入党申请书都要咬手指甲,平时喜欢唱歌跳舞和自拍,有时间就跑去当群众演员,可爱得不要不要的。
我洗了个澡,一头栽倒在床上,却满脑子都是钟小北,怎么也睡不着。直到九点多钟,空气又热起来,我心里燥热难耐,也顾不得风湿病,把空调开到最大,昏天暗地地睡到了下午三点。中间只觉得空调吹得肩膀疼,又昏昏沉沉醒不来。
醒来时,钟小北躺在我身边。一双桃花眼黑幽幽的,眉头皱得好难看。
这厮怎么跑床上来了?我吓了一跳,张嘴正想骂人,心里却蓦然软了下去,不由得去抚他的额头:“和尚,你皱什么眉嘛。”
他抓住我的手,放在手心里揉啊揉,眉头慢慢舒展开:“我看到你就头疼,离得这么近,就疼得受不了了。”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一把抽出手,翻身起来:“你妹!我让你来的?”
“你还敢问我?”他突然脸色一变,按住我肩膀,又压了下去,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你和任七,什么意思?”
我的心跳起来。周汀甲说,薄唇的人薄情。听起来真不错。钟小北就是个花和尚,长着双四处留情的桃花眼,生着副人神共诛的薄情唇!
“怎么了?就是那个意思呗,和你有什么关系?”
“和我没关系?”他眼睛眯得好危险,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的心快跳出来了。
“本来就没关系。”我别扭着,推他的肩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和我没关系,和谁有关系?和赵云峰有关系?”
“嘿,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钟小北黑着一张脸,一米八几的个子胡乱压在我身上,我两只手被他一起制住,一动也不能动。这人生气的样子也那么好看,简直让古天乐那一版的杨过附了体,剑眉星目,嘴角坚毅,额头的青筋好性感!我感觉自己真的没救了。
“你笑什么?”他脸更黑了。
“我没笑。”丫的,真失态。你问我笑什么,难道我告诉你这是美色所惑的淫笑?你的情商呢?
“不许笑。”
“哈-哈-哈!我偏笑!”
钟小北低下头狠狠地盯着我,然后坐起身来,穿了鞋摔门走了。临走前,扔下一句话:“白月,你适可而止。”
摔门的声音震耳朵。
“丫的,摔碎了门你要赔的!”
我抱着膝盖沮丧地坐在床上,过午的阳光透过窗子,充斥着整个房间。忽有一阵风起,窗前的毛巾、袜子、风铃都晃动起来,物影幢幢,我这才意识到,钟小北关了空调,开了窗子。我只觉得满地的阳光都被打碎,心里怏怏地难过。
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废了那么大功夫,去任七那折腾了一个晚上,他才过来看我,怎么几句话又把人家气走了?现在怎么办,今晚还去流浪者厮混?
我正和自己怄气,电话响起来,是胜男。我傻傻地看着手机屏幕,发起呆来。这电话怎么接?没法接。
太阳好大,我看着地板上自己黑乎乎的影子,只觉得头疼。
这时候门又开了,我条件反射地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钟小北抱着胳膊挑着眉:“赵云峰?”
“不是。”我低下头,然后就听见一声冷笑。钟小北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我心里乱糟糟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来不及穿鞋便追出去。
“和尚!”
钟小北转过身,立在那。走廊里灯光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脸。我希望他说一句话,但他什么也不说。
“和尚,地板好凉……”我心里委屈,语气软得吓了自己一跳。
他走过来,仍沉着脸,把我抱进寝室:“你还追出来干什么?”
我坐到床上,也拉着他坐下:“我怕你不回来了。”眼泪不自控地落下来,有一滴落在他的手背上。我接着说:“你可以不回来,但是不是现在,不是因为赵云峰。什么时候,你真的想走了,你可以带着内疚走,我绝不拦着你。”
钟小北抬起我的下巴,黑幽幽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那么长的睫毛,那么高的鼻子,真让我心跳。他说:“白月,你什么意思?”
“和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现在不能离开我。你现在离开我,会开心吗?”
他的手向上,落在我的脸上,擦去眼泪,然后用我听到过的最温柔的声音对我说:“白月,不管是什么时候离开你,我都不会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