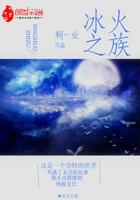优箩没有接画,也没有说话,甚至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只是端着茶盅的手不着痕迹的颤了一下,随即又平复了平静。
徐继仁双手托着画,收也不是,递也不是,时间一长手臂开始酸胀,继而慢慢颤动起来,接着浑身也开始颤抖,扑通跪在地上,“公主恕罪!”
“恕罪?你何罪之有啊,本公主怎么不知道呢?”优箩嘲讽的看着他,突然目光一冷,直直的望进他的眼中,一字一句的道:“小寿子,你可知你也有今日?”
“不,公主,老奴冤枉。”徐继仁抬起头,原本刻意压低的嗓音也恢复了原本的尖锐,“奴才对不起菀妃娘娘,对不起皇上,可是,奴才对得起公主你,虽然,奴才这样做很卑鄙,可是,至少保全了公主的性命。”
“保全了我的性命?”
“是!”徐继仁端起茶盅喝了两口热茶,又把身子往小红泥炉移了移,“奴才奴才姓徐名寿,字继仁,未进宫前是菀妃娘娘的表兄!”
“你说什么?”手中的茶盏掉到地上,跌得粉碎,“你是菀妃的表兄?”
“是,三十五年前,家乡遭了灾我跟随母亲逃难到了京城,本想投靠外公,谁知外公嫌弃母亲不停劝告硬嫁了个无用的农夫,不肯认我们。我和母亲流落街头靠着乞讨度日,有一天,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跑去一家大户人家门口讨吃的,结果被人打得昏死过去。母亲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本想一头撞死,恰好那家的夫人从外面回府,两人一碰面,那夫人竟然是母亲的堂妹。姨母派人将母亲扶进屋,又请来大夫治好我的伤,从此,我们便在府里住了下来。姨夫姓严,是个不苟言笑的大官,姨母只是他的二夫人,因为姨母性格温软,从来都面含微笑,姨夫对她也甚为喜爱。自从我们在严府住下以后,大夫人就对我们看不顺眼,有事没事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我与母亲寄人篱下日子过得甚为辛苦。好在没过多久姨母生下了表妹,姨夫高兴之余为表妹取名玉菀,小名儿东哥儿。东哥儿小时候很调皮,常常骑在我脖子上要我驮她,姨母见了就骂她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而姨夫则是笑呵呵的摸摸她的头,叫她‘我的小宝贝儿’。”徐继仁想起少年时那纯真的梦,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那时,他还只是个七八岁的少年,对表妹打心眼儿里疼惜。
“说来也怪,自从东哥儿出生后,大娘就莫名其妙的开始生病,而且一日比一日严重,终于,有一天她死在了寝室的床上。而姨母自从生下东哥儿后身子就大不如前,她常常躺在床上听着我与东哥儿背诗文,母亲衣不解带的在她身边照理,然而姨母还是日渐消瘦,那时,姨夫已经又娶了三夫人回来,对东哥儿也没以前疼爱了。只有大夫人生的奇少爷时常给东哥儿带些新鲜玩意儿。东哥儿一天天长大,我们的感情也日渐加深,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她表白了我的感情,她羞红了脸跺跺脚跑开了。母亲察觉到我的心思,悄悄探了姨母的口风,姨母也乐意我与东哥儿在一起,我暗自高兴,因为,东哥儿会成为我的妻子。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东哥儿十五岁那年,姨夫突然提出要送东哥儿进宫为妃,而且说圣旨都已经下了。突然来的噩耗惊得我不知所措,我一头冲进雨中,胡乱的跑出严府大门,漫无目的的不知道跑了多久,最后力竭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已经过去了三天,救我的人家找了辆马车把我送回严府,东哥儿已经被鸾轿接走了。我大病一场,而姨母因承受不住母女分离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了世。姨母死后,母亲**哀伤哭泣,没多久也随着姨母去了。我一个人在诺大的严府里日夜思念东哥儿,终于有一天我跪在姨夫面前求他送我入宫,姨夫答应了,我被送进皇宫做了太监,从此,再没有离开过皇宫一步。”
徐继仁抬头茫然的看了看无边的宫墙,也许过去太久,久到他已经忘却了年少时编织的美梦,当年的一时冲动到现在只剩下空洞和迷茫。从进宫那日开始,他就知道从今以后,自己的生死就握在了别人手里。
而那个人,就是抢了东哥儿的男人,他得到了她的心,她的身,却没有善待她。
他好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