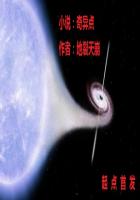第二,雍正改制,也一举消除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与相权、将权之间权限划分不清,经常发生矛盾的问题。历代皇帝设置丞相,但又担心相权过隆,担心皇权受到侵犯,因而对在位丞相罢黜甚至杀害的已不少见;但亦有像曹操这样的权相,威震胁迫皇帝的事。国家政务繁杂不设相以辅助,不可能;设置丞相,又怕太阿之柄,而成尾大不掉,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长期存在的大难题。雍正经过长期思考设置了军机处这样的机构,以之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每日有效率地承上启下处理大量军政重务,但它仅是作为承宣皇帝谕旨,为皇帝的工作做准备和辅助,规定不设官署,不发关防,不置机构和属官(军机章京仅为助手的助手),还不许以军机处名义对外发布任何指示性的文件,仅能在每日由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对内外军政重务作出批示之后,军机大臣才能根据皇帝的意见,拟出名为“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名式的下达文件。可见,军机处仅为一个特设的皇帝御前机要秘书处。用军机处和内阁组成双轨议政,内阁负责处理一般性的大量的政务;而军机处则紧密协助皇帝办理军机重务,有分工,有配合,而皇帝紧紧掌握着绝对的统治权力。这一巧妙设计,一举解决了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将权的复杂矛盾,是封建社会晚期一大成功的改革。
除了上述两大改革措施之外,雍正的政绩还是很多的,而且大多卓有成效。诸如,他为解决官员政风问题,一方面严惩贪污,另一方面,则采取厚俸养廉,规定各级官吏合法的收入范围。他亲自掌握与各级重要官员的沟通,健全“密折奏事”,并由皇帝本人“朱批”口谕示制度。他在位13年,现存他与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市政使、按察使、甚至道员、知府之间的来往奏报和批示近万件。他定期亲自召见军政重要官员,也召见委任或即将赴任的中级官员,甚至在召见单上密密麻麻地写出对有关人员的印象和使用意见。他大力改革赋役制度,推行摊丁入亩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无地少地贫难下户减少负担。他严查亏空,充实国库。在社会上,解放丐户、蛋家、世仆等所谓“贱民”,恢复这一部分人民的平等地位。在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社会进步,大力加强统一。在巩固边防上,他铲平青藏地区的叛乱势力,追剿仍图再起侵扰中原的蒙古贵族集团,相继取得军事的胜利。
别具一格的用人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合,孟子就说过:“尊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类的话。从原始含义来看,“贤”往往和“不肖”对称,是指品德高尚又才干出众的人,它包含了德与才两方面的含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墨子说:“列憾而尚贤”。《尚书·大禹谟》说:“野元遗贤、万邦咸宁”,等等。在很长时间人们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贤”这个词的。
到了北宋司马光那里,则别有一番解说。他以为,世俗不加区别地把才与德都混称为“贤”,结果导致了“失人”,即将人才鉴别错了的严重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首先把德与才的概念区别清楚。什么是才?“聪察强毅”是也;什么是德?“正直中和”是也。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才者,够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也不赞成把人简单地划分为贤与能两大类,而应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味地抹杀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含义的:“革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论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即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恩,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总之,在雍正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在雍正心目中,田文镜、李卫、诺敏等名噪一时的能吏乃其最上者,而清官巧宦的典型则是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之辈。”
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士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盛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治理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生,“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易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钓誉、欺世奸诈之人;为众人所攻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倍加呵护。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13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下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务实反省的作风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30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6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也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伍
装甲铁流之魂: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