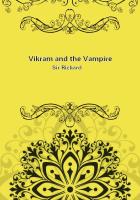当文衣单的重剑碰到妇人身上那枚玉佩时,妇人并没有表现出少年所期许的讶然,依旧端坐在营帐中最为舒适的蒲团上,双手交叠于前,静静地看着少年。
少年从小便被父母遗弃,自然也没得到过所谓的亲情与关怀。至于文姓夫妇,在那种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即便他们很想给予少年一丝亲情的温暖,也是奢侈难求的。
因此,当少年接触到妇人那般温暖,充满关怀的目光时,他脑中所想着的不外乎是两件事。一是她接近自己究竟有什么目的,二是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求生方式,才能在这强大的妇人面前求得生机;至于妇人为何如此待他,他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想。
“可怜,真是可怜!”妇人连道两声,并缓缓从蒲团之上起身,径直来到少年的面前。她伸出嫩如青葱的纤纤玉手,轻轻地抚摸着少年。那小心翼翼地言谈举止,像是怕惊扰了眼前这只畏生的小兽,又像是怕捏坏了少年宛如瓷器的脸蛋。
“你究竟是谁?”少年虽然言语上显得十分强硬,但无论是从他右手指尖处地微微颤动,还是从他频繁眨动地双眼之间,都可以看出少年此举有点色厉内茬的味道了。
“你这般怕死,着实不像是大汉之人。”妇人并不在意少年的无礼,但是对少年如此举动很是失望。
汉朝自高祖斩白龙起义以来,至今已有四百余年。期间除去少有的几位帝王在位时,大汉多半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但几乎每位帝王所在期间,都对那些所谓的侵略者给予着最惨烈的打击。
汉人不善征伐,喜好用计。但这并不是侵略者以及汉人自身眼中所拥有的唯一特性,至少那妇人眼中的汉人,不仅仅如此。
在夫人眼中,抑或是在传统的汉人眼中,他们一直都有着一种称不上优点的优点,那便是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性情。无论敌方是强是弱,也不管自身是否有着进行反抗的力量。只要你敢打我,我必拼上性命也要换你一拳,哪怕没有蹭掉你的一块皮肉,这在纯正的汉人眼中,这也算值得。
有人说,大汉强盛时期自该如此,人们敢恨敢爱,快意恩仇的性情正是国家强大的一种表现。可如今天下纷争四起,战火连年不休;在这种情况下,不学明哲保身,依旧敢怒敢言的人,岂不是傻蛋一枚?然而,在真正的汉人眼中却并非如此,他们依然会是那些恩怨分明,快意恩仇之人,相反对那种懂得避世,逢凶化吉的“道人”,给予更多地反倒是鄙夷与谩骂。
因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斩草除根这种信念本就是大汉的立国根本,是大汉的灵魂。
这就是汉人!
就是有着这么光荣的称号,他们才能毫无道理的简单粗暴下去。
所以,文衣单另那妇人所怜惜的,并非他那瘦弱的身躯,更不是他那根基浅薄的念力;而是他骨子里,那早已烂掉地汉人之魂。
“明明生得龙睛凤额,一副天生的帝王面相;竟然如此懦弱,卑贱。”因此,妇人觉得好生可惜,便出言叹了那两声“可怜”。
然而,文衣单却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可怜之处。相反,他觉得自己十分地幸运,不值得妇人这般同情。因为他觉得,活下去才是人世间最简单,也是最粗暴最直白的道理。
所以,当妇人一脸失望地说他不像汉人时,他反倒松了一口气。就连原本将要崩溃的道心也在这句话中缓缓复苏起来。
“我确实不像汉人,如果可以,我宁愿不是!”衣单将小脸从妇人的手掌间拿开,那略显慌乱的神情再次平静下来,他微微颔首向着妇人说道:“恐怕您好像有些误会,我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拥有信仰的高贵子弟,只是一个为了生计疲于奔命的军士罢了。所以,您大可不必这样。”
少年话中所指的是,刚刚妇人为他活血化瘀,治疗肩伤的那件事。
再看妇人,虽然眼中的光彩不及先前那般明亮,但依旧紧紧地盯在文衣单的身上不肯撤走。
“你为何不愿被称为汉人?难不成,这让天下人都为之自豪的称呼,在你眼中就如此不堪入目么?”良久,妇人缓缓开口说道。
“只因汉室凋零,权臣当道;纷乱连年,匪患横行。如此大汉,如此汉人,又有何颜面称之为骄傲呢?”营帐中,一阵清风将帷幔推开,带着一道人影悄然落在文衣单身旁,开口说道:“您说,我说得对不对啊?师叔!”
“是你!”“你是?”两种截然不同回答在营帐中陡然想起,但另人不解的是,明明被人影唤作“师叔”的文衣单,一脸懵懂不知人影之中的所为何人;反倒是那姿容俏丽的美妇人,抢先一步认出了来人。
人影闻声从黑暗里走出,来到帐中烛光所及之处,将道袍之上的兜帽摘掉,露出一副笑嘻嘻的娃娃脸来。只见他再一次对着身旁的文衣单拱手行礼道:“道融,拜见衣单师叔。”
……
……
东南有山,名为龙虎;其山巍峨高耸,首尾绵延,形合抱气运之势。其上有河,名为“上清”,河中杨舟泛泛,载沉载浮。河的两岸,山峦层叠翠竹交错之处,仙气氤氲而生,遮挡住那红砖砌成的层层楼台。其下有峡谷深潭,碧寒幽静,仿若龙虎盘栖一般。
上清河的小舟上,一名男子正轻抚胡须,望着河水中倒影的青松,朗声大笑。男子脚尖轻点,自小舟之上腾空而起,来到山峰之巅,云端之处。他反手朝云海翻涌处一抓,将云边嬉戏追逐的两只白鹭收置身下,踏在其上向着群星环绕的道观飞去。
道观位于群山之间,却不似其他楼台一般放置在地,而是悬空而坐。其上三百六十五颗周天正星做盘旋之状,遮蔽着道观之上的苍天。其下花鸟鱼虫应有尽有,奇珍异果更是琳琅满目。仙雾自虚无氤氲而起,将道观衬得更似仙境一般。
男子踏白鹭而来,自道观上空纵身一跃,脚下升起股股清风,缓缓落在道观之前的太极上。太极之中阴阳交叠,生生不息;两池黑白各异的道鱼相互追逐,首尾相映。只见男子将手中一枚油符点燃抛掷在太极池水之上,黑白二火便由此自下而上来到男子所在的上空之中,霎时间,烈风突起,飞沙走石。只见,四只截然不同的小兽突然出现在太极池上空。它们之中,有体表碧绿的长虫,白绒绒的小猫,赤红色的小鸟以及蓝盈盈的王八。它们无精打采地在东南西北,各觅一处,安安静静地打起盹儿来。
至此,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将长袖一挥,身边再次出现八枚明晃晃地符箓。这符箓显然与刚刚那枚油符不同,其上印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金闪闪的大字。就听“嗖”的一声,八枚符箓自男子身边冲天而起,没入到道观之上的周天星辰当中。
再看男子,此时正双眼紧闭,嘴张唇合并念念有词,双手之间不断变换着各种掐诀的姿势。片刻间,就看他朝着身下的太极池用力一指,那黑白二色的道鱼便从池中腾跃而出,随着火焰一同进入到小兽所镇守的大阵当中。
良久,男子终于将大阵完完整整地运行起来,他取出手帕将额头之上布满的汗水尽数擦去,并把早已沾湿的道袍脱了下来。男子赤着肩膀来到太极池的正中央,将方才从道袍中取出的一枚玺印放置在那好似阵眼的地方,径直盘膝坐了下来。
玺印地放入使得躁动的大阵立刻平静下来。而玺印所放之处则投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柱,透过大阵打在那八枚符箓所去向的星空方向。
片刻,光柱缓缓收回,平静的大阵再次骚乱起来,只是这次没有刚刚那样声势浩大,在几番膨胀后便随着清风烟消云散。
至于那被光柱击中的八枚符箓,在大阵消失的那刻,环绕着一颗白色的星辰朝着龙虎山西北方的天空一簇而过,带起了好看的尾云。
“白星略空,大世无争!”男子在看到星辰所去向的方位后,小声说道。“西北方?竟然是他!”
说罢,男子缓缓起身,丝毫没有理会此处的狼藉景象,朝着身前的道观走去……
……
……
“我不曾拜师,何来的师侄?”文衣单望着身旁这位看上去比他还小的道童,疑惑地说道:“只怕你是认错人了。”
“非也,师叔你还曾记得,你这一身修行的法诀是谁教你的?”小道士颇为神秘的向着文衣单挤眉弄眼道。
文衣单听闻此言后,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你说得,可是那汉中城楼处的正一道观中的老疯子?”
“什么老疯子?那可是你师傅!”小道士被文衣单那大不敬的言语气得小脸通红,经过好生一阵平息后,才接着对文衣单解释说:“那老疯子,呸!师祖乃是龙虎山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也是咱们天师府的第三位天师。前些日子,师祖羽化升仙之时,曾对现任天师,也就是你师兄说过,他曾经在建安十七年间收过一个天资聪颖的孩童做亲传弟子,希望你师兄可以将你带回天师府好生教导。然而,经师伯运用星辰大衍术推算后,发现你就是老天师口中的那位弟子,因此师伯派我来,请你到龙虎山去认祖归宗,并参加天师府的继任大典!”
“喂,那边的小道士!”营帐中,在一旁等候已久的妇人见这道童竟要将文衣单带走,瞬间不乐意地说道:“我说你说完没有!虽说你年纪尚幼,但也不能仗着此等身份,在我眼前出言放肆吧?至于这位小少年,可是奴家看上的人哦!”
“夫人可是开玩笑了!几个月前,老天师可是被魏王收做了镇南将军。咱们自家人,您这样做,岂不是让魏王脸上无光么?再说了,妇人此时不在邺城养伤,不远万里来到此处就不怕大殿下怪罪?”道童虽小,但说起话来有理有据,期间还对美妇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威胁之意。
“既然如此,那妾身就不在此叨扰你们叔侄相会了。”说罢,妇人狠狠地瞪了道童一眼,并有些不舍的看着文衣单,缓步离去。
就在妇人掀开帷幔,将要走出营帐之时,身后再次传来那位道童的说话声:“夫人此去,还望多加小心;我临来时师伯托我带一句话给夫人,他说万事无所争,非保身之道;然知其不争,切不可生怨。望夫人细细体会其中的含义。”
语罢,帷幕再次落下,军营之中只剩叔侄二人,相立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