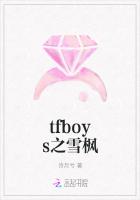不一会儿,心花和芳姨就来到后花场。这里培植的是园林观赏植物和室内观赏植物。一道道、一垄垄的培土就像刚被梳理过的头发,清晰有序,全都笼罩在白色大棚里。心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对眼前的事物和景象充满好奇。她不停地向芳姨请教花草树木的名称、特点、养护要领等,记得特别快。一个花农的日常工作是很繁杂的,但今天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修剪和施肥。一阵忙碌过后,芳姨领心花到东边墙头的一张长椅上稍作休息。心花见芳姨满头大汗,立刻从裤兜里拿出纸巾递给她,甚是贴心。
芳姨接过纸巾,看到心花沾满灰土的手,心酸地叹着气说:“心花小姐,真对不起!昨天让你受苦了,是我连累了你。”
“芳姨,你快别这么说。我不觉得苦,没事,别放在心上。”心花宽慰道。
“让我看看你的手臂。”芳姨一说完便握住心花的手臂,将她的衣袖迅速地往上捋,左右看了看。只见原本白皙嫩滑的手臂青一块紫一块地肿胀起来,芳姨心疼地说:
“老板娘这手劲可真大!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她对我们这些下人都从来没有打过,为何你刚来就造此毒手?”
芳姨的一番话确实让心花难受极了。她一声不吭地低下头,眼睛湿润了。此时芳姨从衣兜里掏出一瓶尚未开启的新药酒,拧开盖后将药水倒在自己手心里,再轻轻地涂抹到心花的手臂上。她的目光里饱含着母性的光芒,令心花感动不已。
“好多了,不疼了。芳姨,你别担心。你的药酒真是神奇的药酒,呵呵。”心花打趣说。
“孩子,真的好多了吗?这药酒你带着,隔两个小时搽一次,能消肿止痛,活血化淤,估计过两天就好了。”芳姨慈祥地说。
“呵呵,不用过两天,现在就好了。不信你看看,这,这,哦,还有这,都已经不肿了。”心花摆出一副乐观的笑容说。
“你这暖心的孩子,这药酒再好也不是神药啊,哪有说消就消的?”芳姨看着心花的手臂,满是疼惜地说。
“芳姨对我这么好,我的疼就不是疼了。”心花摸着手臂,坚强地笑着说。
“我真搞不懂她为什么要对你这么狠?而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不好好待在老家读书,跑到这里寄人篱下,见人脸色,受苦受难?”
心花极力掩饰的伤痛被戳中,心像碎了一样。她也在苦苦寻求答案。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一来到这里就如同进了地狱一般。她也有无数个心结想解开。可是,又有谁能告诉她为什么呢?为了不给芳姨带来麻烦,心花一肚子的苦水只能往里倒。
“呃,我想是我家太穷了,做亲戚会给她掉面子。而我到这里是为了将来能考上大学。芳姨,其实我能理解我姨妈,毕竟我是额外的负担,以后时间长了也确实会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心花懂事且认真地说着。
“嗯,就算是这样,那也不能乱来,况且还是自己的亲外甥女,照顾照顾也是亲戚情理。依我看,她一定有其他心思。我两口子跟她比较早,对她很了解。老板娘可是出了名的势利眼,而且城府深,有手段。要不然她当年怎么会把你姨父这个大老板从别的女人手里抢过来?”芳姨摇着头,蹙着眉说。
“哦?”心花一脸惊讶地看着芳姨。
“真的,这得从十九年前说起。当年老板娘和我们同在乐州西文区一家花圃打工。她那时做推销,由于长得漂亮出挑,又能说会道,一下子就被赏识重用。有一天,老板,哦,就是现在的老板到我们那儿买花,碰上了老板娘。由于做茶庄、酒店生意,老板每次来都会订一大批名贵花卉,阔气得很。老板娘每每见他出手大方,便起了心机。她把所有送货地址都记在脑子里,有事没事就到这些地方转悠,很快他们就好上了。不过当时老板已有家室,不愿意离婚分财产,一直以来只与老板娘保持地下情人的关系。可是老板娘哪会甘心?待时机成熟后,她便亲自找到老板的前妻闹事,把那个女的逼得死去活来。老板看在钱财的份上,还是不愿意离婚,老板娘就跑到竹林江畔以死相逼。她原本只想吓唬一下老板,却不料失足掉落水中。幸好你柱子叔在场,水性好,把她营救上来。但怕再次出事承担责任,老板只好先答应她的条件。老板的前妻不堪折磨和打击,无奈地接受了婚姻的破裂,移民出国了。当然啦,蛇鼠一窝嘛。老板就是个孬种,是个风流成性的无情郎,但碍于生意场上的面子,和怕日后纷扰纠缠,最终还是娶了老板娘。不过为避开老板娘的日夜监控,他买下了这个花圃,交给她打理。这么多年来,老板经常以应酬为名,彻夜不归。所以这个家不过是个空空躯壳。有人说老板是个精明的算盘子,他不想在老板娘的身上花太多钱,于是就雇人造了那栋洋楼。那栋楼虽然漂亮,但是是违规建筑,由于隐藏得好,至今也没人来查。平时呢也只有老板娘和城子住在里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才有机会进去,其他人连大门都进不了。所以你要千万小心,没有得到老板娘同意别随便进去。”
心花点点头答应:“嗯。”
芳姨咽了一下口水,继续侃侃说道:“哦,听阿万说啊,这个花圃的地皮已经正式划到城子名下,可值钱的咧。不过话说回来,女人找男人嘛,那就得找真情实意的,找情投意合的,千万不要看在钱的份上糊涂一时,悔恨一世。一定要清醒脑袋,刷亮眼睛,慢慢去寻。不然到头来,痛苦的人还是女人自己。所以啊,好闺女,钱财虽然重要,但它们不是幸福的保证。你看看老板娘现在的生活,就知道我说的在不在理。唉,曾经我觉得她是个可怜可悲的女人,满是同情。但从昨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只觉得她可憎可恨,因为她对你如此恶毒。我啊,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把老骨头咯却又无能为力。幸好昨天老板回来得及时,不然谁都不知道她发起疯来会对你再做些什么。唉……”芳姨摇了摇头,深深地叹息着。
“啊,姨妈真的是这样的人吗?那她现在和姨父的关系很僵了?”心花听完这些话后,心情变得特别复杂,焦虑地问。
“看在钱的份上,她不会跟老板过不去。但也很难说,因为人心总是难以揣测。”芳姨说。
“可我……觉得姨妈看到姨父回来的时候还是很高兴啊。”心花皱着眉头不理解地问。
“孩子,那些都是假的,装的。老板娘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她可比老板阴险、狡诈得多。她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也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背叛过婚姻的男人还能守得住吗?其实老板娘从一开始就不爱老板,不过是利用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罢了。所以老板经常在外鬼混,她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以她的性格,这绝对不是包容、退让,懦弱或者说无奈,而是等待。至于等待什么,只有她知道。”芳姨思索后说道。
“这样还能过日子吗?”心花不禁打了个寒颤,心慌得很。
“孩子,你还小,不懂得当婚姻遇到生活的时候意味什么。等你长大了,就会体悟到婚姻是存在苦涩的。很多人的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交易达成了,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继续,但幸福自始至终不曾降临。所以如果想要美好的婚姻,至少从一开始就要认真仔细。不该爱的人不能爱的人,千万别去爱。如果爱了,那只能认命。”
“啊,我突然感觉压力好大。不过我会牢牢记住芳姨的话,从一开始就认真仔细。”心花捂着胸口,带着些许焦虑和彷徨,郑重地说。
“不管怎样,孩子,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和你柱子叔打算在这里干多一两年就回老家开个小花店,到时我们就不能再陪着你了。愿上天保佑你!”芳姨握住心花的手,感慨地说。
“谢谢芳姨!你真好!嗯,有件事我可以问吗?”
“当然可以,问吧。”
“呃,我姨妈的脾气这么差,为什么你和柱子叔要跟着她过来呢?”
“当年你柱子叔不是救过她一命嘛。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她想把我们招过来,说包吃包住还给高工资,开的条件确实比其他花圃好。唉,我也是一时糊涂,净往钱上想,就让你柱子叔答应她了。没想到一干就十多年过去了,什么都习惯了,我们也懒得变换。其实我们老两口也没啥图的,就希望还能走动时多挣几个钱用来防身养老。”
“这么说她对你们还是有感恩之情,对吗?”
“嗯,感不感恩我不知道,只觉得她太善于利用一切资源来保护自己了。孩子,人的一切都会改变。她在变,我们也在变。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只求有份活儿干就好,受点委屈也会看得开。其实在哪儿打工都一样,不是指使别人就是被别人指使。如今我和你柱子叔都看淡了一切,只求平平安安干多几年,活多几年,临死的时候啊能安心闭眼就好。”
“芳姨,别想这么沉重这么悲观,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心花露着坚定的微笑,宽慰芳姨说。
“孩子,或许你说得对,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虽然生活充满许多无奈,但毕竟我们还活着嘛,呵呵”芳姨说着说着自己就笑起来,似乎是开朗的,也似乎是无奈的。
“嗯,我年纪不大,但也深有体会。生活的苦有时就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毫无心理准备。”心花想到自己的命运,又不免神伤。
这时,芳姨透过几层枝叶,瞄见了进来搬花的阿丛,便大声地问:“阿丛,现在几点了?”
“哦,快九点了。”阿丛回应,借着叶缝看了看心花,瞬间红了脸,匆忙搬起花盆大步流星地走出去。
“孩子,咱们出去吧。老板娘他们应该醒了,是时候吃早餐了。”芳姨站起来,拍着裤腿上的泥灰说。
“嗯,好的。”心花站了起来,却突然感到有些眩晕。是的,她今天知道了许多秘密。而这些秘密就像大山一样压迫在她心里,产生一种将要窒息的昏沉感,她想逃却已经逃不掉了。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这个美丽的花圃掩饰着黑暗的人心和冷酷的绝情。所谓的世态炎凉,或许会在这里充分演绎。她开始害怕,害怕美丽。因为美丽往往有毒,或在其本身,或在其周围。
心花一边思考一边默默地跟在芳姨后面,只听见她碎碎念,却听不清她说什么。当快到竹亭时,她们正好碰到城子打着哈欠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