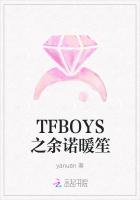妮娜弟在医院静坐被劝阻,医生拿出所有医疗档案,并说他们对她特别慎重,医疗方案是由专家会诊决定,用药每笔记录在案决无差错。这以后,妮娜弟总觉得姐死得不明不白实在太不公平,现在只有获得相当的经济补偿,才是对姐的亡灵的最大安慰。
于是他便希望有一个与妮娜贴身护士很熟的人去医院先探路,从护士身上打开缺口,拿到任何证据就能对医院起诉。经人介绍,他就认识了剧团大院的那位热心人,他在剧团演出部工作,在医院病床紧张的情况下,就是靠他在医院有表妹的关系,妮娜及时地住院医治的。这间病房的护士就是他的表妹。于是他便到剧团演出部找到了他,那位热心人当即愿意查明情况,他的名字叫耿耿。
但妮娜弟万万没想到,耿耿查下来这事可能是谋杀,而且与姐夫万烈有说不明道不清的某种内在联系,他说:我姐死了,姐夫有份,十恶不赦!一查到底!
万烈囬城后,从姨妈电话里还听到这样的传闻,简直心尖发颤,说他是害死妮娜的教唆犯。万烈确实在妮娜病重期间,见到她满面憔悴气息奄奄,三十多岁如同垂危的老太了,身上插满了管子,她在病床上呻吟,万烈走出病房,在走廓尽头的窗前,他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医生这样说过:现在该怎么办呢,妮娜这么活还不如死!
哦哦,我确确实实是对医生说过那两句话!我真该死!鄔殳嬿当即也掉了泪。但邬殳嬿明白我话里的意思么?
难道邬殳嬿因为我说了这話,认为我要她死就把她毒死了么?按鄔殳嬿那种独来独往什么也不怕的性格,她难道真的成了杀人犯么?那我就成了教唆犯。万烈往这上面想的时候,不由得手指也会发颤。
事情在发展着,万烈听说耿耿正在搜集证据,一定要把邬殳嬿告倒。耿耿传出话来,当时的主治医师曾在他的日誌里写道:由于病人情绪很坏,并发心脏病,计划是先稳定好心血管,养好身体,然后进行脑部手术,我们在医疗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病人突然死亡了。这是一起非常死亡,需解剖尸体作出决定。主治医师曾征求家属万烈的意见,被阻止了。耿耿断言:这里肯定有鬼。不仅如此,妮娜弟弟已经起诉了,但法庭说谁主张谁取证。目前没有开庭,是因还在取证。耿耿已找到医生,证明邬殳嬿曾先后找到他们,希望他们用什么特别手段,让病人马上死亡,或较快地安乐死。这就证明了她有杀人动机。这事万烈也不敢问邬殳嬿,就怕她果真是凶犯。这段时间,万烈的心时常吊着,他更怕邬殳嬿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里的医生,只能她自己下手了。
前几天,他在电脑里还收到邬殳嬿的来信,她说及妮娜之死却是那样乐观。她说:万烈呵万烈,人总要死的,千万不要再为妮娜难过了,你想想,妮娜如果活到现在,就恐怕又要花上几十万了,医院用的是进口的昂贵的药,不能报销的。你再想想,她幸存活下来了,你就终生服侍她吧,你的一生也垮了。如果复发,那就更惨了,你穷得当裤子当个光腚汉吧。所以说,妮娜和我们都是幸运的。
殳嬿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与妮娜的关系,让他内心一阵阵地难受。这个殳嬿哪,调到外地剧团,怎么知道大祸临头了呢?
万烈不愿去看望丈母娘的原因,主要怕她老人家要说起妮娜。而且他总觉得关于妮娜之死,她了解更多情况,当然小弟会把具体情况告诉她。但她并没有向万烈追问关于鄔殳嬿毒死妮娜的事儿,而总说女儿死了,让她心里很难受。见她时,她总是流泪,仿佛是在谴责他,他去干什么呢?后来妮娜母亲打电话来让他去玩,他硬着头皮去了。除了担心她问妮娜的事,还怕她问起他的工作,他在单位里下了岗呀!一想到这事脸上就发烧,无颜相见。不过,这次与儿子万欢、儿媳郁兰一起去,万欢会扯些别的,万欢可以做当箭牌。
当他们仨走进妮娜母亲家的宽敞的客厅,妮娜母亲高兴极了,她紧紧地抱住外孙,朗声地笑着,说:外公也时常念叨着欢欢,怎么不来玩呀!这会儿,老同事约他去打保龄球了,你们倒来了。妮娜母亲让雇的阿姨煎鸡蛋,下汤团。
她双眼盯着万烈看,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道:万烈,我知道你下岗了,你在想什么呢?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心里还憋着一鼓劲吗?
万烈忽然感到一个零丁,猝不及防,呃了半晌,才说:怎么说呢,我觉得选好下一步挺难,干编剧这行是选错了。入睡前对自己说:打住!坚决不想!但上床后,剧情在脑里又活跃起来,挡不住……可能因为我的神经有过创伤,我真是不适合干这一行……
妮娜母亲说:可以拍电视剧,台词短,开拍前看下剧本就记住了,欢欢,你外婆到了七十岁也客串过电视剧呢。
欢欢说:当然这比演话剧方便多了。不过有的导演要求把一场戏的词儿背下来,连拍一场戏然后插近景,但毕竟就一场戏,最多十分钟了不起了,这对爸还不是小孩床上翻筋斗鬧着玩儿么。
万烈说:爸哪有那么神的,爸从来是死做的。你给我记住,演戏不能凭小聪明。
欢欢说:兰兰,你看爸够厉害的,外婆给他在上课,他就给我上课。我马屁没拍成,反挨了一脚。
郁兰抿嘴一笑,瞥他一眼,笑道:活该!
妮娜毌亲把話转到万欢身上。她说万欢是小青年、老艺人,精通此道了。嘿,拍了那么多戏可不能忘了妈。于是她就沒完沒了地谈妮娜。
她先是胃癌是怎么得的呀?有些地方是贫困地区,转点路上只能咬窝窝头喝冷水,忙起来就空着肚上台演出。送戏下乡可就要随乡入俗,在河南贫困村随农民三頓吃红薯,胃里一直泛酸水,在广西山区随景颇族人家吃酸吃辣,什么口味都要接受。
而且贫困地区演戏条件差,有时住后台也沒条件,经常是睡大队仑库啦,学校礼堂啦,冬天的风雪会从门窗里钻进耒,她总是用腰带束住脚跟的被子御寒,睡后台的日子,她总是挑选风口的床铺。久而久之,就得了胃病。十年后竟变成胃癌。
切了我半个胃我还有半个,沒事!她总是这么说。
手术后她依然演戏。我记得她开刀后还沒拆线,正逢全国会演,剧团要把她参演的一台戏参加比赛,演出那天B角又病了,她说我原是A角,义不容辞应当我上!谁也拦不了她。欢欢呀,你不能想象,世上有象你妈那样不要命的!
你猜怎么着?她演的是个象李双双那样泼手泼脚的农村妇女,她说话时时常把手抬上抬下,结果一场演下来,内衣的胸前肚前都是血迹呀!英雄呵!她是到我家来换衣衫的,然后我就陪她上医院。她说:妈你不要告诉万烈,他准会骂我。她就是这么个不要命的,还是接角色啦,巡迴演啦﹐后来又调电视台当主持人。想不到脑子里都长出东西了,疾病总是找象她那样倔強的人!
她擦了擦泪水闪闪的双眼又说道:欢欢呀,外婆早该把你妈的那些亊儿告诉你听,你妈这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现在的人都想长寿,可你妈却说:人的贡献与长寿无关,骆驼在艰苦的沙漠里负重奔波活四十多年﹔鸟鸦整天呱呱叫却能活到七十年。欢欢,你妈就是这么看的呀。
妮娜毌亲说到这儿,見在场的三人都低垂着头不吭声,她马上说,不说她了,我是说她这犟脾气就是遗传我的呢。
我在省話的那年,被弄到七里湾搞斗批改。我原先是个温顺的人,可是那年春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死了一个人,-下改变了我的性格。
事情是这样的:那次回城休假的路上,春雾特别大,到了九点时才慢慢消散,有十辆卡车在乡村大路上缓缓行驶,四周的堤岸、麦地、苇荡、小河开始显露出来,文化局车队的司机们为了在午饭前赶到城里,加快了速度前行,我手拉把杆,闭着眼,随着颠簸的卡车摇晃着,突然间听到哇地喊叫,车上大哗,车停了下来,喊声哭声就响起了一片。人们呼喊着:不得了呀,不得了!他只剩个身子还站在那儿,头没啦,头没啦!-------
我赶忙跳下敞蓬大卡,那无头的身体被人围着,我忙脱下外衣罩住还在流血的颈部,不由分说,他无论冬春都穿件旧风衣,竖着领,那就是剧团的中年演员大块头老倔头。平时他爱说笑話,快板说得很好,朗诵是在剧团出了名的,在七里湾他教会大家劝伪军投降的小调,现在每个演员都会唱:叫声我郎你细听,八路开来十万兵机枪大炮无其数,你要抵抗活不成,叫声我郎听仔细,没有办法我教你,放枪要向天上打,不拉弦的手榴弹往外扔-------他边唱边扭着舞蹈乐得大伙儿直不起腰-------现在他就这么意外地死去,真叫人不可相信。原本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站在车上好好的,后来不知怎的用手撩起篷布,伸出头向外看,也许是看渡口到了么,这时突然迎靣一辆运输卡急驰而过,把他的头拉掉了------哇哇哇哇-------我和别的女演员都哭了-------
所以说,人的死都是突然死亡,有什么要闹要吵的呀。
妮娜弟,我的这个现世宝,现在还在查他姐的死因,说市話的一个叫符之及的,还特别起劲,还组织了妮娜非常死亡调查组,这到底为哪桩?我真想去找你们的齐团长!
噢噢,别别,千万别。万烈站了起来,苦皱着脸,忙摇着双手阻止道。说这里边事太复杂,太复杂,这亊要弄个明白,不然我真对不起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