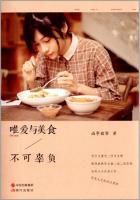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扛上肩哟!”
“嘿——嗬!”
“走起来哟!”
“嘿——嗬!”
“一条道哟!”
“嘿——嗬!”
“不回头哟!”
“嘿——嗬!”
“上跳板哟!”
“嘿——嗬!”
“莫低头哟!”
“嘿——嗬!”
“扛一包哟!”
“嘿——嗬!”
“钱一串哟!”
“嘿嗬嘿嘿!”
泉州临江的码头上,回荡着热火朝天的搬运号子。
夏末正午的阳光,晒在搬运工们因汗流浃背而显得黝黑发亮的皮肤上面,更显毒辣。
正午的阳光虽然毒辣,但是搬运工们却显得格外的精神抖擞,倒不是因为号子里“扛一包哟,钱一串哟”的激励,而是因为现在他们肩上所扛的,已经是这艘商船的最后一批货物。经过一上午的劳碌,一整船的货物终于上完,终于可以休息开饭了。
在这些搬运工中间,有一个人的皮肤明显没有旁人那般黑。也许因为他是新手,也许他天生就不容易晒黑。但是只要在这码头上干得久了,早晚都会被晒得跟黑炭一般。
当他把最后一包稻米卸下肩膀后,对指尖残留的触感依然恋恋不舍。
由于连年的战乱,北方的粮价常年居高不下。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正当秋收之前,最是青黄不接,也是一年中粮价最高的时候。这一船稻米此时运到北方,几乎可以换回同样的一整船绢布,获利之丰,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而这位肤色不深的搬运工却可以想象,所以他才会对指尖残留着的隔着麻袋传来的稻米的触感这般恋恋不舍。
商船在装满稻米后,并没有多作停留,很快便扬帆起航。毕竟在秋收前后,粮价的贵贱可是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虽然时间还算宽裕,却也没有任何可以拖延的理由。
商船离港后不久,一艘小艇也从码头出发。小艇张起一叶轻帆,没过多久便追上了满载稻米的商船。
在从商船侧舷超过的时候,小艇上的几人,都饶有兴致的看着眼前这艘航速缓慢的商船,炽热的眼神中,毫不掩饰内心的贪婪。其中一人,正是之前码头上那个肤色不黑的搬运工。
闽江之上,舟来船往,井然有序,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安静祥和,
……
一叶孤帆,浮在波澜不惊的碧蓝色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席帆侧过一个角度,驾着侧风缓缓航行。
船上共有三人,都戴着斗笠,两个人在操帆划桨,还有一个人扶着舵,在看风景。
这里,是神州东南,闽越沿海,海岸线极尽蜿蜒曲折之能事,既是山与海的交界,又是山与海的交融。既有山兀立于海中而为岛,又有海迷途于山中而成湾。
看风景的人,名叫林宏道,是一名海商。海上的岁月并没有在他将近四十岁的脸上,划下太过深刻的痕迹。他自诩运气一向很好,并期许着这次的“买卖”也能有一样的好运气。
海商的生涯,向来充满了危险,在丰厚的回报背后,隐藏着的,是风暴,是巨浪,是未知的远方,是迷失的归途。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葬身鱼腹,才能换来琉璃的色彩和香料的芬芳。
但也只有那些敢于直面危险的人,才有机会从困境,乃至于绝境之中,采撷到成功的果实。
林宏道虽然运气比较好,尚未经历过太多真正的危险局面,但并不意味着他会畏惧那些危险。前面的路,并不好走,但是一旦成功,回报却也难以估量。
今天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一笔大买卖,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过的最大的买卖,各种意义上,不论成功还是失败。
……
沿海群山中的某处,吴刚正在挥斧砍树。他并不是樵夫,而是一名盐农,在海边煮盐为生。而煮盐,自然需要烧柴,烧很多很多的柴。
所以吴刚并不是一个人上山,他还带来了三个帮手,三个小帮手。
一株碗口粗细的树被砍倒,吴刚终于可以放下斧头歇口气,一边揉捏着酸疼的胳膊,一边自然而然的把目光瞥向了不远处那三个充满朝气的身影。
正在采野果的,是自己十三岁的女儿吴月儿。她可是吴刚的心头肉,方圆十里,哦不,方圆五里之内,可没见过哪家的小姑娘有她这么可爱标致的。
旁边,则是孙家的小兄弟两个。
正在用柴刀砍柴的,是哥哥孙远,虽然今年只有十五岁,却生得高大,尤其是最近这两年,就像雨后的新笋一般,蹭蹭蹭的直往上长,眼瞅着个子就快超过自己了。
正在捡拾枯枝干柴的,是弟弟孙帆,今年十三岁,虽然比哥哥矮了一头,但想来也快到长个子的时候了。
看着这两个小男孩,吴刚忍不住开始想象,自己的小儿子吴小宝,再过些年也能像他们这般大,也可以带到山里来帮忙了。
看了看偏西的日头,吴刚对三个孩子喊道:“该回去了,你们先回船上吧,我一会儿就来。”
“回家喽!回家喽!”三个小家伙闻言如蒙大赦,一阵欢呼。
然后孙家兄弟一起把剩下的柴禾都捆好,用扁担挑了。吴月儿则把装了半筐野果的背篓背上,临走前还不忘擦了个果子塞进父亲的嘴里,把吴刚乐的嘴都合不拢。当然,谁的嘴里塞了个果子都会合不拢的。
……
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在山林间静静流淌。淙淙的水声和清脆的鸟鸣,交织成一曲天然的乐章。
溪岸的浅滩上零星的搁着十几条小船,小船上都堆放着柴禾,它们的主人也都是进山樵采的盐农。
这些天,盐田陆续都将开灶。盐农们每天都会约好,去同一片山林砍柴,如此一来,大家相隔不会太远,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毕竟山林之中,偶有野兽出没,有些盐农甚至还会带上弓箭以备不虞。
当然,在离开村落不远的山中,本就有猎户常年打猎,凶猛的野兽一般很少会出现。只要别深入山林太远,基本上还是安全的,否则吴刚又怎么敢让三个孩子单独行动。
……
三个小家伙回到自家的船边,先把背篓和柴禾卸了,又吃了几颗果子。然后,孙家兄弟拿出了弹弓,到处寻找目标,比试谁射得更准。
吴月儿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趣,又有些口渴,便寻了一片合用的芭蕉叶,在清澈的溪流中冲洗一番,然后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水杯,从溪水中舀水喝。
水的甘洌,叶的清香,极好的驱散了一天的疲惫。
“这里的水真好喝,你们也来喝水吧!”自己解完渴后,吴月儿又招呼起了孙家兄弟。
“来,喝吧。”吴月儿先把舀满水的芭蕉杯递给了哥哥孙远。
孙远从吴月儿手中接过芭蕉杯,饮了一半,就要递给弟弟。
孙帆却不接杯,说道:“你喝完就好,我再舀好了。”
“好吧。”孙远并不知道,弟弟这其实是吃味了,因为吴月儿先把水给了他。
孙远喝完水后,正要把芭蕉杯递给弟弟,却被吴月儿抢先一把夺过。
吴月儿又舀了一杯水递给孙帆,孙帆接过芭蕉杯,避开哥哥喝水时用的叶沿,把纯净的溪水一饮而尽,心中却是说不清,道不明,别有一番滋味。
把芭蕉杯还给吴月儿后,孙帆不知道从哪鼓起的勇气,问道:“月儿,我和哥哥,你更喜欢谁?”
“都喜欢呀。”吴月儿不假思索的答道。
如此不经意的回答,孙帆显然无法满意,继续追问道:“如果只能喜欢一个的话,你会喜欢谁?”
“嗯?唔……”吴月儿看了看孙帆,又看了看孙远,又看了看手中的芭蕉杯,突然一拍脑门,似乎想到了什么,笑着出主意道,“要不这样吧,你们去找海螺,谁找到的海螺更好看,我就更喜欢谁好了。”
孙远有些犹豫道:“这,好像有些儿戏吧?”
吴月儿嘴一嘟,假装生气道:“哼,好像你是大人了似的,觉得是儿戏的话你可以不用去找。”
孙远赶紧说道:“我找,我找,我找还不行吗?”
吴月儿得理不饶人道:“你这么说,好像不是很乐意的样子嘛?”
“乐意,乐意,非常乐意,极其乐意,一千个乐意,一万个乐意!”
孙远看似被吴月儿说得焦头烂额,孙帆心中却反而更不是滋味了,这怎么越看越像是小两口在说话呢?
……
暮色将近,归帆渐集,成群的鸥鸟发出嘈杂的叫声,或在天空中盘旋穿梭,或在海面上随波起伏,让人能感觉到这里充满了蓬勃的生气。
眼前的景象,林宏道无比熟悉,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哪里有暗流漩涡,哪里有礁石浅滩,他都最清楚不过。就算让他在这片海域中闭着眼睛掌舵,也断然翻不了船。
在数重山岛的掩蔽背后,是一座被群山环抱,方圆近十里的海湾。许多渔船每天早上从这里出海捕鱼,到了晚上再回到这里。
海湾的西侧,绕过一座伸入海中的山后,是另一座隐藏得更深的海湾。
这是一条狭长的海湾,宽约三里,远处在山中转折,不知道后面还有多长,看上去像是什么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但从小生活于此的林宏道却知道,这条长达数十里的狭长海湾之中,只有几处山溪小河汇入。这里,依然是海。
……
“爹,喝水。”
“嗯,乖!”
满头大汗的吴刚,接过女儿递来的芭蕉杯,入喉真是说不出的清凉解渴。但是女儿接下来说的话,却让吴刚有些哭笑不得。
“这杯子反过来还可以当帽子用,爹你戴上试试。”
“啊?这个,男人是不能戴绿色的帽子的。”
“为什么呀?”
“因为……嗯……总之,这是不好的意思。”
“哼,不戴就算了。多好看的帽子,远哥哥你来试试。”
“我觉得还是弟弟来戴比较合适。”
“哎呀,不用谦让。我再去做一个,你们一人一顶。”
……
父女兄弟四人把装满了柴禾的小船推入小溪中,用竹竿撑着顺流而下。
出了山林后,是一片平坦的溪谷。溪流在稻田间曲折前行,沿岸的村落炊烟袅袅,看上去显得宁静而又祥和。当然,有时候犬吠在邻近的村落之间此起彼伏,听着也挺闹心的。
“咕……咕……”
“咕……”
也许是看到了炊烟的缘故,顶着芭蕉叶的孙家兄弟的肚子相继提出了抗议。
“哈哈哈哈,瞧把你们急的。再忍忍吧,就快到家了。”
“嗯。”
“咕……咕……”
……
稻田的尽头,是一座较大的村落。村落的背后,再经过一段盐碱的荒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水波不兴的池塘,这里就是盐田了。
小溪从盐田的边上流过,沿着山脚注入到一条狭长的海湾中。
东南沿海,每到夏秋之际,多有狂风侵袭,巨浪滔天,不似长江以北,可以直接在平坦的海岸线上构筑盐田。
这里之所以能够构筑盐田,是因为这条海湾狭长而又曲折。外海就算是有再大的风浪,也都能够大而化小。
而且这条狭长的海湾深入群山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溪谷入海的地方,才会有一些平坦的滩涂,可以用来构筑盐田,所以这里的盐田就显得格外难得。
但是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盐农们虽然坐拥稀有的盐田,却也只是能够维持生计而已,因为他们并没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交易对象和价格。
……
小溪和盐田之间,是一道长堤,盐农们的家,就建在这道长堤上。
把小船拖上岸系好,吴刚让三个孩子先进屋吃饭,自己则留下来,把船上的柴禾挑进柴房。
没一会儿,却见自己的小儿子吴小宝跑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自己从没见过的小木剑,一边跑还一边喊:“爸爸,爸爸,家里来客人了。”
吴刚闻言,赶紧放下扁担,拉住吴小宝的手就往家里走。
只见夕阳中三个戴着斗笠的人,站在自家门口等着自己,氛围颇为诡异。
为首一人缓缓摘下斗笠,夕阳照在他将近四十岁,并没有留下太过深刻痕迹的脸上,吴刚几乎瞬间就认出了他。
“道士?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