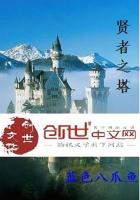五月十三日,夜幕降临时,福顺沿着土路往下走,走到福生家屋前时,看见有个穿黑白色校服的女孩正在往上走,巧捷也看出了面向自己走过来的人是父亲,便叫了一声爸爸,福顺愣了一下,“回来就好!”他念叨着。
巧捷快步走回家,她看见灶屋里有一束摇摇晃晃的亮光,一支燃了半截的蜡烛在习习晚风的吹拂下烁动着,芸香正在灶后忙碌,碰得锅碗发出一连串悦耳的脆响声,她的头上戴着福顺在井下作业时才戴的安全帽,炭黑在脸上抹了一绺。巧捷对着屋里喊了一声妈,芸香怔了一下,快步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女儿毫发无损,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地。
福顺领着蕙兰回来了,锅里的饭也熟了,芸香在灶后舀饭,巧捷和蕙兰各端一碗走出灶屋,走到街院里饭桌的椅子旁准备坐下来,福顺大喝一声不准坐,吓得巧捷差点把碗扔在了地上。四个人并排着站在街院里吸溜着面条,时而埋头喝碗里的汤,嘴边传出“噗嗒噗嗒”的响声。房梁被突如其来的抖动震得干响,蕙兰嘴里喊一声“妈呀”,端着碗朝着屋角的空地冲过去了,巧捷和父母紧跟其后,竟然跑出了整齐的队形,就像几年前刚买回电话时那样。
搁下碗,芸香从衣柜里取出福顺前些年从外地背回来的军用帆布包,把放在抽屉里的现钱、存折以及一些重要证件装到最里层,接着把每个人的衣服装了两三件,背包被撑开,费了好些力气才将封口系好,福顺把叠好的两床被子抱在手上,一家人朝着柏林的硬石板走去了。开会和福生两家人也都抱了被子往这边走了过来,电筒光在沟渠的狭窄土路上时明时暗。
到了一块平整的地方,男人们把被子递到小娃和女人手中,拿着镰刀斧头进了近处的树林,砍了些树干,把树梢剃下来。一阵忙碌之后,一个能容纳十来人的茅屋初具雏形,男人们把白天从田坎的桑树上卸下来的干得枯黄、但因被雨水浸泡长了些霉斑的稻草铺在茅屋顶上,再用牢固的线绳一层一层固定好,接着在上面铺了一层家里打顶棚用的厚油纸,万一下雨,这东西能把雨水顺到四周去,省得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茅屋里也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再铺上竹席和被褥,小娃们忙不迭的滚进去玩闹起来。福生手里拿了个随身听样式的收音机,他用右手拨了下开关,立即从里面爆发出一阵尖锐的杂音,他连忙抽出天线,杂音减弱了些,但还是听不到主播的的说话声,他拿着收音机朝着那条巨大的石梁走去,音效越来越好,主播正在播报地震灾情。他俯身快速捡了几块石头垒了个石台,把收音机放在上面。河对岸的人们也正在忙着搭棚,电筒光像天空的星辰,光影很小,不断移动着。有笑声在黑暗里炸开,紧接着有人说:“都啥时候了,还笑得出来!”笑的人不以为然,“我们不是还好好的活着么?你看汶川那么多人没逃出来,我们这是命大,做梦都应该笑醒!”“真是没心没肺!”“你懂个屁!”
琳琳的手机持续不断的传来“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的来电铃声,她总是快速挂断,然后神情紧张的回复短信。
“再等一分钟,说不定就没命了。”琳琳妈自顾自的说道,她看着琳琳问道:“这大晚上的,哪个给你打电话?”
琳琳有些难为情,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的问话。
“女娃嘛,这么大有人打电话很正常。”芸香开了腔。
“我是说哪个这一晚上打电话来响两声就挂,也不问下我们地震严重不。”琳琳妈说道。
这时候,慧芳的电话响了,是文炳打来的,文炳在职业中学读了一年就被分配去了广东工作。慧芳接了起来,不料手机漏音,文炳的声音变得浑厚粗犷,这让巧捷很不习惯。
文炳:“妈,地震感觉啥样的?”
慧芳:“跟筛糠一样。”
文炳:“我想回来感受下!”
慧芳:“你娃儿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地震有啥好感受的?你看汶川一下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这儿人倒没问题,但是抖一下我们也吓得屁滚尿流,李春霞昨天在茅坑上吓得裤子都没提就跑出来了,还好没掉进茅坑里。这一地震,我们都变成野人了,这会儿几家人在柏林里睡茅草棚,你老老实实的呆在广东,等不地震了再回来!”
文炳:“你们三个都体验过了,就我一个人没体验过,这不公平!”
慧芳:“我要是手杆再长点,非要给你两巴掌,你不晓得地震是啥样的,那我给你说,你以前过吊桥的时候爱在上面筛来筛去,其他人根本走不稳,地震除了走不稳之外,还有房子倒,田坎垮,山上的石头从四面八方往下滚,河那边的山都掉了一层皮。”
文炳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想象地震的场景。
文炳:“今天我们公司组织捐款了,我捐了100块钱,是给你们捐的,到时候记得收啊!”
慧芳:“哦呵,你这是给活人烧纸!”
开会掏出扑克牌摆在铺盖上准备打,福顺站了起来,拿着电筒走了出去,说是去找老太爷。二零零八年开春以来,周成才的离家出走愈演愈烈,以前是背着人偷偷的溜出去,现在即便是福顺站在他面前,他照样旁若无人的往外走,只要福顺不上去拉拽,他就不会停下脚步,福顺说什么他都置若罔闻。有天在自留地种苞谷,周成才从屋里出来顺着路就往下走,福顺几大步跑到他身旁把他拖到地边的土路上坐着,然后回到地里继续挖窝扔玉米,由于力气大手脚快,一会儿工夫就把两环地挖完了,芸香在后头施肥盖土。
“莫挖了,你挖这么多我盖不完……快莫挖了,我盖不完啊……”周成才歪着身子坐在石头上对扛着锄头的福顺说道。
福顺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一脸无奈的望着父亲的芸香,欲哭无泪。
芸香看着福顺顺着土路走了下去,转了个弯开始向上走,电筒光随着他腿脚的迈动而晃动着。福生两口子和开会两口子对坐着打起了扑克,蕙兰、文静和琳琳妹妹三个小娃在铺盖上滚动打闹,巧捷在听琳琳讲给她打电话的那个男人的事,只有芸香,定定的、死死的望着那束逐渐微弱的电筒光,余震不时的发生,地面微微颤动着,每一次的力度都不一样。
河对岸的说话声平息下来了,移动的电筒光也没了踪影,四下里一片漆黑,二闷子家的瘦狗狂吠了几声,大概是开会家圈里躺卧着的牛突然站立了起来,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响着,山头的那只大鸟不知飞去了哪里,这两个夜晚都没听到它那沉闷的吼叫声。草棚里的小娃们接二连三的打着哈欠,文静已经安然睡着了,四个成年人还在兴致高昂的剃光头。
“嗨哟~嗨哟~”周成才喊着口号声由远及近,芸香连忙探头出去,果然看到一束电筒光朝着窝棚的方向走了过来,只是那速度像个蹒跚的老人。
快到窝棚处有一截陡峭的乱石路,福顺叫了声开会,让他过去帮忙,开会扔下手中刚码好的扑克牌走出了窝棚,福生女人看了福生一眼,福生识相的丢下手中的牌跟在开会身后走了出去。走到乱石路中间的一道塄坎时,周成才直挺挺的站立着,上半身倾斜着倚靠在福顺身上,福顺推了推,周成才往前迈了两个碎步,可等他稍微松懈,周成才趁机倒退了回来,逼得他往后退了两步才站稳。开会和福生见状,连忙从塄坎上跳下去,福顺抬头,开会抬中间,福生抬脚,三人协力将老太爷往上搬运。
“哎呀,你们要把我往哪抬嘛?哎呀……”周成才嘴里抱怨着。
终于把老太爷搬运到了窝棚处,福顺早已累得满头大汗,开会跟姨父说不要没事到处闲荡,现在正地震呢,万一哪儿滚落个石头下来砸了你咋办。周成才对外甥说的话不予理睬,嘴里自顾自的说着:“哎呀妈呀,这把我累得!”福顺特意睡在窝棚的最边沿,第二天清早睁开眼,父亲已没了踪影。
过了些天,村上给各家各户派发救灾物资——饼干、方便面和矿泉水,有人说发啥水嘛,山上河里到处都有水,说不定比这瓶子里装的还干净呢,要发干脆直接发钱,让老百姓缺啥买啥,我们这些农老二天天喝矿泉水不逗人家笑吗?另一些人不爱听了,说国家给你发水你还舌头长废话多,这些是人家几万人的命换来的,平常咋不给你发矿泉水呢?
刚恢复通电的那几天,全国的电视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打开电视机,全是关于地震灾情的播报画面,同样身为灾区人民,看到电视中出现的夷为废墟的建筑、血肉模糊的同胞,既难过又庆幸,尤其是福顺,如果矿井的顶棚支撑得不牢固,如果震动再强烈些……他不敢往下想,芸香也不敢往下想,一家人谁都不敢往下想。
余震渐渐变得微弱,晚上,人们不再怀抱着被子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照着电筒排着不太整齐的队形往柏林的硬石板走去睡觉,不过他们依旧不敢锁着门睡死过去。福顺在街院里打了个简单的地铺,他和芸香睡在这里,巧捷和蕙兰睡屋里的床垫,房门敞开着,便于余震动静过大时逃离,年轻人不警醒,做父母的,怎能在屋里的床垫上睡踏实?
白天,人们重新回到地里做活路,饿了就回屋烧两瓢水泡一桶方便面蹲在地边吃,那弯弯曲曲的面条泡在泛着红油的汤里,腾腾热气中飘散着干葱花被开水泡开后的香气,用胶叉在纸桶里绕两圈,泡软的弯面条就缠在了叉子上,把叉子从纸桶壁面划到嘴边,吸溜进口时,发出一阵美妙的响动,听得旁边的人恨不得上去抢食两口他的面。吃面的人吃得更响了,还故意吧唧起嘴巴,红色的汤汁溅到脸上和衣服上,抬起手随意的抹两下,下地干活谁不是穿着破烂的脏衣服呢?溅的汤汁只要抹均匀即可。人们爱吃方便面和饼干,从村上领回来的两箱方便面和饼干省着吃,但海水经不起瓢舀,两个纸箱很快就变得空空荡荡的了,矿泉水喝得比较慢,往往喝一半剩一半,庄稼人不习惯铆足劲儿挖地的时候喝着两块钱一瓶的端端正正贴着标签的矿泉水。
地震把房子摇得走了样,但人都安然无恙,日子还得过,不种地不务弄庄稼吃啥呢?要是在剧烈的地震中活了下来却因为懒散被饿死了岂不成了世间最大的笑话?身为农民,只要能动弹,就要下地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村上的干部领着乡上的干部,一行七八个人挨家挨户的视察灾情,听人说国家要给重灾户派发专项救灾款用于重建,有人逢场就往集市上凑,到处打听重灾户的名单到底有哪些人;有人自告奋勇的给单身的干部介绍姑娘。
八月中旬,巧捷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关于恢复上课的通知。
学生们重归学校,足球场上立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板房,门口处贴着高三各班级的字样,教学楼横七竖八的裂着口,学生公寓也不例外,外围拉起了一道明晃晃的警戒线,学生们只能住进在篮球场上搭起的密密麻麻的蓝色帐篷里面。帐篷内的面积仅有几平方,学生们从教学楼后面搬来掉落下来的砖头在地上铺了三四层,再垫上一块一指厚的木板,接着铺上被褥,睡上去硬邦邦的,翻身会咯吱咯吱的响。
夜里下了场雨,早晨醒来,学生们刚睁开惺忪的睡眼就被吓得眼仁儿鼓了出来,床边的鞋和放在地上的杂物都浸在了污汲汲的水里,被褥也湿漉漉的。中午出了太阳,帐篷内温度一路飙升到45°,根本无法午睡,只能勉强趴在板房教室的书桌上休憩,板房对地震极其敏感,地面稍有抖动,房顶就会传来类似于断裂的巨大声响;同时,板房的吸热性极强,学生趴在书桌上午睡时,总要出一身臭汗,有学生受不了这种罪,瞅着吃晚饭的空隙,拖着行李箱去校外租住民房。
学校外的街道大体上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气息,但还是有不少店面房门紧闭,玻璃门和门锁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少数年久失修的危楼在地震后摇摇欲坠,现今已被推土机夷为了一堆残渣废土。那学生一路走一路问,路人们纷纷摇头表示遗憾,一直走到郊外的深巷中才发现有空闲民房,学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房东的要求,回学校搬运行李时,恰巧被班主任撞见,班主任黑着脸领着学生进了办公室。
“你要出去租房子住?”班主任质问道。
“嗯。”
“我知道住帐篷很恼火,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可是高三将近两千人都能坚持住帐篷,你为什么不能?”
学生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开腔。
“外面很多房子是危楼,而且离学校那么远,安全谁来负责?住帐篷确实会吃一些苦,但是每晚都有四五个老师执勤,确保你们的安全,再说,现在余震不断,万一楼房发生垮塌,你父母咋办?可惜了这么多年的大米喂了你,喂头猪还能卖几百块钱……”
每天晚自习后,球场上的帐篷内亮起星星点点的光芒,一直延展到球场边沿,像无数只萤火虫散布在蓝色的海洋上空,教学楼下安装了许多水龙头,男女生成群结队的拿着脸盆过来洗漱,相互喜欢的人会趁机凑到一块儿说说话儿,直到熄灯铃响了操场上的路灯灭了,沸腾的操场才渐渐平息下来。白天站在高处往下看,密密匝匝的帐篷很是壮观,叫人忍不住感慨:这样的高三一定是别致的高三,多年后回想起这个场景,很难说不会怀念,但是此刻,还是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高三的日子本就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