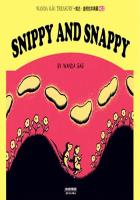己到深秋,地里的庄稼大部分都已进家,现在只剩下了红薯。每年要到霜降以后,甚至要到下了苦霜才能把红薯收回家。
今年秋天雨水少气温高,天气比较干燥,庄稼长的并不好。
天明,我就被喊起来,穿好衣服就出了门。在东南门里边等齐了几个伙伴,就一同直奔大杨庒南地窑厂红薯地。这块地是离家最远的一块地。天明起来,赶到地里东方的太阳已是树梢高。由于离家太远,早饭和午饭都不能赶回去吃,只能在地里自己解决。
同来的几个伙伴都是我的邻居,他们的父母都是和我爹一样,种地主二八地的种地户。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地里解决两顿饭,所以来时都要到打麦场抱一些干柴草来,以备烧烤食物用。
我们把抱来的干柴草放到红薯地头,就开始了准备我们的第一顿饭。前一段地里可吃的东西还很多,可以烧大豆角,煮大豆子,还可以炸焦芝麻。现在不行了,那些庒稼早进了家,现在地里只有红薯,所以我们也只能吃红薯。
今天我们来了四个人,按以往的规矩是合伙烧红薯。这种合伙烧红薯,只是把各人的红薯拿来放在一起烧,但红薯还是各人是各人的,并不能混着吃。这一点是大家都明白并无条件遵守的。
下边就开始了第一项工作,就是扒红薯。这也是有规矩的,那就是各人只能扒自已那块地的红薯,绝对不许扒别人的红薯。
我来到我家那块红薯地,顺着红薯沟寻找地下的红薯。我知道,凡是红薯藤下,地皮被撑裂的地方肯定会有大块的红薯在其下边。因为只有大块的红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才能把其上部的土块撑破。我很快就发现,一块被撑裂并拱起的地块,知道其下边必有大块红薯躲藏。于是就蹲下来,用手把撑裂的土块挖掉,再把那些耕作土掏出来。在不太深处,就发现了一块细长形的大块红薯。再把那块红薯两边的土掏出来,最后就用两手指把那块红薯抠了出来。这个过程全部是用手来完成的,用不着铲子之类的工具。这块红薯很符合烧红薯的条件要求,因为它的个头大,且又是漫长木锤形。这种体型的红薯好搭架,易烤熟且又不易被烤焦煳。
要准备两顿饭的材料,一块红薯肯定不行。就这样我顺着红薯沟继续往前寻找,时间不大就又挖了三块。四块大红薯,两顿饭足够了。
我两手捧着四块红薯回到了地北头。他们三人也各自从自已地里挖回了红薯,也先后回来了。
学文哥用木棍在红薯沟上挖了个圆形的土坑,在一边留有缺口。这个不太深的土坑就是烧红薯的炉膛,留这么个缺口是准备从这里往炉膛内加柴草。看到他俩把大家挖来的红薯,当着大家的面,在表皮上用指甲刻划成不同的记号,以此来区分不同的归主。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红薯,在土坑的周围垒成一个空心的宝塔。
至此,第二个程序,把挖来的红薯垒砌成一个空心宝塔,就算完成了。下边要进入第三个程序,也就是生火烧红薯。这也是整个过程的最关键的程序。弄得好,能把这一窑红薯烧得金黄剔透,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扑鼻,吃到嘴里软绵可口,又香又甜赛沙糖。
当然,这要先生成火才行。生火在当时也是一个更关键的技术活。当时在乡下的农村,打火机肯定是50年后才有的东西。就连火柴,当时叫洋火,那也是乡下有人只听说过,但绝对没见的东西。那么,人们在生活中,火源是从何而来?我告诉你,说起来确实可怜,他们的取火方法是火镰撞击火石取火。但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取火方法,要比我们的老祖先猿始人钻木取火先进了许多。
就是这种火镰撞击火石取火,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行的。在我们四个人中,只有那两位当哥的才行,我们两个只能站在一旁看。
孬孩哥取出火镰和火石,还有一个用泡桐棍筒装的草纸媒。只见他左手握紧火石和纸媒,右手握牢火镰。随即就用火镰用力撞击火石,火星四溅,没几下就点燃了那个草纸媒,取得了火种。随即就点燃了宝塔下炉膛中干柴草,浓烟立即就冒了出来。火舌舔着宝塔上的每块红薯。到此,我们的烤红薯才算真正的开始。
按规矩,两位哥是主烧,我们俩是邦办。邦办的责任我俩也明白,主要是到地里捡干柴草和完成哥们吩咐的临时差使。炉火着得很旺,冒出浓浓的黑烟。哥们正在聊着昨夜的农会开会情况,就是划成分,斗地主,分浮财,分土地。他俩聊得很来劲,有时竟然忘记往炉膛里加柴,眼看炉膛就有灭火的危险。我们当邦办的也明白,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炉子灭了火,主烧顾不及,我们邦办上。
于是我们两个就蹲不来,往炉膛里添加更多的干柴草。瞬时间,炉堂里就冒出滚滚浓烟,接着来的就是火势大旺。我俩看到成果显着,很受鼓舞,就不停的往炉内加柴,当然是火势更旺。
哥们正在那聊得起劲,回头一看红薯宝塔上冒出高高的火苗,立刻惊叫:
“你俩干啥?不能烧那么大火!看把红薯烧煳了。把火小点,慢慢烧。”
“好的,好的,火小点,慢慢烧。”俩邦办立即回应主烧。
于是,就减柴,文火慢烧。但总感到小火慢烧不赶劲,像这样,猴年马月才能吃到烧红薯?无形中,火可能又烧大了。
哥们还在那漫无边际的扯着,我们俩就在那尽职尽责的烧着。
“有煳味了!该翻番了!”
只听学文哥叫一声,立即来到红薯宝塔前:
“快停火!你们把红薯烧焦煳了!不让你俩烧那么大的火,你们就是不听!看把红薯烧成啥了?再烧一会就成一堆黒焦灰了!”
停了火,把烧煳了红薯从火堆中扒出来。发现迎火面都烧焦煳了,而背火面则尚是生的,没烧着。
没办法,扒了宝塔,重新再垒起来。不过这次是为了专烧生的那一面。
这一次不敢让我们邦办操作了,就有他们主烧亲自下手烧炉。我们俩邦办就去干我们的正事,去捡干柴草。由于我俩的蛮干,把本来有富余的烧柴已提前烧完。现在红薯还尚未熟,还需要柴。怎么办?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只好去捡柴草来。
最后,把我俩捡来的干柴草也烧完了,这也只好停了火。等消了浓烟,才看清红薯宝塔的真面目。从上到下一团乌黑,几乎分不出红薯的真面目。把塔扒开,立即就能闻到一种焦煳味,很是呛鼻!看来,这窑红薯是真烧过了头!
原来红薯上做的那些标记,早已被烧得无有踪影。当然,也就无法分辩出那个红薯是谁的了。
按理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是很少的。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不可怕。因为它有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规矩,可友好解决这个难题。
具体说,就是让长者或非责任人先挑,晚辈或责任人收底。
他们俩虽不是什么长辈,但他们是哥。在弟面前哥总是长者。所以这一堆烧焦煳的红薯就有两位哥们先挑。我们两位弟们,又是责任事故的制造者,理该收底。结果是,他们把那些大的,焦煳得不十分严重的都挑了去。剩下的,我就不用再描述了。不过,你也能想象得到,都是一些啥样的。
这次算我俩倒了霉。第一次烧得有点夹生,第二次又烧过了头,基本上全烧焦煳了。那些大的虽说也被烧焦煳了,但中间尚有不少未煳的好肉。而那些小的就不同了,由于它的体积小,不耐烧,焦煳了的部分几乎一直到了中心!哪还有能吃的?所以,我和老得只能啃一点焦煳的红薯焦煳灰沫,到嘴里感到苦得很,根本无法吃。最后,也只能落得个满嘴乌黑。
就这样,我们还得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说笑着过了这顿饭。
谁让我们比他们小,力不如人呢?不能得罪他们,不然他们发起狠来,不与我们玩儿,就坏了!
你想啊,这块地离家那么远,每天都是天一明就下地,有时到天黒还不能到家。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庄稼棵,一个人在这小路上走,确实够怕人的。万一从庄稼地里窜出个什么东西来,不要说是妖魔鬼怪了,就是一只兎子,也能把人吓个半死!再说,我们俩年龄小,玩不转那套火镰撞击火石打火的把戏。弄不着火,咋烧东西吃?一天两顿饭呢?咋弄?所以,大事上我们俩就离不开他们。这一点,我们俩知道,他们俩更是明白!
本来要吃两顿饭的时间,由于这次烧红薯的失败,拖拉了很长时间。草草的吃了点烧焦了的红薯焦灰,实际上肚子并没能填饱,在这里又没其他的东西可以下肚。再烧一窑红薯吧,所存的干柴草已烧完,要临时再弄些来也不易;同时也有点不想干。因为,这肯定又是我俩的事。
所以,我就提议提前回家。至于怕别人偷红薯的事,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就随他去!
这个提议得到了他们三人的支持。于是我们就拔腿往家走。
这时已是晌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估计应是下午的三点多钟吧。当时没有这个时间概念,白天都是以太阳的高低来说时间的。
我们往回走,太阳热辣辣地。早晨来的早,穿了个破棉袄。到了晌午太阳又好,走起路来感到热燥。只好把棉袄脱了顶在头顶,以遮太阳。老得也学我的样,把他的破棉祅也顶在头上走。
一路慢慢地走来,他们两个当哥的走在前,我们两个当弟的走其后。我听到孬孩哥说,他想当民兵。说民兵可以发枪,有了枪什么都不怕了。并说拿着枪可以打地主,甚至说把地主都打死。学文哥倒是较文雅,他说想去上学,将来当个老师。
我只在他们后边跟着,没敢接他们的话茬。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干啥?要上学吧,还真有点怕老师打;要说当个民兵吧,感到自己还小,扛不动那杆快枪。再说,我也怕那玩意儿,弄不好走了火,不是好玩的!
“渴了,弄点啥解解渴?”
我正在后边胡思乱想地走着,听到前边的孬孩哥叫着。
“我也渴了。上哪弄点啥解解渴去?”学文哥也叫起来。
于是,他俩就站在那四下瞅着。跟在后边的我们俩也只好停下来,看他们怎么办?大主意,我俩听他俩的。
“这里又没井,上哪弄水去?快点回家喝水吧。”老得站在那,向两位哥建议。
“不行。家太远了,现在渴得不行!得弄得啥解解渴?你俩到那块红薯地里扒两块红薯来,让咱解解渇。”
孬孩哥就直接命令俩小跟班去扒人家的红薯。
我从头顶棉袄的缝隙中四下瞅瞅,发现路北边就有一块红薯地。再往远处看,这块红薯地的最北头还能看到一个低矮的茅草庵子。
“不行。这块地咱不知是谁家的。扒人家的红薯被逮住了,可不得了。”我向两位哥申辩。
“没事。这时候地里哪会有人看。再说,就两块红薯又能咋着。快去扒!”学文哥也坚持让去。
“你看那有个庵子,说不定就藏有人。我也不去,怕被人逮住。”老得也表示不干。
“有个破庵子又咋了?这时候哪会有人!你听着,让我喊喊看。”于是孬孩哥就扯起喉咙来喊:
“北头那个破庵子里有人吗?有人就快钻出来!”连叫数声,没见动静。于是他就说:
“咋样?没人吧?没人。快去扒,没事。”
“说不定他故意不出来。等我们去扒了,他才突然窜出来,把我们逮个正着呢!我看咱还是回家喝水吧。要不,俺俩再回去扒咱自已的红薯来。这样保险!”我向他俩哀求着。
“你说什么混话!返回咱地里比家还远呢。要把人渴死咋的?快去扒!不然以后不理你!”
看来他是真恼了。我明白,这就是给我俩下的最后通谍。
我看看老得,老得也看看我。我俩也都看看那两位哥,他们都黑着脸。
我只好把头顶的棉袄拿下来,交给了孬孩哥,让他给我拿着。老得也同样把棉袄交给了学文哥。
就这样,我俩赤膊走进了,路北不知是哪家的红薯地。在红薯秧下寻找那被撑裂的地缝。这不难,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干这事。时间不大,就发现了目标。于是就蹲下去,挖开被撑裂的土块,下手去抠出了一块红薯。我拿着这块红薯将要直起腰来,就听到地南头的孬孩哥大叫:
“你俩快跑!地北头来人了!”
我一惊,朝北看去,果然看到有两人从地那头飞奔而来,还边跑边喊着什么。
事情突变,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最担心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也不容多想,扔了手中那块该死的红薯,拔腿就跑。待我跑到地南头两位哥的面前时,两个捉贼者也赶到了跟前。他俩气喘呼呼,用手抓住了我一只光胳膊,并不停的说着:
“我叫你跑!你还跑不?这回让我逮住了吧!”
老得的下场也和我一样。也被一个人拧住胳膊,在那数叨。
这两人我们都认得。他们就住在俺集东头,我家的后边,坑北。都姓杨,年龄比我们大得多,都已结婚成家。
当然,他们也认得我们。
抓住我的那位叫杨敬,他有一个弟弟叫杨学文。
说来也是真巧,今天扒红薯被杨敬逮住。为此,第二天我就被弄进了学校。走进一年级的教室,我的同桌就是杨敬的弟弟杨学文。他是我这一生中,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同桌。
咱不说明天的事了,接着还说今天的事。
杨敬抓住我的光胳膊,问我:
“你叫王正,是吧?”
我被吓得六神都无了主,说不出话来。只好点头承认。
“你扒了俺的红薯,是吧?”
我也只好点头,认账。
“好,你小孩。回去找你爹算账!”
杨敬松了我。这样我就更怕了,找我爹算账,那能是闹着玩的!我立即就软了下来:
“杨敬哥,你饶了我吧!我就扒了你一块红薯,还给你扔在那了。以后再不敢了,行吗?”
“不行。现在都解放了,你还偷东西。不能饶了你!”
说罢,他俩就朝地北头走了。
老得的命运也和我一样,人家也扬言要找他爹算账的。
我们站在那都傻了眼。他俩把棉袄都还给我们,我俩都乖乖的把棉袄穿在身上。不敢再顶在头了,因为那太招摇。
老得吓得哭了。我也想哭:
“这咋弄?闯下大祸了!”
“没事。不就是两块红薯吗?何况我们也没要他的,都还给他们了。”两位哥都在安慰我们。
“就你俩,喊着渴,叫俺俩去扒人家的红薯,叫人家逮住了!”我对他俩的不满,终于暴发了出来。
“你不能这么说!你俩去扒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可不能怨我们呀!”这是孬孩哥说的。
“不是你叫去的吗?你吆喝着渴了,非叫我们去不行。你咋就不认账了呢?”
听到他们这样说,老得也恼了,撕破了脸与他们吵起来。
“反正是你们去扒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与我们没什么关系!至于,是我们叫你们去,你们可以不去呀!既是你们去了,那就你们的事了!”学文哥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他俩耍了孬,也没办法。因为我俩打不过他俩,只能把恨藏在心里。
回到家,家里没人。没钥匙,也进不了屋,只能在院内转悠。
天到快黒了,爹娘和姐才回来。我什么话也没敢说,只在屋里床上睡闷觉。娘过来摸摸我的额头:
“不发热。哪里不舒服?”
我懒懒地说:
“没。想睡会。”
“睡啥睡?爬起来吃点东西去,天黒了再睡!”娘看没事,就吼我。
我总是担心会有人来,因为他说要找爹算账的。真怕他真来了,那真是要大祸临头了!这时对我来说,真是可以用那个词来形容:惶惶不可终日也!
我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向老天祷告着:快把时间飞过去吧,一下子能跳到明天,就万事大吉了。
“家里有人吗?”
我在床上刚想迷糊,就听有人在外边叫。我立马把眼睁得老大,来了!
“谁呀?有什么事吗?”
我听到娘出了屋门,与什么人打着招呼。
“王卓在家吗?”
听到来客又问。
“在家。哪一个?”我听到爹说着,也出了屋门。
“你两个呀。咋?有啥事找我?”
我听到爹与他们接上了茬。
“你那个小子回来了吗?”
听到来客问我爹。
“回来了,回来了,早回来了。咋?找他有事?”
我爹很客气的与来客对着话。但从话里也感到了一些疑惑。
“他回来,没跟你说啥?”
“没说啥。回来就歪床上睡了。咋?有事?”
“那有事。他在地里扒了人家的红薯,让人家逮住了。他回来没说?”
“啥玩意儿?扒人家的红薯?他没说呀!这是啥时候的事呀?”
“就是今下午的事。人家把你告了,现在来抓你哩。”
我在床上听到这里,才知道真是坏了菜了!为一块红薯被告了,还专门派人来抓爹。我还能在这床上装没事吗?看来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翻身起了床,来到了屋外。
“你,你,你扒人家的红薯了?”爹的话已不成句。
我站在那浑身打颤,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回答爹一个‘嗯’字。
“看他认账了吧!”
来的两个人也没再多说,就看到一人从腰里掏出一根麻绳,三下五去二的就把爹五花大绑了。爹的双手被反绑了个结实,推着后背就出了院。
这时我叔和婶听到院里有动静,就出屋来。当看到我爹已被那两人推着出了院,忙问咋回事?
“我也不知咋回事?来两人说咱孩子扒人家的红薯了,就把你哥绑走了。”
我娘惊魂未定,对俺叔婶说着哭了。
“来的这人,是啥人?”我叔又问。
“人倒是都认识,都是咱东头的。一个是殷梳,另一个是卫孩。都是跟着梁区长干事的,还背着枪哩。”我娘说。
这时从南也过来三个人。走到面前,看到前边走的是麻欢,也被绳捆住双手。后边也跟了两个梁区长的兵,也都背着大枪。
看来,老得的爹也没能逃脱。
爹被绑走了,全家人就开了审问我这个罪魁祸首。我只好把扒人家红薯全过程交待出来。
你想,全家人哪个会饶我?都不会!
同时,我也不能希望能有任何人饶我!因为我作的恶太大了!把爹都邦走了,还不是罪大恶极?也可以叫罪恶滔天!
就这样,任凭全家骂。让骂足了,骂够了,骂烦了,最后是骂累了,天也明了。
我正担心着,新的一天该咋过去?还没起床,就听到爹在外边与我叔说着话。
咋了?难道说,我爹回来了?